2012年9月,是《书摘》杂志创刊二十周年的日子,二十年了,做为一名在《书摘》工作的编辑人员,会觉得时间过得太快,真有一点稍纵即逝的感觉,二十年前的事情,就仿佛发生在昨天,陈年的旧人旧事会一下子涌上心头,产生无限的感慨,感慨那些曾经和你生活过的同事以及逝去的人,你这时也才会想,应该记下你本不应该忘记的人和事,那些曾经感动你的人和事,那些曾经帮助过你和爱你的人,以及你所尊敬的人。当然首先映入我脑海的就是《书摘》杂志的第一任主编乔福山先生,掐指一算,乔福山先生离开我们是2010年4月,已经二年多了,二年多来,乔福山先生的音容笑貌时不时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激起我心中的惆怅。
乔福山先生原是光明日报文艺部主任,退下来后创办《书摘》杂志,并任主编。当时没有人叫他乔主编,都习惯地叫他老乔,似乎这样叫更亲切,叫主编似乎总有一点“隔”,这不仅是同事们的想法,老乔的想法恐也如此。所以在下文中我想还是沿袭一贯的叫法:老乔。这样显得自然。
我刚接触老乔时,就觉得老乔很好接触,他在离你很远的地方走过来时,脸上就已经是满脸笑容,那个笑容很慈祥,很随和,走过来和你说话,声音略显得粗而且很低,好象那话是在嗓子眼里。如果我们不看人,只听声音的话,你会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很本分,很讲究规矩的人。而事实上,老乔在性格上也确实与这些相近。我和老乔工作这么多年,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诳话,大话,不近人情的话,说起话来总是和颜悦色,平心静气,人做到这点看似容易,其实没有很好的修养很难达到这一境界。
在《书摘》的创办初期,就老乔所招的编辑来看,都是非常喜欢读书的人,我们现在回头总结一下,因为有这样的编辑队伍事实上是已经给《书摘》定下了格调,就是《书摘》肯定是一本读书人的杂志,带有书卷气,在俗与雅之间,他自然是偏雅的,这就是俗人雅不了,雅人俗不了,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编辑,就会编出什么样的杂志,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和特色,以及什么样的品味,这也符合古人讲的天性使之然的道理。人性决定人的形象和品质。
比我们老一辈的人,也就是现在已经七八十岁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他们总觉得自己肩负着责任感和使命感,怀揣着以天下之任为己任,老乔也不例外。他十分关心社会的变革和文艺界发生的事情,关心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他们思考的一些问题,关心古今中外的政治风云和社会矛盾,他与我们平时聊天的话题总是围绕着这些内容,虽然他没有写文章张扬自己的主张和观点,但他的内心是活跃的,时时思考着这些问题,我们现在管这种思考叫忧患意识,老乔是有忧患意识的。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书摘》具有了深度和广度,具有可读性。如果《书摘》还有读者喜欢的话,喜欢的也正是这些带有忧患意识的文章,因为它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这个传统二十年来一直延续至今天,我想这是对老乔最好的告慰。老乔与当时的知名学者和作家很熟,他找了许多名家名人给书摘题词,画画,在这方面老乔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在《书摘》除编辑稿子还搞过发行,老乔因为跟山东有关系,所以我和老乔去济南搞发行,当时山东省委的同志让我们住高级的饭店,老乔拒绝了。我们住在山东科技出版社的招待所,招待所很简朴,很干净,记得早餐山东科技出版社过于热情,两人的早餐够四五个人吃,老乔跟我讲,让他们明天少做点,这太浪费了。我告诉了王为珍社长,第二天给减下来了,但依然不少,这也看出山东人的热情。那次搞发行很有趣的一件事是,我跟老乔说,我几年前到济南时,早晨逛早市,买过几个小碗是元朝的,一个也就十几元钱。老乔听了很感兴趣,他让我第二天早晨也带他去看看,第二天去时那已经不是早市,而是很安静的街道,不过在街道上有几家古董商店,我们进去,老乔见里面有卖笔筒的,店家说是清朝的,老乔要买,我说可能是假的,但老乔说他很喜欢这几个笔筒,一共买了三个回来。回到北京后,他跟我说,那三个笔筒确实是假的。
老乔后来退休了,说起来真是凑巧,他与我的姐姐住在一个大院里,而且相隔不远,这样,我去姐姐家时,就常到老乔家去探望他。他住在一楼,南窗不是很大,屋里东边的墙壁书柜里放满了书,书柜顶上还放着老乔买来的瓷器,所以屋子的空间小了,自然显得有一点昏暗,昏暗看似是弱点,但是它也会给人带来一种意境,就是宁静,老乔给我沏上一杯茶,我们就可以在促膝大的地方长聊,而且无拘无束,老乔说话比较低调的声音此时也显得格外清晰。老乔确实喜欢瓷器和古董之类,他退休还买一些新的瓷器,但是他也买一些旧砚台,老乔跟我讲:“我对砚台还是懂的”。他大概买了有十几方,每次我去都拿出来让我欣赏,在他去世的前三、四个月,我去他家,那次不知为什么他非要送我两方砚台,他说:“你老来看我,我也没什么好送你的,你喜欢写字,送你两方砚台”。我再三推辞不过,最后只有接受。现在这两方砚台到是成了我和老乔友谊的见证。有时候我也胡思乱想,他为什么偏偏要送我砚台,而后过了三、四个月就告别人间,病重住院也没有让大家知道,就这样匆匆而去,是不是他有预感。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后悔我和老乔最后一次见面时应该多待会儿,多聊会儿,要知道这最后的一面真的是永别,永别意味着什么,对生者来说是痛苦,对逝者来说对这个世界是全然不知。在我得知老乔逝世的消息时,独自在家里落了很多眼泪,因为他是我十分尊敬的师长之一。在人的一生中,其实我们是要感谢那些曾经帮助你和爱护你的人,对于老乔我是要感谢和崇敬的。
我和老乔聊天内容很丰富,老乔知道很多文艺界的纷纭趣事,他也常给我讲,比如他到钱钟书那里,钱先生跟他讲的话,他到杨宪益那里,杨宪益跟他讲的话等等,都极有趣,还讲那个写《疯话连篇》的作者老宣,那是他的高中老师,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老宣》,当时老宣的书卖得很火,但是大家对老宣的了解却知之甚少,老乔的这篇文章,到是给读者了解老宣打开了一扇窗户。从他的那篇文章中得知,老乔年青时还写诗,极富有个性的老宣当时对老乔寄予希望。他还常跟我说:“这个时代我最佩服的作家是邵燕祥,何西来(著名文学评论家)说邵燕祥是当代鲁迅,我看也是。”他和邵先生是中学校友,过去不知道,只是在前些年的校庆时才彼此清楚。当邵先生听我说老乔去世,还特意给老乔的女儿写了封信以示问候。老乔对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很关心,常问这问那,问单位的情况。他的这份关爱给我带来许多温暖,至今想起这温暖还在,热乎乎的,我现在也五十多岁了,叫做“知天命”。我越来越清楚,人间的关爱比黄金还珍贵。当我们得到他时并不在意,当我们失去时你才清楚他的价值。好在老乔把这份温暖和关爱给予了我,谢谢他。
老乔晚年出了本书,叫《文艺伦理学初探》,钱锺书先生题写的书名。这本书一般人是不会读的,但老乔对这本书其实很重视,他曾经跟我说,他写的这本书其实是很有开拓性意义。我认为也是这样。文艺伦理学涉及的面很广,伦理这个东西是超出文学之外的,所以要想写好有相当的难度,老乔却知难而进,这能有几个人理解呢?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你在干时别人是不理解的,所以写作者是要承受寂寞和孤独的。
回想我和老乔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私人的交往上,用什么来形容老乔才恰当准确,我想《诗经》里有四个字确是能描述出老乔的学养和性格,就是“温温恭人”。“温温恭人”是儒者的风范,是一种涵养,是读书人的品质。
在《书摘》杂志创刊二十周年之际,我们是不应忘记我们本不该忘记的人和事,尤其是《书摘》的第一任主编乔福山先生,此时此刻,我想跟老乔聊一件事:前些日子,我到邵燕祥先生家,我让邵先生在他的书上给我写几个字。邵先生略加思索写下:“五百年修得同船渡,保留住船票再渡五百年”。他写完我十分欣喜,此话说得太绝妙,太有意境和诗意,现在我想把这句话转告给地下长眠的老乔,我们也是五百年修得同船渡,我们的友谊长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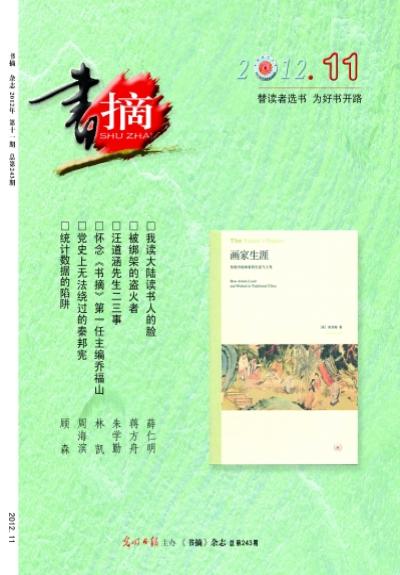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