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昕新写的这些启功先生片言琐记,大都鲜为人知,不仅体现了启功先生的幽默,还让人深省、深思,也是别一种的诲人不倦。
我在先生家闲谈时,先生兴之所至,常有卓识独见或掌故逸闻,使我获益匪浅,亦更深入地了解到先生的性情为人。
有一次与先生谈论诗歌,我说先生以口语入诗,而且入出“打油”风格,在当代应推第一。先生听了,并不以为然,说:“这类诗聂绀弩作得比我好,人家那是真好,我比不了。”姑且不论两位大诗人如何分割秋色,先生这话却是由衷之言。后来我们又谈到张中行先生的《负暄琐话》一书,先生的评价是:“哲理深,情意浓,议论周密严谨,很有逻辑性。真好真好。”谈到张先生的《顺生论》,先生笑道:“那可以算是一部《春秋繁露》。”
先生作有一首七言律诗,题为《一九九四年元日口占》,诗曰:“起灭浮沤聚散尘,何须分寸较来真。莫名其妙从前事,聊胜于无现在身。多病可知零件坏,得钱难补半生贫。晨曦告我今天始,又是人间一次春。”先生说,此诗的末一句“又是人间一次春”的“次”字,原来写的是“度”。但细推敲,“度”字文人味儿重,不如“次”显得直白。我听了后,觉得先生的话只说了半截儿。我的体会,“次”字除了直白,并有调笑的味道外,还有一种无奈的心境,很有意味。由此我联想到曾经问过先生作诗的速度,先生说:“有时作一首诗倒不难,很快。但常常被几个字或一个字别倒了,好久才能爬起来。”
先生又曾谈起,说胡适先生讲,作诗必应有幽默。其实不是必应有,而是诗歌中本身就有调笑的成分。先生对古诗词亦多有独到之见。如对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末尾的解释,先生说:“末尾这句‘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我有个解释,即,谁在多情而笑?这个人,是周瑜,是周瑜的鬼魂在多情笑我早生华发。为什么这样说呢?苏轼词中所游之处是周瑜当年拥兵坐镇的地方,是吴国的属地,所以,故国是周瑜的故国,即吴国,而不是苏东坡的故国,‘故国神游’,指周瑜的鬼魂于吴地飘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是指周瑜赤壁破曹时正值壮年,雄姿英发,风流飘逸,人号‘周郎’;而‘我’,即苏东坡,此时也值壮年,却已‘早生华发’,两相对比,想周郎若多情,是要笑我这未老先衰的样子的。所以下面才有‘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我这个讲法还从没有人讲过,为什么呢?因为容易被人讥为‘活见鬼’!苏轼瞧见周瑜的鬼魂了,这还不是活见鬼!虽然没人敢说,可是我敢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顺带说一句,先生对苏轼是很推崇的,他曾作《东坡像赞》道:“香山不辞世故,青莲肯溷江湖。天仙地仙太俗,真人惟我髯苏。”
先生有一次谈到《红楼梦》时,说:“我有个老朋友,有一回闲聊,说到《郑板桥集》和《红楼梦》,他就给了一句话的评价:‘那都是人道主义。’我回来琢磨,还真是。《郑板桥集》不必说了,《红楼梦》里有一段,讲贾宝玉的书童茗烟与丫头万儿在书房里行男女事,可是不巧,正让贾宝玉进来撞见。两人魂飞魄散,一齐跪下了。宝玉却一跺脚,说:‘你们还不快跑。’两人这才如逢大赦,飞一般地跑出去。宝玉又追在后头喊:‘你们别怕,我不会说出去。’你说这是不是人道主义?”
先生非常推崇和敬佩弘一法师李叔同先生。先生说:“弘一法师那不单是大文学家,最令人敬佩的是他的救世济人之心。举个例子,他每天只吃一顿饭,白水煮萝卜,连一点油也不放。旁人都认为他太苦了,我揣度他的想法,大概他认为自己既是佛门中人,又解救不了大众之苦,于是只有自己多吃些苦来作为补偿。真是可敬。”先生曾有诗赞扬李叔同先生,诗曰:“吾敬李息翁,独行行最苦。秃笔作真书,淡静前无古。并世论英雄,谁堪踵其武。稍微著形迹,披缁为僧侣。”
先生曾在闲谈中说:“我这些诗词歌赋作文章的底子,以及古汉语的基础,全是从戴姜福先生念书时打下的。”至于具体如何打下的,先生没谈。近阅侯刚先生《学高人之师身正人之范》之文,内中对此有所记载。文曰:(启功先生)经他家的一位老世交介绍,随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文章。他(启功)见到戴先生时已是青年。先生对他说:“你已这么大年纪,不易再从头诵读基本的经书了。”于是教给他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拿没有标点的木版古书,先从唐宋古文读起,自己点句。每天留给他的作业,有厚厚的一叠,理解上既吃力分量又重。启功有时想:“这些文句没经老师讲授,自己怎么能懂呢?”老师第二天拿到作业后,便顺文念去,将点错的地方一一指出,并详细加以解释。这样在老师的“追赶”式的帮助下,他读完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又读《文选》,返回又读“五经”,从似懂非懂,逐渐懂得了读书的要领。不懂的地方也学会了怎样找资料,以及读一部书时先了解全书概貌,再逐步弄清细节的方法等等。掌握读书要领之后,他读书的兴趣愈加浓厚了。以后,他又买了一套“二十二子”,先读了《老子》、《列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戴老师喜欢《说文》、音韵诸学,选了常用字若干,逐字讲解它们在“六书”中的性质和意义,真使他如获至宝。戴先生又谆谆嘱咐他要常翻《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并用《历代帝王年表》作纲领,了解古代历史概貌,再去读《资治通鉴》。戴先生还经常出题命他作文,并教导说,在行文上要先能“连”,懂得“搭架子”。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作文要讲究语言的逻辑性,文章要有主题,要层次分明。至于作诗、填词也经常练习,要按时交出习作,老师再给予修改。由于老师的精心培养,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起,(启功)便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先生论及自己的诗词风格时,说:“我的许多诗,都是在很难过的情形下写的。”继而又笑道:“即便是打油诗,那也是化悲痛为玩笑。”我随便说了句:“您可以少作一些应酬诗,多写心曲之作。”先生正色道:“凡收入集子里的诗,即便是酬答之作,也都有些意思在里头。完全应酬的,我也不收。”
某诗词学会出了一本诗歌大赛的优秀作品集,题为《金榜集》。友人送我一本,我又转送先生。先生拿起看看,随手翻翻。我说:“我看了,觉得好的不多。跟朋友一说,朋友说:‘那当然,好诗都在《落榜集》里。’”先生抚掌大笑,说:“妙!”
我祖父在北大念书时,当时国文系名教授、诗人黄节先生善书。祖父曾请黄先生书写一副对联,联句集的是宋人词。联曰:“海棠如醉,又是黄昏,更能消几番风雨;辽鹤归来,都无人管,最可惜一片江山。”上款为:“颖明学弟属书楹帖集宋人词句”,下款为“甲戌中秋前十日黄节书于北平”。我某日将此楹联带与先生观赏,当时先生家中正有几位贵客。先生打开一看,连声赞叹。当着客人的面即道:“这写得好,写得好,我那字算什么呀!”先生谈到自己作为博士生导师时,又说:“带博士生,你爷爷,行。我怎么能带博士生呢!”
1995年夏,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为祖父举行九十诞辰纪念活动,启功先生到会并写了两首诗,诗曰:
陆颖明先生(宗达)诞生九十周年学术纪念会颂言(二首)
学溯蕲黄承绝诣,微言故训首名家。
后堂丝竹传经乐,多少英贤出绛纱。
回首交期六十春。人间已换几番新。
《汉书》下酒微伤雅,何似擎杯听《说文》。
(昔年诫聚,必推颖老讲《说文》数字,四座举杯而听,今惟不佞一人在矣。)
先生不仅写了字幅,而且还亲自托人裱好。听说开会的前一天,主办者曾想先拿去以布置会场,先生未允。第二天他亲自挟着坐汽车来到会场,亲眼看着悬挂起来。挂好后,与会者皆称赏不已。有位师大资深教授对我说:“先生给你爷爷写的这幅字,在他的字里,也要算是绝精的。”发言时,先生忆道:“陆先生算是我的老前辈,比我大七岁,管我叫小启。当时在辅仁的青年教师中我也是岁数小的,后来又来了个比我更小的周诅谟,于是他成了小周,我升成中启。对陆老我有几方面的认识,人是最坦率,平易近人,说错了什么,也乐于承认,表里如一。除了人品外,还有学品,特别值得我们纪念。陆先生不摆架子,不摆训诂学家、音韵学家、语言学家的架子,讲一个字不厌其烦,真正诲人不倦,不教会你不罢休。兴趣也广,会唱昆曲,还上过台,唱《游园惊梦》,扮过大花神。通文学,对史学也有研究。记得我们在辅仁教书时一起吃饭,饭前等菜时,陆先生就用饭馆里开菜单的条子,拿笔在上头写写画画地讲《说文》。比如‘碗’字古时候怎么讲怎么写,‘炸’字在古文字里怎么写怎么念,到今天意义有什么变化。不讲几个字,大家不吃饭。所以当时我们都怕早上菜,大伙举着杯不喝酒,陆老讲一个字大家喝一杯酒。而今,当初席面上的那些人只剩我一个了,所以今天我心里头这酸甜苦辣也说不出个滋味。”会后,先生对我说:“你爷爷跟我说过,黄侃曾经告诉他,做学问不怕标新立异,但是一定要能自圆其说。今天我好几次想说出来,最后还是没说。”我问:“为什么?”先生说:“我一看,台上坐着那么多语言学家,心想,人家那都是内行,我还是别说了。”
先生谈及文人逸事时,曾说到清末民初名士吴江沈羹梅先生,先生道:“你爷爷和赵元方(著名版本学家、藏书家)跟他学过文词。这位老先生很有意思,他有个特点,非常爱整洁。有一回他去某人家,见某人桌上杂物堆积如山,于是他一边说话一边收拾,一会儿便书归书,本归本,笔墨纸砚一一摆好,连掉在地上的东西都给捡起来。等沈先生走了,那人告诉他的朋友们,谁家乱,又懒得收拾,一定请沈先生来做客,一会儿准干净。解放后,沈先生与潘伯鹰先生等人都在上海文管会负责监督文物,那些个老先生在一起时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某次先生谈及人生的遭逢际遇,最后说到自己时,从容道:“我这一生经历坎坷,哪一步也没走到点儿上,到现在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我问先生为何不写回忆录,先生摇头道:“不能写,不能写。”我追问原因,先生笑道:“用曹家麒的话说,这叫‘自寻烦恼’,何必把烦恼重温一遍?”曹家麒是先生的挚友,因面长,绰号“老驴”。
有次我在先生家,正碰上某出版社来人求先生点儿事,同时送先生两本巨大开本、印刷精美、装帧讲究的“文革”时代的图录,上面什么红卫兵造反、抄家、打人、游行、批判、揪斗、喊口号、大字报、认罪书、唱嚎歌、剃阴阳头、坐喷气式、脖子上挂牌、头上戴高帽、两派武斗、大联合、样板戏、芭蕾舞等等,千奇百怪无所不有,集愚昧凶暴阴暗狠毒外加狂热之大全,倒真是难得史料。几位一边给先生翻看这书,一边争先恐后地说这书的图片如何难得,史料如何丰富。孰料先生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突然厉声说:“你们把它拿走!”几位一愣,不明所以,还是劝先生收下,先生又厉色道:“赶快拿走!我看着它恶心!”
多年前,我出了本儿书,准备送先生,题名时有点儿犹疑。因为先生长我四十多岁,小时自然叫他爷爷。可那年我也四十了,不知道这称呼是否还合适。可是写先生,生分;写老师,更生分,最后还是沿袭过去。先生接过一看,果然说:“不用这么称呼。”那怎么称呼?先生说:“回头我拿个刀片儿,把后边这个爷字刮去,这样我就成了启爷,以后咱们就是张爷、李爷、马王爷的那类称呼。”
某次我去琉璃厂逛书店,无意中从旧书摊里拾得曾是先生收藏的《文心雕龙》,清末湖北崇文局本,两册。上册钤一图章:“启功”,下册钤一图章:“元白”,索价亦不高,我遂买下来。后来我给先生送去,先生看了看,说:“当年我嫌这书纸脆,老掉末儿,处理了。那时处理的还有一种什么书,上头有我的批,你见过吗?”我说,没有。谈话中我向先生请教有关版本的问题,先生非常认真地对我说:“这类问题你以后还得多请教书店的老师傅。人家卖了一辈子书,经眼无数,版本知识不得了。别看咱们是教书的,在人家面前可不能端架子。要虚下心,多问才能多受益。”
外界传说先生对京剧很不以为然。有一次,我问先生。先生连连摆手,说:“不是这么回事。我是说,清末时,许多贵族子弟生活腐朽,无所事事,无聊中爱上梨园这行,粉墨登场,摇头摆尾,拿腔作势,那真叫丑,恶心。至于京剧本身,那是艺术,人家演员是正正经经的艺术家,我有什么可反感的!”由这儿先生又谈到清末时事。先生说:“其实清政府也不是不想振作,好把它的统治维持下去。可它所依靠的这些子弟已然腐烂了,站都站不住了,还振作什么呀!对于清政府来说,这也是最痛苦的事。它眼瞧着自己一步步灭亡,就是想不出救自己的法子。这就好比一个人长了大疮,干瞧着自己身上的肉一块一块往下烂,就是留不住,烂完了算,你说多痛苦。”
前些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举行《启功诗作墨迹影印本》、《郑板桥集善本影印本》首发式,先生到会并讲话。先生照例先客气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不过我感谢之余,还得指出,出版社今天把我和郑板桥的诗集弄到一块儿开首发式,这里头可有意思。我们这些写写画画的徒子徒孙能和祖师爷相提并论吗?把我和郑板桥的书放到一起,这是出版社有意让大家对比着瞧,你们说这有多损?!”先生话音未落,立时赢得一片笑声。随后王世襄先生讲话,头一句话是:“我们这些个人,连启功的脚不丫泥也比不了!”
有一天,先生跟我说:“有人打电话给侯刚,问,启功怎么了,中南海那儿有人聚会,说要给他一说法。一打听,原来是一群练气功的。这以后我要改名了。我不叫启功了,我叫启(起)哄!”
有一回李双江去看先生,送先生一张自己的CD。先生把盘从纸袋中拿出,还给李双江,自己留下空袋子。李双江正奇怪,先生慢悠悠地说:“我不听音乐,我也没有放你这个东西的机器,所以这个还给你。袋子上有你写的字,我留下。”
(摘自《启功:诗书继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定价:2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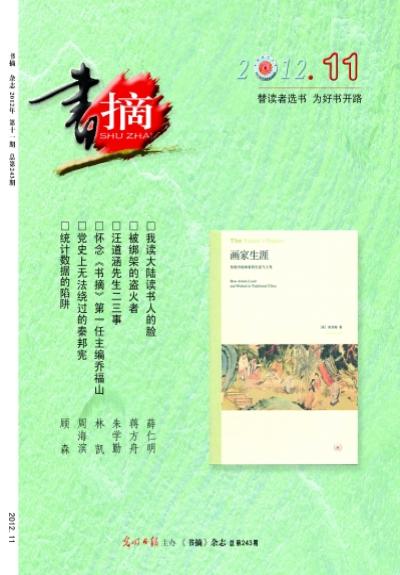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