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县交警队的白色宣传车停在广场边上。车门开着,后座上堆了些宣传交通法规的小册子,59岁的游嘉良坐在车里,一身藏青色警服,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肩上扛的是“两杠三”(一级警督这样的警衔在县城里算是到头了,县公安局局长也不过如此)。游嘉良把白色大檐帽摘下来放在腿上,戴了几年,可帽子的颜色他还是不大习惯。交警队里,他的警服也跟别人有小小的差别,别人臂章上绣的是“公安”,而他的是“司法”。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他一直是监狱的管教干部,担任过教育科科长以及好几个大队的大队长。不过,五年前,他所在的监狱在布局调整中被撤掉了,三千多犯人被分送到省内的其他监狱,干警们也都分流走了。他没去找新单位,还有几年就退休了,就领退休金了,何必呢?作为监狱的“留岗休息”人员,他拿着监狱发的工资,还可以帮交警队搞搞宣传,“打打零工”,只是每隔一段时间,他要回到那个已经荒废的监狱去值班。监房还在,尽管已经破败不堪,但毕竟还是国有资产,他们这些“留岗休息”人员要轮流去看看。
每当坐上重返监狱的中巴车,望着车窗外那熟悉的山坳,过去的日子,又回来了。
一
41年前,游嘉良的梦想是报考清华大学的物理系。
不过,和很多同龄人一样,他的大学梦毁于那场跟文化有关的运动。1970年,在晃荡了四年之后,这个1966年高中毕业的“老三届”从县城下到乡里当了一名物理老师。
他课教得好,学生喜欢,老师们也认可,可却始终不快乐。在那个乡中学,有人提才能上调工资的考核榜。他不是本乡人,没人提。所以,每逢调工资,他便会心寒。1984年,他终于离开了站了14年的讲台,换了工作。
新单位便是那所监狱,一个寸草不生的地方。犯人主要的劳动是日复一日地在山洞里挖硫黄,山坡上的那些绿色早被硫黄熏得没了踪影,吸入鼻腔的永远是那呛人的臭鸡蛋味。当地人告诉他,这地方也叫硫黄矿。
可游嘉良喜欢这地方。
这里的一切是那样不同,什么样的事情也都有可能发生。和一成不变、充满排外思想的乡中学相比。这个劳改局直管的省级单位似乎更具包容性,干部和犯人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没人再将他视为外乡人。
他先是在子弟学校当老师,然后很快成为了大队里的管教干部。他穿上了警服,别上了手枪,那都是他一直梦想的。那身“行头”让他精神抖擞。
二
这既是一个严肃的专政机关,也是一个效益不错的国有企业。
计划经济的年代,硫黄生产出来是不用愁卖的。监狱那时候是全县的税收大户,内部有的是钱,什么都周转得开。犯人们永远都有新囚服和新鞋穿,精神面貌好,劳动积极性也高。监区有好几个大队,每个大队分工不同:一大队负责修房,二大队负责发电,三大队负责养猪,四大队负责种蔬菜水果,五大队负责挖矿……每个月生产出来的肉、蔬菜、水果吃都吃不完。犯人们除了劳动改造,还要在育新学校里学习,参加扫盲班、技工班,学识字,学木工、泥瓦工、煅工……教室是崭新的,课桌也是崭新的,比周围的乡镇学校条件不知好多少倍。监狱有时还会请文化教员来教乐器,让他们陶冶情操。附近农民没见过小提琴和萨克斯,他们会指着那些形状各异的黑皮箱好奇地问游嘉良:“游大队,这是什么新式武器?”
监狱还会请县上的人来放电影。电影一般放两场,头天干部看,第二天犯人看,在操场上放。“首映”的时候,干部家属们会提前把自家小板凳搬去围成半圆占位置,如果是冬天,孩子们还会带个小火炉来,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边烤火,边看电影。那时候演的是《地道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嘎》……不过,在游嘉良的记忆里, 《少林寺》才是最轰动的,放映时,整个监狱像过节一样。
那时候,干部们总有机会喝点小酒,打点小麻将,或是到周末舞会上跳跳舞。生活虽然比不上现在的多姿多彩,却也让当地人无比羡慕,因为附近农民当时还在住土屋,点煤油灯。
在这个不毛之地,如果有人打听硫黄矿怎么走,别人会告诉他,顺着这条路走,突然看到一个灯火通明的热闹地方,那就到了。尽管空气中永远弥漫着臭鸡蛋味,尽管山坡上常年寸草不生,尽管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可还是有很多人想到这里工作。一些附近的农民问: “同志,我可不可以进来劳改?”
三
硫黄矿里自然是要釆硫黄的。
游嘉良当过采矿队的大队长,那时候,每天七点半,他都会准时站在操场上给那些下井的犯人点名,安排他们当日的工作。工作量是自上而下定的,劳改局下达一个总任务,监狱再分到各大队,大队再分到中队,中队分段,段再分小组,最后制成生产报表,考核完成。
任务不是他定的。有时候,碰到任务量突然加大,他就会对他们说:“这个工作量对大家是一个新挑战,你们有没有信心接受?”
“有!”犯人们总会声音洪亮地回答。他知道对于犯人来说,有没有信心,他们都得接受,自己多问一句,只是给他们一些鼓励而已。
通常这种时候,他还会换上工作服,戴上装着矿灯的安全帽,勒上口罩,顺着那条斜斜的巷道下井视察工作。他并不害怕。尽管“瓦斯爆炸”、“偏崩(从旁边垮)”、“冒顶(从上面塌方)”等一系列事故名称经常被人们提起,但他自己还是有必要下去。下井视察能调动犯人的劳动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完成生产任务,他相信这一点。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抓那些牢头狱霸的现形。逼迫其他犯人为自己劳动的现象不允许存在,可还是存在,即使劳动力不够,他也要把这些“抗改分子”送去严管队,因为他们不但不劳动,还会影响其他犯人的劳动情绪。在严管队里,这些“老大们”将喝不到热水,吃不到热菜,只有定量的干馒头。什么时候出严管队要看表现,少则三五日,多则几个月。
井下的硫黄味最呛人,很多犯人都觉得分到这个队最倒霉。他就挨个找他们谈心,消除他们下井的恐惧思想,请人给他们传授专业知识。后来,恰恰是那些当初下井队的犯人出狱后最厉害,他们熟悉井下构造、矿石分析,精通各种井下设备的使用和修理,很快就当上了小煤矿的老板,发了财。
四
有时候,游嘉良觉得,手下的一些干警比犯人更难管理。他们总是抱怨“犯人是有期徒刑,管教干部是无期徒刑”。他觉得这都是些牢骚话,他不喜欢听。当他听到他们抱怨“这鬼地方,不是人待的”的时候,他就会问:“不是人待的,我在这里待了二十多年,难道我不是人吗?”
刚来的干警更令他啼笑皆非。他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和犯人隔离开来,宁愿自己饿着,也不吃工地食堂里犯人做的饭,他们怕犯人会下毒。尽管缺乏生产经验,但是他们还是固执地安排犯人照他们的想法去劳动,因为他们不相信犯人会改好,会好好劳动。他们没想过,大多数犯人都想好好表现,争取评上劳改积极分子,争取减刑加分,早获自由。他发现他们似乎并不懂得这些最基本的道理。
尽管从1990年开始,国家就明文规定禁止体罚犯人,可体罚现象依然存在。一些打过犯人的干警外出时会提心吊胆,害怕遭到报复。
游嘉良想不出谁会报复他。他在基建队时盖房子的犯人,当上了包工头;他在下井队时挖硫黄的犯人,当上了小矿主;他在教育科时帮他出《新生报》的犯人,现在是县里广告公司的老板。只要在外面碰到他,他们还是叫他大队长,要招待他吃饭。
五
不是谁对追上时代步伐都有信心,监狱也一样。
从1994年开始,监狱便开始追不上这个时代了。因为便宜,国家开始向加拿大进口硫黄。市场经济让中国的硫黄市场迅速疲软,监狱开始面临接连不断的冲击,犯人们挖出的硫黄卖不出去,可监狱局下达的指标还得完成,资金周转开始困难,只能节省开采成本,然而在科学有效地开采这一前提下,成本不够就开采不出来。经济效益不好以后,福利就越来越少了,伙食越来越差,干部压力越来越大,开采成本跟不上,犯人只有加班加点地做,通过超强的劳动才能完成生产任务。到后来,为了完成生产任务,只能是乱采滥伐,一座预计还可开采50年的硫黄矿在十多年内可采资源迅速枯竭。
硫黄矿开始进入恶性循环的时候,管教开始把怨气发在犯人身上。犯人不时地挨打挨骂。每次游嘉良听到山坳里回响的枪声时,他知道,又有犯人跑了。
七八月间,收玉米的时候,犯人爱跑,他们能轻易地把自己藏到茂密的玉米地里。停电的夜晚,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犯人也爱跑。
犯人跑了就要去追。追之前,先要上报狱政科,调出档案分析,犯人可能会往什么方向跑,并制订追捕方案,然后到所有可能会经过的路段设伏蹲守。当地农民觉悟高,胆子大,只要听到枪响,他们也会提着锄头出来追,抓到逃犯,监狱是会给奖励的。路上守不到,就得赶紧去犯人家。在犯人家一蹲好几天是常有的事。有时能抓回来,有时抓不回来。抓不回来就要被扣钱。劳改局扣监区的钱,监区扣大队的钱,大队扣中队的钱,中队扣个人的钱,一层层地扣。跑了犯人的管教很长时间内都抬不起头,晋级、涨工资也都受影响,管教情绪更恶劣,犯人就更加痛苦,各种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伴随着监狱的下坡路。
六
再也挖不出硫黄了,领导们开始思考监狱的出路。刚开始,计划整体搬去旁边的金沙县搞煤矿,可偏巧那时候贵州发生了几起矿难,上面便没有批。于是,各个大队的队长就带着那些刑期短、表现好的犯人出去打临工,帮别人挖煤、修路、打石头……什么都做。
监狱一直熬到2002年才正式解散。那一年,贵州省监狱管理局进行布局调整,撤销一批长期亏损或是为适应时代需求而建在偏远之地的监狱。大方监狱两个条件都符合。
七
几十年来,监狱和当地人形成的是一个二元世界。监狱的子弟学校不招当地的学生,监狱自己发电,自己养猪,自己种菜,从不向当地人买东西。也不跟他们来往,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部给了他们难以控制的优越感。唯一的来往是给当地人赔钱,硫黄的烟熏死了他们的庄稼。刚开始,农民单纯,觉得监狱就是国家,赔多少是多少,说什么是什么。到了硫黄矿走下坡路的时候,农民却有了经济头脑,开始提出更多的赔偿。
不过,与此同时,国家刑罚的威慑力也在当地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里的治安,一直都比附近村寨好。当地老百姓还意外地学会了一件本事,讲道理。过去,这里出现纠纷靠的是宗族势力和谁家男孩多,打架厉害。而在后期,经过和监狱长期的处理纠纷的实战训练,他们发现要在监狱干部面前捍卫自己的权利,只能是去跟他们讲道理,所以,附近村寨的农民都比别乡的更擅长讲道理。
几条岔路通往附近的寨子,他能隐隐听到寨子里的鸡鸣犬吠。一扇扇监房的门都敞开着,他突然间想去摸摸那些墙壁和地砖,敲一敲,看看会不会有地道,秘密夹层,或是伪装起来的门。他觉得自己有些好笑。
他路过井口,硫黄矿早已封闭,井口外有一潭透着铁锈色的死水。他曾以为硫黄的味道将会伴随他一生,可现在却消散得无影无踪。他有些怀念那刺鼻的味道,它是消毒的,这让他从来不得什么皮肤病。他经过炼硫黄的混凝土燃料炉,一个老人正在费力地敲炉边的混凝上,以求弄到一点点钢筋。曾经带电的铁丝网也被村民剪掉了,透过瞭望哨被撬光了玻璃的窗户,他能看到监区里长疯了的野草。监区的电线杆被拉倒了,村民们把外面的水泥敲掉,把里面的钢筋拿去卖了。他经常作报告的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已是杂草丛生,礼堂顶上的瓦已经被揭光了,门、窗户也被拆得七零八落。唯一令他欣慰的是不远处,曾经布满硫黄灰的山坡有了绿色,那是当地人新栽的。
一路走着,他突然发现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而又陌生。每轮到他值班,他总是这样,到所有自己工作过的大队走一圈。天很蓝,阳光也很明媚柔和,只是,没人再叫他大队长,他再也没犯人可带,再没机会和那些飘忽不定的眼神较量。
值完班,他会回到交警队,在那里打零工并非只为挣钱。他喜欢和交警队的年轻人在一起,这让他觉得自己也还年轻。年轻的交警如果向他打听监狱里的事,他就会用缓慢低沉的声音跟他们聊聊监狱,聊聊犯人,聊聊硫黄矿,聊聊自己的经历。有时候,他似乎能在记忆中闻到那硫黄的味道,隐隐约约,突如其来。
(摘自《别处生活:20幅平民肖像》,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4月版,定价:32.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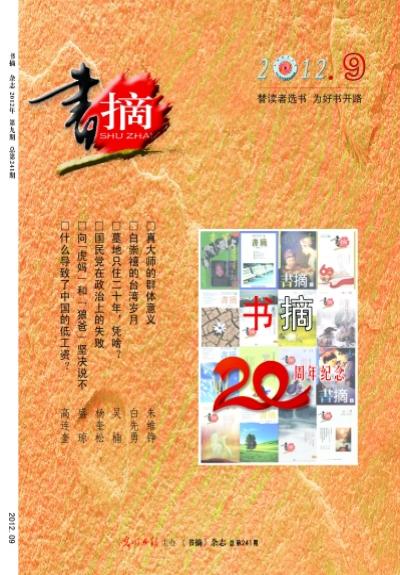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