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香烟软盒比硬盒贵;人们对时尚的追求往往带着宗教崇拜般的狂热;年轻人宁愿蜗居也要挤在大城市……究竟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要这么过?如果仅依赖经济学的理论,显然很难给出答案。但如果我们把这些现象放到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和生活方式中去解释,答案又如此简单。
在传统社会,身份、生活方式和消费结构之间,有着截然分明且近乎牢不可破的对应关系,你的父母是什么人,拥有哪些资源(土地、权力、官爵和专业),以什么为生,将直接决定你可以娶什么人为妻或嫁给什么人,住什么样的房子,甚至衣服的款式颜色,鞋尖有多长,发型和配饰,吃些什么,出门坐车、骑马还是步行,带不带武器,祭祖用什么仪式和祭品,说话的腔调等,几乎无所不包。
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大大松动了身份与消费的关系,而日益加速的消费内容变化也模糊了生活方式的边界,然而,尽管已不那么严格,消费行为的模式化仍是可以辨认的,并且对社会的消费形态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从一些标志性消费行为,如你在中国某小城镇见到有人买了部家用咖啡机,你仍可颇有把握地判断他的职业、地位、收入、社交圈和文化背景,并由此猜测他还会买些什么,他的客厅和厨房里大概还摆着些什么,甚至他会有怎样一位妻子等。
为何高档香烟软盒比硬盒贵
抽烟的朋友可能会注意到,在最贵的那些香烟中,软盒的居多,如中华烟, (多年前的行情)硬盒的48元,软盒的68~88元不等。为什么?
从技术上看,软盒容易压扁弄皱,由于封口撕破后无法关闭,烟还容易撒出来,缺点不少,唯一能想到的优点是,抽掉一半后放在口袋里没那么鼓;而制造成本上,软盒也比硬盒低。
我的解释是:软盒烟卖得贵,正是因为它的那些缺点,使得它可以成为区分身份的有效标识,而高档烟价格中的很大部分(个人认为大致是超出20元的那部分)所对应的商品,就是身份识别符号。
试想,如果你是一个整天干体力活的蓝领工人,或者是整天忙忙碌碌、跑来跑去的白领职员,你不得不随时把烟揣在兜里,你就很难保持烟盒的挺括整洁,你就不得不忍受断裂、压扁、皱巴巴甚至弄湿的香烟,除了一小撮以这种皱巴巴香烟为情趣的异类分子之外,多数人会将此视为不便且不愿忍受。
我们知道,制造身份符号的要点在于难以模仿,于是,“能保持软盒烟的挺括整洁”便成了身居高位或有闲阶级的标识,尽管这一符号远不如别墅名车那么显著有效,但因为它的廉价和高曝光率,还是颇受青睐。
类似的例子还有高跟鞋、拖地长裙、长指甲、很容易弄脏的白手套、难以维护的丝绸服装……(当然其中多半已经过时了)
那些兜售奢侈品的商家,绝不会宣传其产品简单易用,易于维护保养,这些优点是留给大众消费品的。
一个稍显复杂、我还不能肯定的例子是素食、节食和瘦身运动,干过体力活或其他辛苦工作的人可能会同意:在一天劳累之后,你是很难抵御一番畅饮和大快朵颐的,控制食欲、清淡饮食、素食、节食,这些对于工作繁忙的人,是很难做到的,相反,职场的压力和烦闷还经常导致贪食多吃,相比之下,不必工作的居家师奶和游手好闲的富家少爷小姐,则有很好的条件修身养性,或许这正在成为一个新符号。
后记
身份符号的要点在于防伪,要给模仿者制造障碍,所以一旦条件变化使得障碍不再难以逾越,这个符号就会被放弃。
40岁以上的人或许还记得,涤纶在20世纪70年代被尊称为“的确良”,比棉布高档,当时农产品价格普遍低于工业品。后来,全棉成为时尚,一方面因为棉布与涤纶的价格发生了逆转,同时也因为纯棉制品很难保持挺括整洁,这成了有效的模仿门槛。当全棉免烫技术普及之后,纯棉很快失去了其符号地位,接替者是古老的亚麻。
时尚,另一种宗教
时尚的生成和流行过程是宗教之外的又一个观念自组织的典范。从发生机制上看,它与宗教十分相似,所以,把时尚称作一种现代宗教,不算太离谱。
富与贫、贵与贱、博学与无知、高雅与粗鲁、悠闲与劳碌,人的这些差异,常常会影响他们在对消费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这种差别在某些方面——如服饰、住宅、随身物品、交通工具等——表现得特别明显,当这些差距逐渐拉开而变得易于辨认时,人们就会通过其中最明显的某几种差异来识别一个人的贫富等级、地位高低、教育程度,甚至生活经历和职业。
而一旦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常常又会反过来刻意地明确这些差异,状况相近的人们会有意识地调整他们的消费品和生活方式,不约而同地向那些最易于识别的款式和品质靠拢聚集,最终,整个社会围绕着几种典型消费品,自动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栅格状结构,这一分层化的自组织过程就叫时尚。
如果仅仅看到上面的分层结构,那就没有抓住时尚的精妙之处,时尚之所以如此激动人心,重要的是它的结构是在不断运动变化之中保持的。当层次结构日益显现或者已然明朗时,那些面临着为选择某个将要厕身其中的阶层而作决定的人,常常会将目光投向他们的“上”方,选择一个包括了许多条件优于自己的人的阶层。
这种向上靠的倾向使得每个阶层中那些财富地位等条件最优的人的生活方式成为被模仿的对象。然而,一旦这些被模仿对象意识到与自己同处一个阶层的,多数是条件比自己差的人,这一发现会让他们感到恼火。
为了摆脱与乡巴佬为伍的屈辱感,这些被模仿者只好不断地花样翻新,以便与模仿者拉开距离,而后者一旦发现新花样已经成为时尚,总是精神抖擞地奋起直追,就在这你追我赶之中,时尚的浪潮涌动起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潮涌中,追逐的双方都兴致盎然,乐此不疲,劲头丝毫不亚于热忱的宗教信徒。每一波时尚的浪潮,都将一组关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新观念,从最初的一小撮人那里,逐级向下,传播到几个阶层甚至整个社会。
正如权力在宗教传播中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商业力量在时尚流行中——也因为同样的缘故——起到了类似的也许是大得多的推动作用。消费品的经营者首先去努力发现、识别出(甚至制造出)那些最能代表身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产品加以明确化、符号化,然后向那些热衷于向上靠的时尚追逐者们推销这些符号;等这一波浪潮渐趋平静,他们又转过头来,告诉那些“领潮者”,这些旧东西已经显得太俗气了,不再配得上你的高贵身份,该换换花样了,于是另一波浪潮开始了。
后记
时尚的模仿与反模仿追逐游戏,有点像轮番升级的军备竞赛,游戏中的人们必须不断奔跑才能留在原地,有趣的是,在某些时尚元素上,追逐会沿着一个圈子不断循环,如流行色、简与繁、紧与松等。
为何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里挤
在经历了年初以来的又一轮房价大涨之后,政策当局再次宣示了遏制房价的态度,最近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推动城镇和中小城市发展的战略方向,该战略旨在扭转过度向大城市集中的人口分布结构,以缓解一线城市所面临的日益沉重的住宅需求压力。
这一政策转变,把一个多年前曾几番争议的老话题又提上了桌面: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究竟应该面向高度密集的超级都市区?还是稀疏松散的中小城市网络?争论未曾有结果,政府则似乎一直倾向于城镇化,而与此同时,超级都市却早已不由分说地涌现了出来。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争,问错了问题,正确的问题是:按我们的制度背景、资源禀赋和市场特征,未来的人口分布结构将会如何演变?从已经表现出的趋势看,方向无疑是超级都市,如果这一趋势背后有着强大而固有的内在动力,凭几项政策和规划是无法扭转的。
关于蚁族的报道和正在热播的《蜗居》,都生动地展示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为了留在大城市,愿意承受何等的艰辛与压力,这一强烈倾向的背后,必定有着某种共同的动机。
对于大城市的优势,经济学家已有了很多论述。斯密指出,细致的分工依赖于密集人口,只会做一种糕点的面包师,无论手艺何等高明,在小镇上是找不到工作的,而在大城市却很可能享受五星级酒店的高薪。越是高级的专业化人力资本,越需要在高度密集市场上就近兜售,以实现其价值,设备和技术等非人力生产资本也一样。
生产如此,消费也是如此,越是特殊的偏好,越是难以在人口稀疏的乡镇得到满足,若一种商品的目标消费群窄于0.1%,便不可能在只有几千人的小镇设立零售店或代理商。有形商品的问题还能借物流业的发达而得到改善,服务业则更难办,在小镇上你找不到好的电影院、风味特殊的餐馆,大明星也不会来这里走穴。
更要命的是,许多消费必须由趣味相投者共同进行,或需要看得懂的观众在场才有意义。在小镇上,你那件手缝西装会被叫做皱巴巴的针脚不齐的外套;作为球迷,你找不到人一起观球畅饮欢呼;作为发烧友,没人听你吹嘘那根能收上千个节目的天线;即便在数十万人的中型城市,你也难以在每个周末凑齐一桌人打桥牌。 密集人口在实现人力资本价值和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上的优势,构成了人们向大城市聚集的基本动力,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在现代社会,都市已成为人们价值追求和地位提升道路上的一座灯塔,那些力争上进、不甘寂寞与落伍的有志青年,很少能在大城市以外找到施展这一追求的舞台。
人的消费不是随机组合的,偏好和价值观也不是独立散布的,消费行为和驱动它的偏好乃至价值观,被组合在所谓生活方式的稳定结构之中,这些生活方式乃是人群经由模仿和协同而达致的“聚点”。
当一个年轻人为自己的未来生活作筹划时,实际上是在进行社会角色自我定位:首先选择一个竞技场,然后考虑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一旦他朝选定的方向迈出脚步,生活目标便被锁定在一系列逐级爬升的模式之中。
问题是,越是高阶的生活方式,越是小众化,这意味着只能在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才可能存在,只有大量人口中才能找出足够多的同类小众,使得此种生活方式下的消费达到规模经济。对于那些志存高远的青年,即便在眼下可以忍受一个很低的起点,但他们心目中的那个梯子必须有足够多的梯级,可以通达他们所憧憬的高度。显然,这样的梯子在乡村是找不到的。
正是这个梯子,驱使大批青年甘愿蚁聚或蜗居于都市,他们本可在小城市谋得不错的差事,并享受低得多的生活成本,更好的交通,更好的空气,更少的生活压力。他们并没有错,即便最终他们在那个梯子上爬得并不高,但年轻人总是会有梦想。
(摘自《自私的皮球:我们的日子为什么是这样过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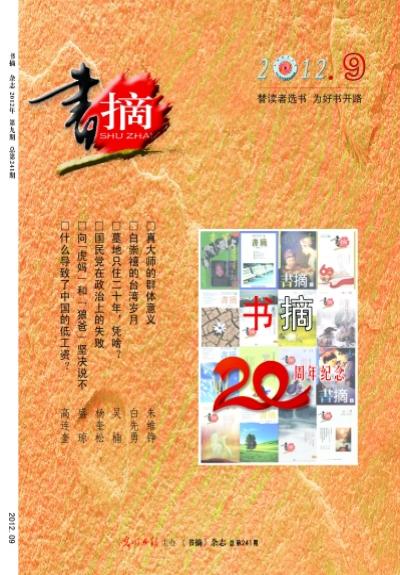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