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坚耳朵里塞着助听器,弱听,让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在他的耳朵里都变得安静了很多。
于坚从云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现在仍然是云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辑,他就在这个芝麻绿豆点的职务上工作至今,和他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歌姿态南辕北辙。
于坚拿过鲁迅文学奖、台湾《联合报》新诗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诗人奖等重要奖项,但也同样引起过各种争论。
生活在别处的仇恨
河西:过量的链霉素注射导致弱听,从此您再也听不到蚊子、雨滴和落叶的声音,这样的世界变得安静,但同时是否也对声音变得非常敏感?
于坚:这个弱听是因为5岁的时候打链霉素过量,落下了一点毛病,但是影响还不算太大,更多的影响来自工厂的生活。文革开始后,1970年我上了一年初中就被国家分到工厂,我向单位请求分配一个噪音低的车间,结果是故意分到一个声音非常响的车间,说是听不见正好。我更喜欢用眼睛来观察,我的眼睛非常犀利,瞟一眼就知道了。从小养成的习惯,和世界的关系是主要是看的关系。我喜欢虚构声音,我曾经发表文章反对现在盛行的诗朗诵,而我的诗却非常注重韵律感。
河西:这种弱听也让您感受到一种歧视?
于坚:中国这样的社会,从我少年时代到现在,是非常不正常的,整个社会的方向就是“维新”、“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是什么?是养生还是反生,不考虑,许多地方现代化完工了,生活世界也完蛋了,枯燥乏味,瞧瞧那些荒凉的小区,只有些商品房。说远一点,20世纪,西方世界流行的是“一种反生活的潮流”,崇拜“生活在别处”。中国深受这种思潮影响。革命说到底,是对生活世界的革命。人们要从旧的社会跨入新的社会,对于所有不符合新人标准的人,有一种潜在的歧视态度。我童年、少年时代深感压力。新人必须德智体全面合格,而我永远不会合格,不只是身体缺陷了。身体的缺陷压力恰恰使我在新人中成为一个另类。1977年恢复高考,我第一届就考取了,通知书都拿到了,可是因为我的听力原因体检没有通过。我的耳朵不是聋,而是声音小一些我会听不清楚,绝对不影响上课。解释是没用的。我考大学考了三次,前两次都是因为体检不过关,后来第三次又考,没办法了,我只好请一个和我长得有点像的朋友,代替我去体检耳朵,这样才蒙混过关的。
文革时候所有学校关门,最后一课我记得只有一本书,就是毛泽东语录。在工厂的十年中,我靠自学完成了整个教育。所以我考进大学以后,觉得都不需要上这个大学了,我只是为了获得一个文凭而已。中文系开的必读书目,我翻了一下,我全都看过,而且都可以说翻烂了。高考对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
河西:16岁以后当过铆工,电焊工、搬运工、宣传干事、农场工人,一方面对您的听力也有影响,另一方面您参加高考是不是也是想要改变现状?
于坚:对我们这代人来说,高考绝对是改变我们的命运最重要的机遇。我1977年考取没录取,1978年生病没考,1979年又考取没去,直到1980年才正式录取。在这四年中,我们工厂里,大部分一起进厂的青工都考取大学走掉了,剩下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大学始终是一个情结,就是一定要在学校里面完成正常的学业。被中断学习流放在工厂里是不正常的状况。工厂带给了影响我一生的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也有很多美好的时光,但是总的来说,我仍然要说它是一种噩梦般的经历。实在太恐怖了!我毕业以后曾经再回工厂,那车间我一秒钟都不能忍受。我不知道我怎么能在那里待上十年。那个时候的工厂不像现在,绝对是西方前工业时代的工厂模式,非常原始、粗糙,笨重。工厂里的劳动强度太大了,名义上是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在文革时期,是以政治口号来要求工人的,经常加班到天亮。
70年代的地下哲学
河西:哲学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于坚:我对哲学的兴趣不是从大学开始的,实际上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民间有很多地下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比我们年纪大的红卫兵知青,我们算是红小兵。他们学的不是官方规定的马列主义选本,而是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原著。受毛泽东的影响,喜欢哲学在当时青年中是一种风气。那时候我就比较喜欢哲学,当时我们基本读不到西方哲学著作,只能阅读马恩原著,但是由于马恩的哲学体系深深植根于西方哲学传统,所以它的许多思想与存在主义等西方思潮都是有关系的,只是你是否能看得出来而已。我早期的哲学基础是从马克思、列宁的那些原著中打下的,那时候还细读过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的文艺理论著作。后来到大学时代,西方哲学真正进来的时候,就觉悟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研究的是世界背后存在着的某种规律性的东西,历史的发展是可以总结出规律来的。但是到了萨特的存在主义,就变成了存在决定本质,和本质决定存在是两回事。可是最基本的东西,什么是存在,什么是本质,我还是从马克思学说里知道的。
河西:既然这么喜欢哲学,20岁又是怎么开始写诗的?
于坚:在中国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任何一种知识的传播都不是西方式的,不会那么界限分明。不是你喜欢哲学就只看哲学书籍。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认为,写诗要有非常强大的哲学背景,说到底,写诗表达的也是作家对世界的一种理解。
我上学的时候非常喜欢老子。我们有几个朋友经常在一起讨论《道德经》。那时候哲学课是不讲老子这些人的,老子对我的影响和古代知识分子不同,他不是主流思想而是另类,是蒙昧时代的光芒。后来我读到海德格尔或维特根斯坦时,感觉海德格尔或维特根斯坦有时候就像在用德语或英语在重述《道德经》,有很多可以通的东西。老子的思想中有很多深刻的关于存在的论述,但你不能说他是存在主义,但是他可以启发你,让你明白存在主义在说什么。
我的诗歌写作一定有哲学的思考在里面。
地下诗刊《他们》
河西:韩东说你们相识是因为封新城当时办的杂志《同代》?
于坚:甘肃兰州的《飞天》有一个非常好的编辑叫张书绅,他觉得大学生诗歌很有活力,就在《飞天》上辟了一个大学生诗歌专栏:“大学生诗苑”。我们当时的诗歌作品基本上只能在自己印的民间诗歌刊物上发表,很难进入官方刊物,只有他那个地方愿意接纳,所以全国在校大学生基本上都往那里投稿,那里立刻成为高校大学生写作园地,一面旗帜。我的诗歌比较另类,官方杂志很难发表,许多都是在《飞天》上。发的时候会把我们的学校班级写上,比如写“云南大学中文系某某级于坚”,“山东大学哲学系某某级韩东”,这就是通讯地址。我们一看,这家伙诗写得不错,就按照这个地址联系。封新城在《飞天》上看到我的诗,就写信给我,说他要办一份民刊《同代》,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韩东。《同代》给我寄了几份,是一份印刷非常粗糙的刊物,用蜡版刻的,上面发了我的诗、海子的诗,他的《亚洲铜》就首发在上面。我看了韩东的诗,很喜欢,觉得他对诗的想法和我有共同之处,就开始通信。然后我们开始自己办《他们》。
我记得当时每期每个人出96元钱,在当时可不得了。我当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六七元左右。先是韩东编一期,我编一期,轮流编。结果我们在选稿上就发生分歧。我们当时有分歧就直截了当地写长信表达看法。韩东寄来的一大摞稿子,我不喜欢,他又很坚持,我就把稿子退回去了,没编。后来基本上都是韩东编的,可能有四五期,然后是朱文编。
河西:到第九期的时候就停了?
于坚:因为我们都被关部门关照过,因为是地下刊物。第一期出来后在全国就引起了极大反响,我和韩东被邀请参加当时《诗刊》的青春诗会就是因为《他们》的影响力。那时候地下刊物的影响力太大了,比公开刊物大。那是一个诗歌的黄金年代,1986年的时候《诗刊》的主编是刘湛秋先生,老一代的诗人,他的思想非常解放,和后来平庸的《诗刊》不是一回事。
《零档案》:诗歌实验
河西:上世纪90年代后,您曾与先锋戏剧导演牟森合作了《零档案》和《关于<彼岸>的汉语语法讨论》,您怎么开始和他的戏剧实验合作的?
于坚: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特殊的文化氛围,先锋诗人和先锋戏剧家大家常在一起玩,至少是听过名字。牟森和我去北京与他合作之前就到过昆明,那时他还在西藏话剧团。80年代有过一次西藏热,马原等等有一批人,大学毕业后去了西藏。他到昆明来玩,和诗人一起吃饭,大家都认识。后来,北京电影学院请牟森来给那些没考上演员班的学生上课,这个班快结束的时候,要来个毕业表演,他们想把高行健的《彼岸》排成一个戏。吴文光和他熟,吴文光原来住在尚义街6号,在昆明电视台当编导,是我的朋友。他后来去北京,他拍的纪录片《流浪北京》中,牟森也是其中一个采访对象。
吴文光带我去看牟森的戏,一起吃饭聊天,然后我就说,高行健这种剧我认为很简单,什么彼岸有花、草,很矫情。对这种乌托邦彼岸应该有一个解构。牟森听了觉得很好,问我能不能写一个和高行健的《彼岸》平行演出。我回去,住在《工人日报》的招待所里写了两天,写了一个诗剧《关于??彼岸??的一次汉语语法讨论》,写完了我在全体演员的面前朗诵了一遍,牟森非常喜欢。就排了这个戏,以我的为主,高行健的剧本没剩下几句话。
河西:《零档案》呢?演出后的效果和您最初想象的是否一样?
于坚:《零档案》1992年就写好了,1993年我才去的北京。那时《零档案》这种诗不可能发表。我们那时候写诗不是说拿去发表,而是自己打印,打印个十几本,然后寄给自己的朋友。牟森看了之后产生了要把它搬上舞台的念头,我就在上面写了:“同意牟森上演。”
我没想过《零档案》会变成戏剧。我看了他的戏剧,我觉得他改得非常有力量。在最初的时候,我和他交谈过,我和他也谈过我以前在工厂的生活经历,对他也有一些启发。
我在现场看《零档案》感觉很暴力。那些电焊机在舞台上直接工作,电光闪闪,眼睛受不了。而牟森就是要这种暴力。血肉的生命,在强大的机器面前,显得那么弱小。它不断地让我想起我的少年时代,演员想说话,总是不断地被后面的切割声打断,那种电焊的声音把你强行切断,而演员的独白变成一种反抗。蒋樾在一个小时二十分钟里,一直在电焊,把整个舞台用钢筋一根一根焊起来,到最后整个舞台全是钢筋,又把几箱苹果一个个用钢筋插在钢筋尖上,很有一些象征性。我的诗是用朗诵社论的声音大声朗诵。暗藏在诗中的一个声部被敞开了,出乎我预料。
河西:十多年前你就拍摄过一部以滇越铁路为题材的纪录片——《来自1910年的列车》,您还说想要拍一部诗歌电视,这方面的工作后来有没有继续下去?
于坚:那时吴文光在昆明电视台拍专题片,我们觉得这挺好玩。1990年,突然有个机会可以给我一台机器,让我们几个人免费吃住,给他们拍纪录片,于是我拍了《来自1910年的列车》,5集,每集30分钟,拍完了,结果让我们拍纪录片的那个人却从此再无音讯,带子也不知所终。过了十年,我还在想这个题材,我想自己拍,于是我就买了一台机器。以前的机器太贵了,现在每个人都能有机器,一台摄像机不过是一只笔。这也是一个民主化的表现。后来我重新去拍了这个车站。
我写作写了十年,文革结束后开始投稿,经常收到退稿信,发表太困难了。经常退稿信上写着:继续努力吧。而拍片子的经历正好相反,太容易了。我朋友跟我说阿姆斯特丹有个纪录片电影节,地址给我,我按照地址寄过去,就入围最高奖银狼奖单元。600个片子只入围五个。我写作这么多年,突然发觉拍片子要成功原来这么容易!当然,我觉得写作的功底对于你拍好纪录片非常重要,拍纪录片其实就是写作,必须要有最基本的文学功底。
文字、作品与作家
河西:有人提出要恢复繁体字,他认为电脑打字的时候,拼音都是一样的。您怎么看?
于坚: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还是觉得恢复比较好。性灵的灵字,旧体是“靈”,新体“灵”,差别不是笔画的差别,而是语言哲学上的差别。灵感的灵被简化为一团虚无之火。而古代的靈的上面是雨、中间是三张口、下面是“巫”字。这是说一个巫师在求雨,巫师得有三张嘴。巫师是最初的诗人,屈原就是个巫师,他的字不是叫靈均吗。灵如果和巫没有关系就不是靈了,巫不是个贬义词,以前在中国文化中,巫的地位很高,他们既召唤鬼神,又给部落的酋长出主意,他们被认为能通靈。这不是个繁不繁的问题,而是恢复我们对汉字本来的体验。
河西:您怎么看您自己的这些长诗?
于坚:我们这一代自觉与文学发生关系的诗人都是理想主义的诗人。我的梦想是写出不朽的作品。这激情至今仍充满我的心中。这个时代可以通过写作来获得其他利益,但你必须保持距离。实际上温饱问题我早就解决了,我大学毕业被国家分到文联当编辑,文联工资低,但时间多,不用坐班。我不需要考虑温饱的问题,我对物质生活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我不太明白,一个作家你开那宝马轿车有什么意思?难道作家的价值是和银行家一样是因为钱多?怪事了!我们的梦想就是要写出真正牛逼的文学。我认为作为一个诗人,朝这个方向努力就一定要能够驾驭长诗,这是对一个写作者专业性的巨大考验,我觉得不能回避。但是我不是说我一定要写出怎么样的长诗来,这有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河西:您写诗一方面给您带来了很高的声誉,另一方面会不会也有一些麻烦,有人觉得您很另类?
于坚:我在编一本《云南文艺评论》的刊物,一年四期,基本上是两个编辑轮流编,一个主编,负责组稿、发稿、印刷、开稿费、邮寄等等。如果你在单位里没有什么野心,不想在单位里图谋个什么一官半职,他们也就不注意你。实际上我很长时间一直是被单位边缘化的一个人,他们觉得这个人可以忽略不计。
这实际上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帮助,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写什么。可能是最近十年才慢慢知道一点,他们不知道也是因为傲慢,认为主流文化之外的东西都不值一提。
河西:郭沫若号称平均下来每天写三千多字,是不是用毛笔来写,有的人也能写得很快?
于坚:他可能从来不修改,中国作家老以写得多写得快为荣。我认为作品要在修改中完成,第一次的灵感是靠不住的。我不认为写作是胸有成竹的事。有的作家以为可以一气呵成,年轻的时候也许是这样,但是后来我自觉反对这种写作。我觉得一气呵成的一定是陈词滥调,只是你当时没有发现而已。你一定要在写作中另辟蹊径,把你潜意识中要说的慢慢地表达出来。一气呵成是对写作不负责任的表现,这种作家太多。有点小聪明小才气,比如海子,他的诗歌并没有严密认真的思考。才气不足为道,谁都有点才气。
中国作家是“一本书主义”,写了一本成名作,然后这个作者就消失了,不断地出现在各种会议上。这种作家太多了,狗屎一样!包括新潮美术,上世纪80年代我认识的一些艺术家现在都是千万亿万的富翁,现在发现他们简直是文盲,很难想象乔伊斯、巴尔蒂斯这样的人物功成名就就天天打扑克。这在中国文化中是普遍现象。所以许多曾经的先锋作家迅速陈旧,连和年轻一代对话的资格都没有!他们的写作不是道成肉身,而是富起来的终南捷径。
(摘自《革命的标记——今日先锋访谈录》,三联书店2011年9月版,定价:4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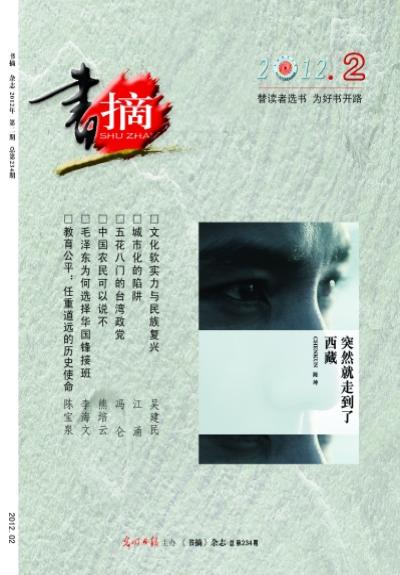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