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的出版
听沈昌文先生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有人动议恢复三联书店,其中也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同意。既然有领导同志,那就不只是动议了,还能领会出“要求”甚至“指示”的意思来。
即便如此,事情也不容易。终成正果已是几年之后。
1986年元旦,三联书店正式恢复、挂牌。当时,三联书店的不少前辈人物(所谓“老三联”)都到了退休年龄,只能发挥余热了。于是,属于“新三联”的沈公受命上任,就职总经理,负责主持三联书店的工作。
初任老总,沈公遇到不少问题,除了开办费仅30万元的杯水车薪之窘,出书方向也是大问题。当时,出版业实行专业分工体制。比如说,在北京,文学类的书只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美术书只能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在这种情况下,从名称上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不具有任何专业色彩,出什么书合适?没有现成的规定。
这是难处,也是机会。拿出点文化智慧,就会有腾挪空间。
沈公提出,出版杨绛的《洗澡》,立即引来质疑。有人说,《洗澡》是小说,小说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三联该出什么书,当时确实费琢磨。沈公说,好在路总是人走出来的,而且最主要的是,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形势。这种形势的一个特点是,尽管大的体制还没有变,但是允许人们想一点招了。他和同事想到了一个词:文化。
沈公问“上面”:我们不出小说,出文化类的书可不可以? “上面”答复说,可以。
于是,三联把杨绛的小说定义为“有深刻文化内涵的文学作品”,然后再问可不可以出。
“上面”说,当然可以出,有文化内涵的书,适合你们三联书店出。
这一下,不仅出了想出的书,而且把多年沿袭的所谓专业分工体制也部分地打破了。
XO当黄酒喝
三联书店恢复之初,改革开放已持续数年。出版界有了利用海外文化资源的条件。沈公昌文先生干脆把重点放在海外。标榜的口号是,学习周恩来总理当年广泛团结海内外作家、搞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经验。
为开辟海外文化资源,出版海外文化类的书,沈公到香港去发掘资源。香港三联书店的朋友听说总店的老总来了,设宴招待,喝酒助兴,摆出XO。
沈公祖籍宁波,很熟悉绍兴黄酒,问:你这个酒什么牌子啊?朋友告是XO。一问一答,沈公确认,这一定是XO牌的绍兴黄酒,遂放心畅饮,居然喝下一瓶。然后,就醉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如今说及,沈公笑言:“这就是我这土老帽儿第一次到香港去的悲惨经历啊。”
一瓶XO,打开了三联利用海外文化资源的大门。沈公得以引进蔡志忠的漫画。这是他很得意的一件事情。此前,其接触到的漫画有叶浅予的,有丁聪的,等等。其中比较进步的,很多是讽刺蒋介石的作品,表达一种政治立场。蔡氏的漫画却是另一种,用漫画的形式传播知识,而且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沈公评价道:难能可贵。
“文革”结束后,很多年轻人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完全无知,不知道中国文化的来源和老祖宗了。沈公认为,出蔡志忠的书,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当即拍板引进。
《孔子说》、《孟子说》、《庄子说》等书出版后,很多中学生、大学生致信沈公,说他们是看了蔡志忠的漫画以后,才知道孔子说了什么,孟子说了什么,庄子说了什么,以及那些古训的真实含义。
出版界说起这桩事,有“沈公拣了一棵菜(蔡)”的段子。后来三联出版金庸的书,又被说成“拣了一块金”。
言及此,沈公说:现在讲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很多,成了时髦。比如于丹等等。我冒昧地说一句:在帮助大家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方面,蔡志忠的成就比于丹大,收入比于丹少。
《情爱论》的出版
就外语说,沈公昌文是学俄语出身,俄语书看得很顺溜。其留心俄国问题时,留意过一本俄语书,叫《情爱论》。
沈公总结过一个社会现象,每当一个社会要大步向前,要突破约束,要冲破思想藩篱,总是女性走在男士们前面,因为她们所受到的社会压迫要比男人多出一层来。她们比男士们呼吸得更不顺畅,比男士们多出一重窒息的感觉。
《情爱论》出版于东欧事变之后。沈公认为,该书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谈论爱情问题,提出了惊人观点。书中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讲任何问题都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惟独讲到爱情问题的时候,不讲唯物主义了,而是讲唯心主义。爱情是要有物质基础的,所以肉欲问题是不能回避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要回避这个问题呢?只需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正面的、好的解释就行了嘛。《情爱论》就对此问题做了很好的解释。
当时的文化气氛,还没有今天这样宽容。为书能出版,沈公坦承,“作了很多孽”,主要是作删节。他对《情爱论》责任编辑吴彬说,《情爱论》的基本观点当然很好,可还是要求求你帮帮我的忙,把书里边那些“比较恶心的”段落删掉。于是,就缺少了原版书的一些内容。
回忆当初,沈公说,我们讲唯物主义,从理论上承认肉欲的自然性,但是在实际上,已经把关于肉欲的具体段落删光了。我当然并不愿意这样做,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现在的环境,真是好出太多了,连木子美都出来了嘛。我曾经对木子美说,你现在讲的那些事情,那些话,《情爱论》很多年以前就在原则上提到过了。
沈公送书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个暑天,一位朋友领着沈昌文先生到家里来。
那时,《读书》杂志在知识分子心中何等地位?总觉得这杂志的主编是个大人物。迎客进门时心想:一个平常读者,见他就这么容易么?
那天,沈公边吃西瓜边聊天,时有玩笑,适度,自然。虽是初见,却不给人陌生感,更没有某某驾到的架势。完全像个邻居串门,随和,家常,善意十足。说说最近有什么好书,好文章,吃点水果,告辞,又去忙他的事了。
忽忽20年过去,与沈公交往渐多,对他的平民感、平常心有了更多体验。比如,见面时说起一本书,他知道我没有,又想看,就会想方设法再弄一本。实在弄不来,他会费点周折复印一本,用牛皮纸包好,或骑车来,或走路至,放在我所在单位的收发室。这些年来,经这样中转而得的沈公赠书总有几十本。
某年临近春节,是个雪天,沈公又来送书,我刚好走到,在大门口碰上。接过书,内心感动得不行,他神色一如既往。这算什么?一本书嘛。聊上几句,我欲留,他要走。长年里,他要见的人很多,想见他的人更多,日程总是很满,当然该让他走。
看着沈公摇晃于雪中的背影,想起传说中季羡林先生在北大帮新生看行李的事,想到一个词:古道热肠。季先生看行李大概不会重复多次,沈公送书可就是家常便饭了。他认识多少人啊,多少喜欢书的朋友啊。相信享受过沈公上门专递服务的朋友不在少数。
有些年,遇有不好买大家又都想看的书,沈公会复印多本,放进双肩背包,骑车出门满北京城转,或是专程送到朋友家门,或在餐叙时掏出来,赠人惊喜。
沈公广交天下名流,遍识各路神仙,时常高朋满座,为他们备点书,自在情理中。对一个完全属于芸芸众生的平常后辈,何必劳神费心惦记着送书?这样的念头,模模糊糊地转悠过,又觉得不该去想。
一个老人,见一个孩子饿了,给他馒头,无非是不忍看他饿着。非去琢磨为什么,未免有失厚道。
有这样一本书
为沈昌文先生记录其口述历史,说到一本书,是他在“文革”中与史枚先生等人合编而成。该书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作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49-l966.5)》,油印,孤本。编者落款:遵义兵团韶山战斗组、孺子牛战斗组。
沈公善解人意,知我想看,遂复制一本,慨然相赠。
粗略翻阅,见到正史里难得讲到的一些出版掌故,很有意思。
1951年6月至7月,胡乔木名著《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当年10月18日,胡乔木就该书的出版致信该社,建议出版物上的社名不用毛泽东的题字。信中说:“出版社用毛主席题字实在不好。”“我坚决主张干脆一律不用”。11月19日,该社通知全国各人民出版社,“一律不在书上印毛主席的题字”。11月28日,又通知全国新华书店也一律不准在印刷品中使用毛泽东的题字。同时,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该社出版物“继续保留生活书店等三家的招牌字”。
1959年,陈伯达提出文化上要“厚今薄古”。王子野说:古今都是钢板,厚薄都有用。
同年,陈原传达邓小平提出的对有问题的翻译书稿的处理原则:各取所需,能删不能改。
周扬主张“出版社要为作家服务”。1962年,王子野、范用等谋划成立了“作家服务组”,把冯友兰、冯定、朱光潜等数百人列为服务对象,为他们提供购书证,“要买什么书给什么书。有些书没有了,也要竭力为他们寻找,送货上门,还可以不付书款,欠款也不催”。
1963年召开出版工作会议,周扬说:“政治第一,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多出政治书籍。”会后,林默涵、陈原等起草了一个报告,提出“要注意出版一些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内容无害,而在学术上或艺术上有一定价值的东西”。
同年,刘少奇说,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就要了解它。既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也要读读现代修正主义者的著作,这叫 “比较学习法”。大概与这一主张有关,“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办公室”,推动出版了“灰皮书”、“黄皮书”系列,在知识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沈公当年参与其事,今日忆及,仍有快意。
随沈公买折扣书
为《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的增订,与传主和责任编辑约好,在蓝旗营的万圣书园见面,苏里兄也参加。四人中,沈公路最远,到得最早。本以为自己是提前到场,进门时,见沈公已买下一套《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价钱打五折。
见此煌煌四卷,自是眼馋。一问,书还有,也要了一套。沈公说:“你对降价书也感兴趣呀,那我带你再去两家,就在附近。”
随其出门,东行。过了隔壁,沈公指着一个牌子说:“这家店里边有个‘小平的店’,进去就看见了。都是旧书,都有折扣。再往前,这家超市里也有一家。这两家我都看过了,都很好玩,我都有收获。”
依沈公指点,进得超市,直奔书店。见有“五元区”、“十元区”、“二十元区”及“七折区”、“八五折区”,不仅便宜,值得一买的也不少。
那套新版的剑桥中国史,堂皇厚重,成排站在“八五折区”。对衷心喜爱者,这实在是不算少的优惠。在万圣书园,最高级别的“荣誉会员”也不过享受这样的折扣。
拎着一大包书,进了“小平的店”,淘到一本施蛰存先生著的《昭苏日记/闲寂日记》。封面古朴雅致,内文用影印与排印对照,板式古意盎然。信手一翻,128页,见施先生先卖书再买书的一段记录。
(摘自《远古的纸草》,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2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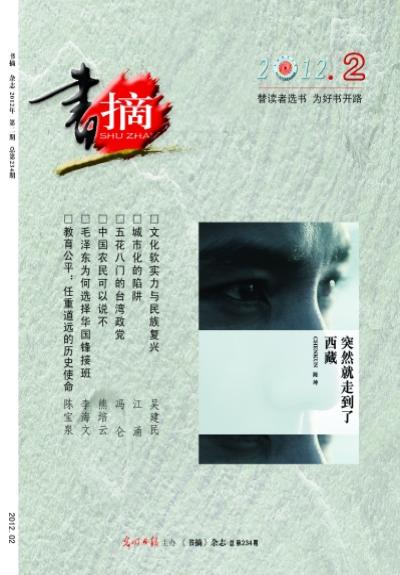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