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水词人
苦水,先师顾随先生的早期别署。那时北京(一度称北平)的文人学子,无人不知“苦水词人”的名气。他以词曲最为擅场,但诗也毫不逊色。他为何自署“苦水”?自然寓意有在,但我揣度这和燕京大学有关联——他在燕大教“词选”课,燕大的文件皆是中英文并列,于是先生的名字便写作Ku Sui(旧拼法,不作Gu Shui)。这个发音就很像“苦水”了。
苦水先生是够苦的。他家人口多,薪水薄,生活清苦。为了养家,须在几个高校兼课,奔走不停。
大约就是因此之故,后来又号“倦驼”。骆驼在沙漠中行走长途,未闻其“倦”,而先生以倦行之驼自喻,其“苦”亦可知矣。
记得先生的一首绝句写道:
煨成薯芋如软玉,嚼来萝卜似甜冰。
半年不吃肉边菜——惭愧西山入定僧。
他不说“菜边肉”,而掉转过来说“肉边菜”,这滋味浅人是难知的:盖清贫之家不能常有肉吃,馋了也只买一小块炖炖,专为烩白菜吃,取那点儿肉味而已。故仍以菜为主,肉只是个“配角”,此“肉边菜”之真谛也。
每诵这样的貌似幽默的句子,辄深感慨:做个高级知识分子如先生者,也如此不易为生。
我平生受知于先辈诗家学者,屈指可数十几位,而唯独先生对我的垂青异乎寻常。他写信给友人时,曾说有周玉言(拙字)者是我平生得意弟子。并注明云:他中外文皆通,文言白话都好……
沦陷了,精神痛苦已极,我的母校被日寇封闭解散了,我在津沽老家“暗室”遁居,逃避汉奸的搜索。每日写些忧愤激烈的斥敌爱国的诗词。因与先生鱼雁唱和,竟蒙不弃,有信去必即赐复——那一笔美极的行草书已令人爱不释手,再加上时有佳句录示,简直是我的“超生福音”,冉冉而降!从此,与他结为超越师生的深交。
先师的手迹,我珍如至宝——很多是他的诗词、论文的草稿,至为名贵。不知何故,搬家之后,一批册页、书画、信札,皆觅之不见了(另有多篇学术论文手稿,被津中某人骗去不知下落)。这是我的最痛心的一件不幸和灾难。
先生晚期又号“糟堂”。
他也是西语系出身,但课堂讲授,讲到外文的诗,与中华的相较,时有妙语,足以解颐。
如有一次他说:西洋诗为表感情激动,一开头常就是一个Oh!这一Oh,可就糟了!——逗得学生大笑。其意是说:中国诗人是不采用这种浅露乏味的“方式”的。那味儿很不相同。
又曾讲,西方讲文学重在“描写”,即所谓description(细节刻画,琐琐外貌……),这就又与中国两途,中国高级文学不讲外表形似,专讲神韵丰采……我这样写成“文字”,就没趣了,在他当时“上堂说法”,那真是音容笑貌,精彩百出。
名师上堂,正如名角登场,你没见过那种精气神,一招一式之美、一音一字之妙,只看“书面记录”和“回忆录”,那又有什么用?真是百般徒唤奈何了。
名师已往,永怀难忘。他在上世纪40年代末,大病一场,病后调职津门,我亦回京。但未获一面,先生辞世。此前他百计想调我到津,与他合作一桩胜业(虽未明言,料是研著一部中国诗论大系的巨制)。
此愿来酬,先生长往矣。
先师之逝,未免太早了些 (只刚交一九六〇之年),以致大业中折,难以为继。可是又一转念,“文革”一起,把先生家抄得片纸不存。他若还在,岂不太觉难过?早逝几年,又是有幸了。
先生进入新社会后精神焕发,诗词一改前境,皆奋进之壮语。最幼女公子入党,喜心翻倒,特意来信告知于我。
老教授一腔热血,满腹经纶,文采过人,书法绝代!这是真正的国宝。
青眼相招感厚知
1947年秋,重返燕园,仍在西语系读书。其时钱锺书先生正在清华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燕京、清华两名校相距“咫尺”。燕京大学北部包括了朗润园,其命名是与清华对仗之意,盖取唐太宗《圣教序》称赞玄奘法师“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也。
我回到燕大,中隔六年之久,学校也遭受了巨创,旧识师生寥寥无几,中文系的阎简弼先生,不拿我当“学生”,相见则论学问,他向我推荐钱先生的《谈艺录》(开明书店版)。
我从吴允曾兄(哲学系,为教师)借得此书。这是我始“识”钱先生的因缘,读之深为得味,喜欢这种治学之路数。
后来,又读到他的《围城》。对此小说,我不妨直言,心里并不怎么推崇,它的气味流露出笔致心境的聪颖轻巧——不少读者最赏它的“机警”、“俏皮”、“幽默”……的语文风格,其实这并非钱先生的真高处,甚至可说是一种“短处”——它吸引一部分读者的兴趣与赏爱,却难以属于伟大文学创作的等级。
又后来,友人帮助去听了一次钱先生的课堂讲授,他一口纯正的“英国英语”(有别于“美国英语”),讲述潇洒,风致不凡,不愧为名教授,深得学生们的敬佩。
但我们的交往并非师生之谊,却带有一点“传奇”的色彩。
大约是1948年之秋,因读雪莱的《西风颂》,一时兴起,即以《楚辞》“骚体”译为汉诗。友人见而赏之,就拿给钱先生看,从此得到了他的青目。记得一封惠札有云(大意):得一英才如此,北来为不虚矣!
友人给我的溢美夸赞,恐怕也起了作用,以致钱先生竟有兴致邀我这个学生去晚餐。我感到这真是一种殊荣。
当然也忘不了杨绛夫人的盛意,要为治馔费事。记得清楚的是,有一盘烹大虾(津沽称“对虾”),当时的北京此乃不多见的佳品。
我的记忆力大半失灵了——这次餐间的谈话,竟不复存一字于胸臆中,只记得在感动之下,回来即作了七律一首,以志高情殊遇——我们唱和的七律诗曾有很多篇,一字无存。
有我和他原韵的,回信赞我押韵“如土委地”:即浑融一体、了无勉强之痕迹的比喻。
钱先生如此称赏一名在校学员,并不足以说明我就真的十分高明卓异,却令我体会到他的寂寞之感——可以共语之人已然无多了。
燕大图书馆是一座出奇的宝库,你想找的书,可在此处不费任何烦难手续而一索可得,可以保证借到想借的百分之九十九。我这个西语系学生,专借线装书,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
那时借书极为便利:只需在书卡上签名(或学号)就可以了。我所借的,一看书卡,竟是空白,我为多年来的第一个借阅人,这令我颇为惊讶而感叹。另有若干部清初人诗文集,则书卡上有了一个签名者——竟是“钱锺书”。
例如顺、康时的顾赤方(景星)的《白茅堂诗集》,也只有我们二人借过,而书眉上却有墨笔批注语,入眼便知此皆钱先生的手迹。
另有一件事,顺带叙及。还记得那回谈及中国诗的神韵问题,钱先生说:神韵是确实的存在,并不玄虚,只是有人不能领会到,便以为无所谓神韵。例如我的servant(原话用英文字)就无法理会什么是神韵。
我想,他的意思是说明此乃文化教养水平的事,不能强求于每一个人,同时也说明,神韵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与西方类似概念的同异,必须深细讨究。
但到解放之后60年代,一件难以名状的事态发生了,即是种种批判运动中忽然又出现了一个新名目,叫做“拔白旗”。
那时人文社领导人早都 “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讲政治,紧抓运动最积极,在所出的书中,选定了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是“白专”的大标本。于是组成了“批判小组”,要纷纷发言,务必分清“红”、“白”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组”里,业务上弄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说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宋诗选注》,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聂公邀我进燕都
1952年至1954年,在成都华西大学、四川大学外文系当了两年讲师;因1953年之秋《新证》问世,聂绀弩先生见之有致赏之心,遂烦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工作。我当然愿意进京。川大不放行,冯雪峰社长请中宣部下调令,几经力争,方得如愿。
我于1954年春夏之交,回到北京。到京后给我的宿舍在东城东四牌楼十二条胡同以北的门楼胡同,三间正房。
报到之前,聂绀驽同志来看我,是和舒芜先生一同来的。
这次来,只是观看一下住处情况,未落座,也未多谈。两个细节记忆犹清:聂公见我在正北墙上悬了一副对联,写的是“旧有雄文悬北阙,近无老屋在南山”(欧楷甚佳,已忘书者姓名),他便立刻说:应改——改为“近有雄文悬北屋,旧无老屋在南山”。
他的敏思让我惊佩(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红楼梦新证》刚问世不久,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知我的“家底”“出身”了)。
舒芜老兄那次初会未说什么,只言:“我若知道社里还有这么好的房子,我早来(住)了!”
及至上班后,又与他是同一办公室。记得是向南的窗,两桌分列,他东我西。
隔壁是张友鸾与顾学颉。因此舒兄曾示我戏语曰:这屋是“不作周方”,那屋是“东张西顾”。上句运用《西厢》“不作周方,埋怨煞你个法聪和尚!”——他本姓方,故巧用“周方”一语。另句即又变用“东张西望”的俗语而只改一字,切合了张、顾二姓 (顾也合“顾盼”之义也)。
初来之人,好比新媳妇刚入门,一切新鲜,故这些琐语细节也忘它不了。
我到班之后,聂公给我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恢复”《三国演义》里被删的题咏诗。他说:“毛主席指示,那些诗不能删,要恢复原文。”(因该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诗句删掉了,以为“无用”云……)
我补完诗后问他: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他说:那就校校吧。他的话总是这种简而不繁的语式。
我一校之后,校出大量问题,改正之后,写了一份很长的工作报告,交与聂公。
不久他将报告给我送来,面有喜色,说:“报告大受称赞!你写篇文章,给《光明日报》替新版宣传宣传!”后知受称赞是指巴人(王任叔)。
我写了文章,由社方交《文学遗产》版刊出了,见署名是 “孙模”二字,不知出于哪位代拟的。
要我当小说组长是在此之后,聂公亲口“任命”的。
我当时十分惶恐——多年一直在高校,来社后一切不懂,如何做什么组长?十分为难,便找他辞“长”之任命。他说:“没什么,你只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张友鸾帮你。”
我辞不下来,跟着就要我作一份当年下半年的“文稿计划”,要按月份列出拟出的书名来。
这下子可更把我难住了!
无奈何,到邻室去找张老了。
张老是个老报人、老编辑,老练非凡。见我去求他,说:“听领导的指示!”——其语亦庄亦谐,不卑不亢,可也很“厉害”!那“领导”二字即指我这“组长”新头衔了。
他确实有本事,不一会儿就列出了一份六个月的“发稿计划”。记得其中有《聊斋》,还有《阅微草堂笔记》。
以上各情,初来的“新媳妇”印象太深了,终身难忘也!
记得四兄祜昌说过几句话: “你耳坏之后,有聂公为你之知音——以其姓之三个‘耳’字,其中有妙理也。”今日回想,也有意趣。
(摘自《天地人我:周汝昌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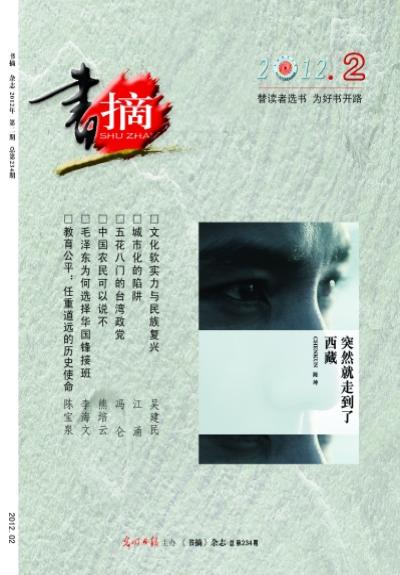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