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这个名字是那一代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寻找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今天对此或许可以批判,可以指责,可以反思,但当年围绕浩然所形成的一个历史场,对人们的熏陶和指引却是难以磨灭的,它是一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
那天去北京方庄东方医院看病重的浩然老师,手上抱着一束鲜花,心中忐忑不安。几年前在做有关文革文化专题史料时,曾数次驱车到三河市采访浩然老师,他的思维敏锐和身体利索都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他曾对我说,得过两三次脑方面的病,但都扛过去了。中午吃饭时他不顾我们的劝说,执意要喝几口当地出产的酒,兴致颇高地说:“没事,身体没事。今天难得高兴,难得啊。”
到了病房,看到浩然老师躺在床上不能言语不能识人,脸上皮肤尚好,一双大眼睛混沌地瞧着来人,过了一会儿嘴角一咧,竟有几颗眼泪从眼眶渗来。旁边的护工说,看到亲友来访,他都会有这样的表情,也许他能认出你来。
握着他骨关节突出的手掌,我许久难以说话。老人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没有飘移。我觉得他的视线穿透很远,落到别人难以企及的、无可名状的某个时空深处。
一些朋友闲聊时,问及少年时的经历,我一再坚决表示:“浩然是我小时的偶像。”大家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当年我对于农村的感觉,基本上都是靠长篇小说《艳阳天》建立起来的,以至于在高中读书时对上山下乡之类事不发怵,甚至对农村生活有一种意味十足的向往。细细琢磨书里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很自然又被我移植到对现实人物的判断,像富农弯弯绕这类算计精明、从不吃亏的鲜明角色在生活中是很容易发现的。我觉得浩然的笔下有魔力,佩服他对人物游刃有余的把握,我们写作文时大都受了他的短句子、简洁白描等影响。
当时中学课本里收了不少浩然的短篇小说,所收的篇目大概仅次于毛泽东、鲁迅等文章和报刊社论。高二时学了浩然新作《一担水》,农民主人公身上大公无私的爽朗对我们有一种无形的影响,再写作文时也留意让笔下的工农兵人物豪情万丈,比起模仿鲁迅的《一件小事》顿时要神气许多。
浩然有一本名叫《幼苗集》的青少年读物,当年是班级红卫兵组织学习的必读书目。他用清新的笔调描述了一群农村少年是如何爱护集体荣誉、爱护公物的,品质的淳朴和风景的秀丽都让我们入迷。最关键的是他的文字洁净朴实,不拖泥带水,没有鲁迅文章那样的深奥,没有社论文章那股政治化的火气,也没有夹杂很多当时常见的让人生厌的八股气。对于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得益于这种文字的滋润已经属于理想的事了。
1974年浩然写出了《西沙儿女》,我们读后颇感惊讶,主要一点是他还会写散文诗体,还会在很短写作时间内把当时政治军事斗争事件大杂烩地码在一起。多少年后我把当年的读书体会告诉他,老人苦笑地说:“当时可苦死我了,好几个晚上在部队的铁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好把小时候知道的抗战故事挪到西沙,加上反击战和批林批孔的内容。用散文诗写作是为了取巧,为了赶进度。”
我记得,他用了“不足为训”四个字来总结过去那段的写作生活。
1998年在做完老舍、汪曾祺等作家史料专题后,我就很想接着做一篇浩然老师的专题文章,《读书》的编辑叶彤也极为支持,认为由此可以深入到文革文艺重点人物的内心状态。就那么巧,有一天接受报社采访任务,到雁栖湖走了一趟。在游船上竟意外地见到浩然老师,他当时情绪极好,与周围的人谈笑风生,可以看出他在京郊、冀东一带有着很深的人脉关系,当地人不计文坛风雨变化而依然取敬仰的态度,也从侧面显示他在那一片土地的文名之盛与长年影响。
我找了一个空隙,把自己的采访意图告诉老人。想不到他“嘿嘿”一笑,一口答应下来,还详细地讲了一遍开车去三河的路线。
接下来的采访,对我来说已成了一生中难忘的经历。一方面与少年时候的文学梦想相关,另一方面又得以收集文革当事人口述的珍贵史料。我至今难忘的是,老人坐在寓所二楼书房的大书桌前,面对玻璃外还算整齐的县城大小建筑物,一动不动地平静讲述自己一路碰撞走来的创作经历。暮色越来越浓,老人的脸部轮廓线渐渐有些模糊。我坐在侧面记录的同时,看着融入夜色的老人头像,不由又搅起了从少年时代沿袭而来的特有的偶像情怀。藏在内心多少年的文学梦团在那种暮色苍茫的场景中生发开来,构成了我一生中最渴望时间停滞的感性片断之一。
他的记忆力在同龄人中算是出色的,连三十多年前与江青、姚文元的对话内容都可以大体复述出来。他详细叙说了他所知道的文革初期老舍挨斗受害的情景,说完后长叹一口气:“老舍去世是北京文联当时最大的事情之一,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组织向我问询过有关老舍的最后过程。我今天是第一次跟外人说得这么多,就是因为没有人问过我。”
根据这几次三河采访,我又陆续走访了二三十位有关当事人,完成了《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一文,在当年《读书》刊发后反响颇大。事后老人对文章还是满意的,唯独对女作家草明评说他的一段话十分在意。有一次他陪老伴来京看病,住在西三环万寿寺附近一家军队招待所里。我请老两口吃晚饭,那天老太太言语不多,在一旁瞧着老头激情讲话的样子就偷笑。我知道,浩然老师受文革牵累二十多年心结很深,有时在阴影中难以解脱。我轻言相劝,他总是摆摆手:“没法说,没法说——”再劝他专心完成已拟提纲的《文革回忆录》,他又摊开手:“有难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片面性。”
春天的时候,我开车拉着刘庆棠、钱浩梁夫妇等三位老师应邀前往三河做客。浩然老师一早就在大厅等候,见面时摇晃着手不放,泪眼朦胧,反复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六年没见了,二十六年没见了——”作为文革文艺界核心人物,他们再次相逢时白发丛生,面有衰容,言语不达心意,应了“岁月磨人”那句老话。
可如今,老人躺在医院里面对历史再也说不出什么了,对任何批评也无言以答。对于亲友来访,已呈现植物人状态的老人居然会有一些细小的反应,这让不少老友们颇感惊异——对于人世间的温情还是有所感知的。
我只能在心里把暮色中的老人叙述的场景静静地定格。
我印象中的浩然几件琐事
十年前,我曾三次在河北三河采访浩然老人,基本上都是上午九点多开始,老人坐在寓所二层书房大书桌前,大致按着事先设定的范围做专题讲述。
浩然几乎是自我放逐到小城的,抱定决心与京城过去的一切割离。他说:我不愿住到城里,住在文联宿舍不愿见人,老是低头走路。
背着过去的包袱,老人没有走出十年浩劫的阴影,在人与事的许多枝节上没有求得一个彻底解脱。他来北京,有时偶尔来开个会,有时为多病的老伴求医抓药,总是当天来回。文联宿舍的熟人们很难见到他,只知道他在三河写书、扶助冀东文学新人等等,文革的纷争及清查的往事渐渐变得模糊,甚至偶尔提及都有一种不真实之感。
他的内心还是牵挂城里的一切,视野放及世界。记得有一次,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最近文艺界有无大事?”我说:“作协刊物要断奶。”他停顿一下,若有所思地说:“《北京文学》还能凑合,有董事会。”他任过几届《北京文学》主编,这种牵挂就变得很实在。
有一次闲聊到某一个邻近国家的做法,他愤而说道:“他们还是老一套。”这也是一种态度,间接表明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满意度。他诚恳地说过:“不搞改革开放是不行的,要不人心会涣散的。”他对冀东大地上的变化是满心欢喜的,只不过对当地一些暴发户的做派看不惯,闲谈时多有愤激之言。
浩然年轻时从事记者工作,跑遍冀东、京郊一带,与这一片土地有着紧密的情感联系。他说,当时只有一辆自行车做代步工具,靠了它走遍许多村庄。他还说,曾骑车到过十渡、怀柔、密云等山区,深入到农家采访,与不少固定的老关系户保持密切联络。
最熟悉的村庄莫过于顺义的焦庄户,这是当年抗战时因地道战而闻名的村子,他时常骑车来此走家串户,介入农家的生活,与干部村民打成一片。村支书萧永顺成为《艳阳天》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之一,焦庄户发生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也融进作品的字里行间。
他曾刻意躲避江青,他说这是无奈之举。他认为,在文革那样的官场混事,有时耽误时间太多,很想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基层,留在与农民的生活联系上。
浩然创作生涯中的亮点和不足、长处和局限性都很明显,作为文革文坛标志性的人物之一,他所留下的文字和教训应该成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遗产。
北京“月坛北街”是他的一个迷潭,有时他要费不少时间才能解析清楚,有时他仿佛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涉及月坛北街的岁月,他有时是爱说的,而且披露的细节格外鲜活。譬如他说,文革中每次去钓鱼台见江青、张春桥等,都是坐上面派来的面包车进去的,从来不能用文联机关的车辆。他对当时大批判时一些人的发言颇感恼怒,这些发言者说他从西沙回来先奔江青去了,机关司机在钓鱼台外面冻了一夜。他大声地对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上钓鱼台从来没有用过机关的车。”
他又说了一件事,当时广东一家报刊发表批《西沙儿女》的文章,全国到处转载,他觉得自己在政治上算是完了,心里又害怕又委屈。他给中央某机关领导写了一封解释信件,就是从月坛北街家中直接送到钓鱼台收发室,也就是几百米的路途,他走得特别费劲茫然。信交出去,但没有回音,更增加心中的苦闷,坐在家中望着远处的钓鱼台方向而难于释怀。
他说的另一件事给我印象最深:一天上午他离家去参加市文联大会,他念了一小时检讨书就算解脱了,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那天正巧是他大儿子结婚,散会后他直接从会场到了婚礼现场。他说:“事情就那么巧,总算那天很高兴。”
2008年2月20日晚八点,接到浩然女儿通报的电话,我问老人最后在医院的情况,她说:“从去年十月开始,父亲的病情就很不稳定,医生让住到重症病房抢救,这几个月情况一直不佳,血压、器官都不太好,今年春节前就出现了病危。”
老人五年前住院后就已经不能认人,躺在病床上再也说不出什么。他从同仁医院移到方庄东方医院,静静地在十二层一间干部病房走完最后的日子,没有思考,也没有缠绕多少年的烦恼。
我每年总要去医院探望一两次,几年间觉得老人在家人和护工的细心照料下,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腿部稍有萎缩。脸上皮肤尚好,甚至跟正常人一样光滑,细看起来竟还有一些红晕。只是他在病中曾用牙咬过嘴,在嘴角处留下一处咬破的伤口。
听护工大姐说,病重中的浩然老人对于亲友来访有时也会有一些细小的反应,对于人世间的温情还是有所感知的。
有一年春节前,护工大姐突然发现老人眼角流出几滴泪水,表情也有几分哀戚,她甚感诧异。过了几天她从家人的口中得知,相伴几十年的浩然老伴就在那天不幸去世。护工大姐连连感叹:老人多少还有几分感应,真让人惊奇。
后来,护工大姐在床旁放置一个金鱼缸,有几条无忧无虑的鲜艳的小金鱼在缸内欢快地游玩着,老人总是侧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久了就会咧着嘴“嘿嘿”几声,脸上表露出一丝丝难得的愉悦神情。
浩然是我们那一代学生的集体偶像之一,“浩然”这个名字是我们在少年成长时共用的符号,每个人都会从他那里或多或少地寻觅到过去时代的某些碎片。《艳阳天》、《金光大道》固然有天大的缺陷,但却是我们在万分苦闷之中最难得的必读之物,书中一些个性十足、读来亲切的人物(如精于算计的富农弯弯绕等)一直是我们念念不忘、时常叨唠的文学群像。
如果没有浩然的文字,我们头上那片文学的天空只能是更加无味和暗淡。在采访之余,我曾对浩然说:“您的作品影响了我们的一生,像《艳阳天》、《幼苗集》当时不知读了多少遍。”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谢谢,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文艺界是非事太多了。”
我们特别在意作品的阅读效果,只存一份谢意;他依旧没有走出过去的阴影,只留一份沉滞。
这就是我们两代人的真实心境,中间相连着十年浩劫和改革开放的岁月,那种能够深入骨髓的东西依然在悄悄地发酵。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岁月造化,人陷在残酷的政治运动中所面临的思想困境和性格悲剧,没法躲闪,难于排遣,这一点在浩然身上体现得十分鲜明,他是那个年代最具标本性的人物之一。
(摘自《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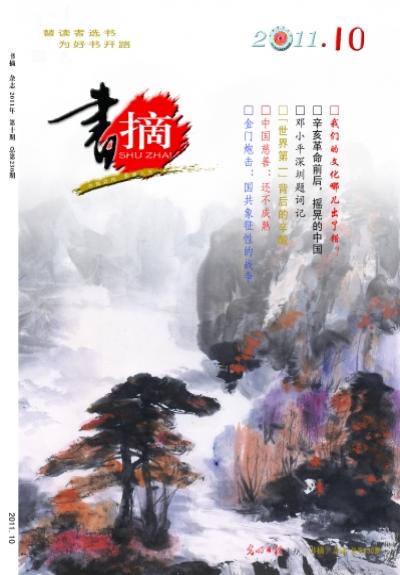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