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黄永玉的猫头鹰
出版社来了新同事。她来自苏格兰,叫白霞(她的英文名字是Patricia)。一起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她邀请我过几天和她一起去拜访戴乃迭和她的先生杨宪益。我欣然答应。
戴乃迭和杨宪益夫妇不仅健谈,也很好客。他们很喜欢学术上的讨论,很快我们就定期去拜访他们,每次去我们不是带上一两瓶白酒,就是蛋糕或者是一条烟。有时我们是那里唯一的客人,有时那里坐满了艺术家和文人学者,大家在烟雾缭绕的氛围里畅谈,这时戴乃迭喜欢用“文革”时的话说杨宪益是在“腐蚀青年人”。如果想和这对夫妇谈得来,首先要对中国的革命和“文革”的悲剧有深入的了解。如果不了解或者以西方的发展历史作为衡量标准,戴乃迭和杨宪益夫妇就会在告别的时候笑着把对方拉到怀里,安慰地说:“其实我不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从1952年开始夫妻二人在外文出版社工作。他们虽然很欣赏西方,欣赏那里的科技、民主、文学、戏剧、音乐,但也很珍重中国,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他们在中国生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一家人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离开中国。
1977年对于很多中国的艺术家来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在社交活动中,在宴会上,在媒体中,忽然涌现出了很多艺术家的身影,其中有演员、导演、画家、音乐家、书法家、作家。他们终于从被遗忘的角落里走了出来。一听到他们的名字,人们都会感到眼前一亮。人们再一次用惊讶的目光去审视他们的作品,不仅看他们在五六十年代的创作,也看他们解放前的创作。有些作品表现出令人无法想象的现代性,在绘画方面,无论是中国画法还是西洋画法,人们都不得不为一些早期作品所体现出的多元化而惊叹。在北京生活的外国人好像忽然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有小道消息说在北京很快要举办一场贝多芬音乐会,一时间这个消息成了外国人圈子里最热的一个话题。
白霞和我有时陪杨宪益夫妇去黄永玉的家里做客。
在黄永玉家里我们不是坐在小板凳上就是直接坐在地板的垫子上。讲到自己曾受到过的迫害,黄永玉充满愤怒,说到他的过去和对未来的计划,他神采飞扬又不失幽默。
黄永玉的猫头鹰不但在全国出了名,后来竟成为了代表反抗的符号。全国各地很多人给黄永玉寄来以猫头鹰为主题的绘画、摄影、雕塑,作品数量繁多,形式各异,其中还有人寄来了猫头鹰的标本,更有甚者表示要给他寄一头活的猫头鹰来。黄后来说如果他事先知道这只猫头鹰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他一定会画出最美的一只猫头鹰,而且在下面签名的时候也会更加仔细一些!
对于批过他的人,黄觉得其中90%的人其实是好人,只是没有勇气替他反抗。有的人很善良,在没有旁人的时候悄悄地鼓励他要坚持下去。有的人不敢直接和他说话,就给他打手势表示同情。所有这些都让他觉得人们并不都是冷漠的,内心里还是有反抗的。在批斗中有两个同事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们虽然和黄永玉不是很熟,但却公开表示不同意对黄的批斗。其中一个年轻的画家在“黑色艺术展览”期间大声地叫他的名字,还走过去和他热情地握手,他说那是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据说姚文元曾经命令《人民日报》把黄永玉描写成最危险的阶级敌人之一,但是文章在最后关头被毛泽东亲自制止了。
“不要再问他关于猫头鹰的事了,”我们告辞时他的小女儿黄黑妮对我们表示抗议,态度十分认真,“猫头鹰死了!”我们都禁不住笑了出来,黄永玉笑的声音最大。
三个星期之后圣诞节到了,我们一群人又都聚在一起,这次是在杨宪益的家里。让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黄永玉竟然给我带来了一幅画,一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这只漂亮的猫头鹰有金色的眼睑,穿一件金红色的袍子,留着一撇小胡子,悠闲地站在一根树枝上。画的下面写着:“此鸟每夏捕鼠一千二百只,合节约粮食一吨,实除四害之大大英雄。”
画还没有裱过,节后我决定到著名的荣宝斋把画给裱上。等我10天后去取的时候,画已经被挂在店里十分显著的位置,有的人好奇地询问:“啊,黄永玉又开始画猫头鹰啦?怎么看上去像是个外国人?”当我把这些话告诉黄永玉时他大笑起来,他说第一张猫头鹰就是在荣宝斋被造反派看到的。
与沈丹萍,在叛逆的气氛中恋爱
凌子风经常到友谊宾馆来找我,我们一起在餐厅里吃饭,一起坐在家里的地毯上聊天。如果知道他要来我总是事先准备好一瓶白酒。我们在一起聊艺术、电影、女人、政治,直到他酒意大发开始画画。有时我把饭店里的其他外国人叫来一起聚会,有时也请北京电影厂、八一电影厂或者总政歌舞团的年轻人过来。这样的聚会通常会持续很长时间,热闹非凡,大家又唱又跳,音乐的声音震耳欲聋。
有一次我给凌子风打电话,半开玩笑地问他下次来的时候是否可以带上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两个小时后他已经来敲我的门,身边还真的有两个年轻女子。他故意很大声地给我介绍:“刘丰!她是我们电影厂期刊的编辑。”对于第二位他是这样介绍的:“沈丹萍,我们厂里最有名的电影演员之一!”他的口气既有趣又让两个年轻女子感到很受用,他很会给别人面子的。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沈丹萍这个名字,穿着军大衣的她看上去非常年轻,怎么可能是最有名的电影演员之一?我充满赞许地向他们点头,接过他们的外套,倒茶上小点心。为了活跃气氛,凌子风不停地给我们讲笑话,看来两个年轻女子还从来没有这么近地和外国人接触过。刘丰看上去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身材苗条,比一般中国女人要高挑一些,有一张很漂亮的面孔,表情中透着顽皮;沈丹萍身材娇小,有些拘谨,没怎么说话。她的笑容一下子迷住了我。两个年轻女子都住在电影厂的宿舍里,还是同屋,关系好得如同一对亲姐妹。凌子风认识刘丰,刘丰不想一个人来,她决定把沈丹萍一起带上。开始的时候沈丹萍并不想来,说她怕见外国人——刘丰讲到这里时沈丹萍很腼腆地笑了出来。我对沈丹萍说她不用怕我,我可以帮助她摆脱对外国人的恐惧。那一晚我们四个人聊得很开心,他们走的时候我们又约好了过几天再见面……
我的女朋友沈丹萍住在北影厂的17号宿舍楼里,我不可以随便进去找她。为了掩人耳目,我们约会的时候总是带上一群人,通常是她的几个女朋友,她们几个人坐在屋子的一角,我和沈丹萍坐在另一角,就这样我们才能悄悄地说上心里话。有的时候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说不完的话,遇到不会的词我们就在纸上画。有时候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陪着我们的女朋友们都没话可说了,我就过去和她们搭一会儿话,然后再回到沈丹萍这边来。
当时见面的气氛既让人感动又有那么一点儿反叛的味道。
沈丹萍的生日快到了,我们约好了周日一整天都在我的家里为她庆祝,我把刘丰、凌子风和他的儿子凌飞也一起请来了。早上10点钟的时候客人们都来了,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开心的一天。
下午的时候沈丹萍不得不离开,作为北影厂的代表之一她要去参加法国大使馆文化处举办的一个活动。我们约好了在法国使馆的晚宴结束后大家再回到我这里来继续庆祝。到了晚上真正回来的只有沈丹萍一个人,她从法国大使馆叫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到了我的家。进饭店大门的时候门卫看到了车里的她,负责保安的人一路骑着自行车追到我住的楼门口才追上了出租车。他们问沈丹萍为什么没有在前台登记,说她没有权利擅自进到饭店里来。保安认出了她,直接叫她的名字。沈丹萍很紧张,门卫允许她到我的门前来打声招呼,她当时语无伦次。如果她不是一个人过来问题可能还不会这么严重。我和沈丹萍一起坐上出租车,在出门的时候我很严肃地对保安说我是“外国专家”,希望他能通融一下。他一直盯着我们的车开出了友谊宾馆。
在路上沈丹萍对我说,虽然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差点儿出了大事,她说她再也不到饭店来找我了。后来两次见面是在城里,但又怕被路人认出来,我们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特意拉开五到十米的距离。这个办法不是很好,后来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又能到宾馆里来找我了。每次来的时候她都带上她以前的一个男同学,英俊潇洒的电影演员贾东朔,“老贾”在进门的时候故意把手搭在沈丹萍的腰上。老贾把沈丹萍带进来后就坐在一间屋子里听音乐、看书,而我和沈丹萍在另外一间屋子里聊天。
我的合同和签证始终是个问题
在出版社里我一次次就我的合同问题提出抗议,我的行动最后终于惊动了出版社的最高领导。我说话的口气也不再客气,对于我受到的不公我开始直接地质问领导:“我知道,有人说我认识了不该认识的大人物,这是谁说的?是谁觉得我没有资格去认识这些人?”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期,但是很多道理人们是在很多年之后才明白。我不知道是谁如此反感我和中国名人的接触,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的恐惧,为什么有人想限制别人的交往自由。我请领导告诉我,作为一个外国专家我到底可以和什么样的人交往。我很坚定地说,如果没有明文规定或者是事先明确告诉我这些问题的答案,出版社没有理由拒绝我的合同延长申请。
出版社的副社长刘德友决定在我的合同到期之日起再给我延长三个月的时间,我请他给我延长12个月,刘社长没有答应我的请求,但是也没有立刻拒绝。他当时正准备去文化部接一个副部长的位子,可以看出来他很努力让各个方面都对他满意。
情况虽然比开始的时候好了一些,但是未来仍然很不明朗。我和沈丹萍是否能在中国待下去的问题成了很多人谈论的话题,后来连“新华社内参”的人也听说了。我们接到新华社内参部一个记者的电话,他说想采访我们,我们答应了他的请求。记者是个年轻人,在饭店里他和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不但是个聪明人,善解人意,英语说得也想当流利。我们和他开诚布公地讲了我们的困境和我们的想法。我们遇到的问题包括我的签证,单位曾经极力阻碍我们的婚姻,诬陷我是个“有问题的外国人”,还有我们到了年底就不得不离开中国的事实,因为我将没有工作,而沈丹萍又分不到房子住。
这篇关于我们的报道发表在1985年8月6日的新华社内参上,虽然我们没有资格看到这份报纸,但是我们听说一些政府和党内的领导对我们的情况表示了同情,至于他们都具体说了什么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迫不得已给中央写信
还有两个月我的“外国专家”签证就要到期了。我想申请一个新的签证。找到一份新的工作好像完全没有希望了。没有工作单位在中国意味着很多麻烦,工作单位比自己的母亲都重要,一份工作可以为你铺平生活道路也可以一下把你打倒。保住一份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保护。一个人和他的工作单位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工作单位生活该怎么过!我的特殊情况是,不论我去哪里,不论开始的时候对方有多客气,最多见过几次面之后他们对我的态度就会发生改变。他们也不对我隐瞒原因,说他们收到过通知,有时是口头的,有时是书面的,明确地要求他们不要和我合作。
我的签证到期后我将失去外国专家的身份,必须离开中国。到时我可以在德国再重新申请一个新的签证,可我不会为了一个签证专门飞去欧洲,而且就是到了那里我也不确切自己是否能得到签证;此外我的太太将要在12月生孩子,对我来说12月离开中国是个非常不合适的时间,而让我的太太怀着孩子跑到异国他乡去也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我又给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我写道,我从来没有违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但是总是有人“想方设法不让我在中国待下去”。我认为这种对我的做法是“极其违法的”,在信里我还说如果我没有新的工作,警察在12月31日之后不准备再给我延长签证。“我请求您,”我写道,“在所有我工作过的单位,保护我的权利和我的名誉,洗清对我的指责。”我的口气很坚决,对胡总书记我充满了信任,“我向您声明:一天我的名誉不被恢复,我就一天不离开中国,不论他们给我施加多大的压力!”
同一时间沈丹萍也给妇联的领导邓颖超和康克清写信请求她们帮助。当我看到信的开头时禁不住笑了出来,沈丹萍把她们称作“亲爱的邓妈妈”和“亲爱的康妈妈”。
女儿给我们带来了新生活
12月6日上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三天之后沈丹萍和我们的女儿离开了医院。我们刚刚回到友谊宾馆的家里电话铃就响了。是北影厂打来的,我把话筒递给沈丹萍。我能听出来有人在电话的那一边祝贺我们女儿的出生,然后我注意到沈丹萍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边在话筒里说“是,是”“很好”“一定”,一边瞪着大眼睛对我点头,放下电话后她的眼睛还是瞪得圆圓的,好像触了电似的。她说从“非常高”的领导那里下来了“特别指示”,让我们住进电影厂的新宿舍楼里去,钥匙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沈丹萍只要去取就行了!……简直是太好了,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把小婴儿从包着的被子里抱出来,她躺在那里放声哭了起来。
我给负责外国人签证的刘警官打了电话,他问我孩子是否已经出生了,然后他向我表示祝贸。他的态度十分友好。他问我这几天是否有时间到他那里去一趟,带上护照、两张照片和一份延长签证的申请信。他说他已经知道我们分到了房子,而且也拿到了居留许可。
两天后我去了位于紫禁城东边的签证处,刘警官说一周之后我就可以拿到签证了。告别前他对我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很明显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作为负责外国人的警察,我们要保护中国人的利益不受外国人的侵犯,同时也要保护外国人的利益不受到中国人的错误侵犯。”从他的话中我明白了,我和我的上级单位在过去这几年中一直存在的问题终于有了了结。
(摘自《穿越界线——一个德国人在中国35年的传奇》,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10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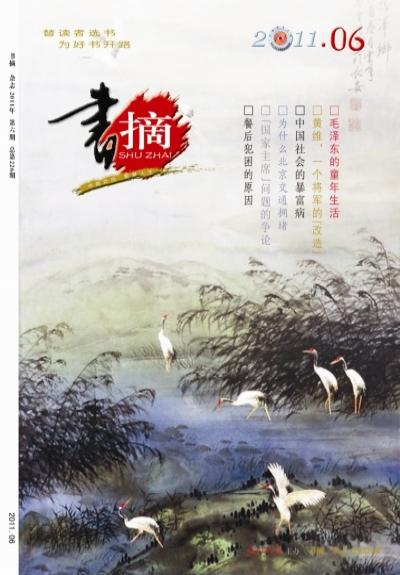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