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开始了在北京大学十年的生活。1979—1980学年,第一次听林先生讲课,课的名称是“《楚辞》研究”。这门课对我的影响,多年后我才明白。
这是一门选修课,内容包括先生正在撰写的《天问论笺》。先生用了好几堂课的工夫讲解《天问》的考证和错简的问题。我对《楚辞》学一无所知,听起来当然像天书一样困难。不过,先生化繁为简,举重若轻,竟然将考据和笺注这样的题目讲得引人入胜。先生说:我们固然不是为考据而考据,可是考据的问题又总是无法回避。考据并不意味着钻故纸堆,堆砌材料,闭目塞听。好的考据家就像是出色的侦探。我们每天上课下课,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对周围的世界,或者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如果福尔摩斯也从这条路上走过,他的观察就和我们不一样。他能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看出问题。任何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蛛丝马迹,也逃不过他的眼睛。他甚至凭嗅觉就知道发生了什么。这种锐利的直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是侦探的职业敏感,也是考据家的第一要素。先生的话引起了我们对这门学问的兴趣。年轻的大学生,说到侦探,有谁不跃跃欲试?其实,这两门行当,如果不是旗鼓相当,至少也可以触类旁通。不论是侦探还是考据,都需要耳聪目明;推理之外,还得有洞察力和想象力。我后来才知道,先生的这几句话也同样适用于诗人和学者,更是他本人的写照。而考据的难处和好处,我当时当然都是体会不到的。
二十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先生的讲课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诗人的气质和风采。先生身着丝绸长衫,风度翩翩,讲课时不读讲稿,只是偶尔用几张卡片,但是思路清晰,且旁征博引,让我们一睹文学世界的万千气象。讲到《九歌》,先生用的几乎是诗的语言,而他本人便如同是诗的化身。我记得当时我们完全被征服了。全场屏息凝神,鸦雀无声,连先生停顿的片刻也显得意味深长。这情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诗的魅力和境界。1982年本科毕业之前,我决定报考中国古典文学的硕士研究生,师从林先生的弟子袁行霈先生,专攻魏晋南北朝隋唐诗歌。
先生的“《楚辞》研究”是退休前最后一次为本科生授课,是先生告别讲坛的仪式。在听众中,经常可以见到当时系里的一些老师。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我得以亲历其境,当然深感荣幸,不过荣幸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心,因为期末得交一篇论文。我煞费苦心炮制的那篇文章,细节已记不清楚了,题目好像是《从离骚中的龙与马谈起》。文章交上去不久就发了回来,我的成绩是A!那一年我不过17岁,于古典文学尚未知深浅,因此,兴高采烈之余,竟有些踌躇满志了。学期结束后,有一次又听先生的助教钟元凯说,先生以为文章写得不错。这当然更让我大喜过望。曾经想去拜访先生,可是事出无因,未免唐突,终于也就作罢了。
1984年底,我获得了中国文学的硕士学位。在此之前的几个月,听袁先生说,系里在考虑安排我留校任教。记得有一天晚上,钟元凯忽然来敲门,问我是否愿意在任教之外,接替先生的助手工作。当时系里或许也有类似的考虑,不过,先生希望先见一面。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在元凯的引导下,我第一次走进了燕南园62号。那天室内的灯光略显暗淡,可是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兴致很高,问了我的年龄后,大笑说:“我们之间隔着半个多世纪!”就这样开始了我与先生相处的三年多的珍贵时光。
因为我刚刚开始教书,助手的工作耽搁了一段时间才真正起步。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为先生做事,和先生聊天,是相当愉快的经验。按照当时的日程,我们每周见一次面。首先是整理出版《唐诗综论》。其中的文章大多已经发表,只有两篇得从头开始。先生因为常年手颤,书写不便,我们的工作方式通常是先生口述,由我记录整理以后,读给先生听。如此往返几次,最终定稿。先生以治中国古典诗歌而闻名,讲论唐诗更是他的本色行当。记得先生每次说到唐诗,总是神采飞扬。若不是师母叫停,真的是欲罢而不能了。这些谈话留给我的印象,至今新鲜如初,仿佛唐诗的精神已经化作了先生的生命血脉,不必假以外力,反求诸己,即可呼之欲出。
先生对文学的评论也有其智性和哲理的层面。他说:“艺术并不是生活的装饰品,而是生命的醒觉;艺术语言并不是为了更雅致,而是为了更原始,仿佛那语言第一次的诞生。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力量。物质文明越发达,我们也就越需要这种精神上的原始力量,否则,我们就有可能成为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俘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这种声音听上去真有如空谷足音,而这又正是先生一贯的想法。早在1948年的《诗的活力与诗的新原质》中,先生就特为强调了诗的“原创性”。先生认为,诗的突破性在于它的全部力量凝聚在一个点上,如同光聚成焦点而引起燃烧。点的突破是一切创造性的开始。点延伸而有线,历史便是线的展开。然而,线性的历史终不免有所因袭,因袭的力量愈强,原初的动力就愈弱。艺术就是要克服这因袭的力量:“就艺术来说,它本来就是要唤起新鲜的感受。这种感受是生命的原始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它往往被习惯所淹没了。因为生活中一切都是照例的,不用去深想,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感觉也就渐渐僵化,迟钝起来。例如我们经常往来于未名湖畔,其实往往是视而不见。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如果因久病住院,一旦病愈,带着一片生机走出医院时,看到眼前的一草一木就都会感到特别新鲜。因为使人感觉迟钝的习惯性被割断了一段,就又恢复了原有的敏感。这敏感正是艺术的素质。谢灵运‘卧疴对空林’之后乃出现了‘池塘生春草’那样‘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天然名句,其所以鲜明夺目,就因为它生意盎然。”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对文学艺术抱有非同寻常的信念。这在今天这个物质过剩、精神匮乏的时代,大概不免要难乎为续了,然而也正因此而更加难能可贵。先生认为物质超出我们个人的需要,就成为负担。而物质的世界,一旦走进去就出不来了,因为物质有引力(别忘了先生早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在先生看来,艺术是一种更高的精神的呼唤。先生用火和光作比喻:是火就要燃烧。火是光的起源。然而,火又同时带来了灰烬,这光最后也可能就要消失在这物质的残骸里。因此,艺术要不断摆脱灰烬,这就是要在精神上不断为自己找回那个起点。先生赞美原始性,正因为那是一切开始的开始。
这些话显然已经不只是在谈文学和艺术,而是涉及了生活的态度和人生的境界。可是我们知道,先生的这种人生的哲学经受过多重的考验。的确,生活中的各种磨难,日常琐事,人事纠缠,政治运动,都足以让人意气消沉,窒息了生命的火焰。先生那一代学者经历了抗战期间的流亡,先生本人就曾在临时迁移到长汀的厦门大学任教。师母回忆说,长汀的条件异常艰苦,动不动还得抱着孩子跑防空洞,躲避日军飞机的轰炸。在“文革”中,先生也照例吃了不少苦头,运动初期,被指派去打扫学生宿舍,家中的客厅又挤进了另一户人家,情形之窘迫,可想而知。后来师母多病,而又近乎失明,先生悉心照料,每日心悬数处,真是谈何容易。可是先生多次说:“我这些年身体还可以维持,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而这又岂止是说说而已?真正的精神力量,并不需要叱咤风云,或表现为金刚怒目。“文革”十年,是物质和精神双重匮乏的时期。不过,先生自有他对付的法子。在《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中,先生说:“十年动乱期间,夜读《西游记》曾经是我精神上难得的愉快与消遣。一部《西游记》不知前后读了多少遍,随手翻到哪里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读下去,对于其中的细节,也都仿佛可以背诵似的。而已经如此熟悉了,却还是百读不厌,这或许正是《西游记》的艺术魅力所在吧。”至于厦大的那段经历,我只记得先生有一次说到,他在长汀的球友多少年后还从海外来看他,一起回忆当年“弦歌不辍”的日子。先生的豪爽和达观,于此可见了。
写到这里,我不禁记起先生关于治学的一些谈话。在我离开北京前的一个月,先生郑重地谈到我将来的学术发展:像你这个年龄是最可宝贵的。重要的是培养你自己的职业敏感和良好的素质,这样才有突破力。就像一把刀子是锐利的,遇到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不论进入哪个领域,都能做到游刃有余。人不可能把材料都收集全了才开始研究,追求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就像侦探总是顺藤摸瓜。而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个敏感性的高度是在青年时代获得的,此后发展的规模取决于这个高度。所以,必须首先去发现自己的敏感点,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全力去培养它,发展它。我更忘不了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无论什么样的学问,都应该高屋建瓴,也就是要保证是在高水平上进行的。就像是唐诗,工拙姑且可以不论,毕竟气象不同。这气象便是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的体现。
与先生谈话,总是这样感到精神振奋,仿佛蓄电池又一次充电。而与先生相处,又每每有如沐春风之感,令人神清气爽。先生是诗人,可是先生说,诗人是一场修炼。先生对学术有自己的标准,却从不固执己见,更不落于迂腐;性情豪爽豁达,而又重人情讲事理;无论是日常平居,还是接人待物,都流露出淳厚的性情修养和文人本色。1988年7月的一天,我上午刚刚在先生那里协助完成了《西游记漫话》的《后记》,下午又收到先生托保姆转来的一个便条:见条后即来一晤为感。我匆匆赶到燕南园,一进门,先生就拉着我的手说:有一件事情,你无论如何得答应我。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才是。先生说:你上午说机票涨价,我不清楚到底涨了多少。这是三百元钱,你就用来买机票吧。我这才想起来,上午说到等出国签证期间,我打算回家一趟,顺嘴提到了机票的事情。我有些措手不及,又后悔上午多说了一句话,连忙说,我已经决定买火车票回去了。先生坚持说:不管买不买机票,这钱反正你是需要的,买衣服,置行装,都需要。我们相处了这几年,真舍不得你走!可是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才好。这种方式当然未能免俗,可是清高不解决问题。你现在有困难,我就应该帮助你。好在这是我们的一场情谊,不在乎方式。
一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北京。此后的几年中,我一直与先生保持通信联系。也曾经多次打算回去看看,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96年才终于成行。1997年和2000年,我又先后两次踏上了燕南园的小径。先生的书房仍然是当年的样子,连摆设也几乎没有变动,一切都让我那样惊讶地感到熟悉,恍惚之间,如同回到了过去。墙上挂着师母的相片,默默之中,含笑注视着我们。阳光透过窗前的竹叶洒落在案头,我和先生像从前那样各坐在书桌的一边,随意聊着,仿佛是继续昨天的谈话。周围的世界渐渐隐入背景,离我们远去,只有空气中的微尘在阳光下闪烁。在这相对晤语之间,十年的时光已悄然流逝!
(摘自《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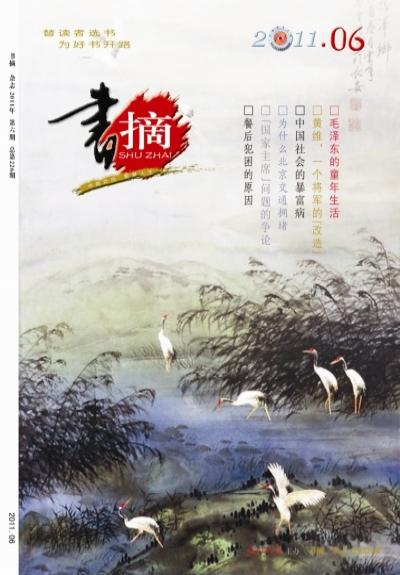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