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两次以裁撤无用政府机构与冗员、将功能相近部门合并成几大部门的“行政改革”,并以此代替“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结果是你死我活的政坛恶斗,先是光绪被囚、康有为逃亡,后是袁世凯几被围殴,慈禧甚至想要跳湖,均以失败告终。这段“行政改革史”,实在是引人深思。
温和的“维新”
第一次是戊戌变法期间的“变官制”。正是行政改革的“变官制”,成为镇压维新的“戊戌政变”的直接导火索。
众所周知,维新派的兴起肇因于只要西方的船坚炮利,回避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务运动的失败。因此,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国富民强之道。虽然他们对近代宪政民主的理解不尽准确、他们的主张也有种种矛盾含混之处,大体而言,在真正开始维新变法的“百日维新”之前,建立君主立宪制是其基本政治纲领。但就在他们鼓吹“开议院”、 “兴民权”的同时,又对中国此时的国情民情能否立即实行宪政也不无怀疑,进而认为“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1898年初,翁同龢等五大臣代光绪帝问康有为“宜如何变法”,康答曰: “宜变法律,官制为先。”梁启超也曾明确提出“变法必先变官制”这种行政改革优先、行政改革导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
“百日维新”期间,维新进入实际操作,康有为等人的主张更加谨慎、现实,绝口不提君主立宪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康有为在呈进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明确提出现在开国会、立宪法为时过早,“中国风气未开,内外大小多未通达中外之故”,“民智未开,遽用民权,则举国聋瞽,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对于谭嗣同等少数“激进派”开议院的主张,康有为也以“以旧党盈塞,力止之”。在第一次被光绪皇帝召见时,康有为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力主行政改革的“变官制”,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其行政改革的主张也非常谨慎,甚至被批评为“保守”。其主要内容是“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强调要“存冗官以容旧人”。他后来上折,提出了分别“官”、“差”的具体措施。“官”即官位,高官虚位让老臣旧官去做,使老官僚仍稳坐官位,不减俸禄,以减少他们的反对。“差”即差使,地位虽不如官高,但经办具体实事,所以重要差使一定要委派“才能”,即维新派人士担任。他认为许多不合时宜、已经无用的旧部门虽应裁撤,但他强调,如果现在裁撤必将激化矛盾。所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主要是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改革。在行政改革方面主要是启用了一些新人、新设了农工商总局,然而对行政改革起关键作用的“制度局”却因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根本未能成立。
虽然不撤旧部,但旧部官僚当然明白自己的实权将因新部之设而大打折扣,旧军机大臣怒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表示宁可悖忤皇上圣旨,制度局也“必不可开”。一时“朝论大哗,谓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京师甚至谣传康有为欲“尽废六部九卿衙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干脆以“不必更立名目,转滋纷扰”为理由,拒绝开制度局。这些“旧臣”得到紧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的坚决支持,根本不把“日日催之,继之以怒”的光绪皇帝放在眼中。设立制度局的主张,终成一纸空文。最终,只成立了个农工商局。
由于新设制度局遭到旧部群臣的坚决反对,而各项“新政”又急需费用,朝廷财政一直困难,左支右绌,于是光绪只能不顾康有为不撤旧部的意见,谕令内阁,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录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六衙门,归并到内阁及礼、兵、刑各部办公。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以总督兼巡抚事。裁东河总督,所办事宜归河南巡抚兼。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尽管疏销之盐道及佐贰之无地方责者,均着裁汰。此令一下,朝野震骇,以为此举“大背祖宗制度”,皆请慈禧太后保全,收回成命,甚至有老臣在慈禧面前伏地痛哭。所裁衙门奉旨后“群焉如鸟兽散”,如太仆寺的印信、文卷立刻无人过问,甚至门窗都被拆毁无存,犹如经历了一场浩劫,以此作为对裁撤的抵制、抗议。
简言之, “百日维新”的行政改革,主要就是启用了一些新人、设立了农工商总局、裁撤了部分闲散衙门这三项。然而,这些行政改革也使从京中的许多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侍,到地方上的一些督抚、将军大表反对,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周围, “不谋而同心,异喙而同辞”,使慈禧的政治力量空前强大。一些守旧大臣最终上书慈禧,请太后“训政”。在强大的旧官僚群体支持下,慈禧终于发动政变,对光绪痛斥道:“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表明了对“改官制”的愤怒之情,随后立即将“百日维新”期间“皇上所裁詹事府等衙门及各省冗员”悉数恢复,还恢复了被裁的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而将新成立的“农工商总局”废去。
所谓“维新”,在政治方面其实只是非常有限的行政改革,却还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而以失败告终。
帮助革命的“改官制”
几年后,立宪与革命这两个运动风生水起,渐成大潮,迫使慈禧也不得不宣布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政”,并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而且,仅仅过了五天,即9月6日就颁布了改革官制上谕。显然,无论真假,慈禧这次也想走行政改革为先、政治体制改革在后这“先易后难”的“路线图”。
这次改官制,朝廷派定镇国公、满洲正蓝旗副督统、 “出洋考察五大臣”之一的载泽负责编纂官制,制定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直隶总督袁世凯是其中之一,并命庆亲王、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大学士孙家鼐、军机大臣瞿鸿机总司核定。但众人皆知,其中的关键人物、起最重要作用的其实是掌握“北洋”大权的袁世凯,他同时还兼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八项重职。可谓大权集于一身。自戊戌政变后,袁世凯深得慈禧信任,同时他以巨金贿买了实权在握的领衔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而他在北洋的“新政”又颇有政绩。此次朝廷谕令包括袁世凯在内的14位王公大臣共同制定改官制的方案,他虽排名最后,但他因有奕劻支持,同时在负责官制改革机构“编制馆”的关键岗位安插自己的党羽,编制馆的所有文件起草和建议方案最后都要由他阅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由袁主导的官制改革方案出台。由于是为“立宪”预备,所以对官制的改革较为全面。除合并了一些不太重要部门外,还将原来的内阁、军机处、吏部、礼部、都察院全都撤销,而新成立的机构则有资政院、行政裁判院、集贤院、大理院、审计院等,而最重要的,是成立新的、大权在握的“责任内阁”以取代军机处。此方案规定内阁政务大臣由总理大臣1人、左右副大臣各1人,各部尚书11人组成,“均辅弼君上,代负责任”。重要的是,“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由总理大臣“奉旨施行”,并有“督饬纠查”行政官员之权;皇帝发布谕旨,内阁各大臣“皆有署名之责,其机密紧急事件,由总理大臣、左右副大臣署名”,如果关涉法律及行政全体者,与各部尚书联衔署名,专涉一部者,与该部尚书共同署名。也就是说,内阁尤其是总理大臣、副总理大臣代替皇帝负责任,皇帝发布谕旨须经内阁副署,若未经内阁副署则不发生效力,而且各部大臣由总理大臣推荐。这样,皇帝的用人和行政大权统归内阁、其实主要由内阁总理大臣掌握。袁世凯与奕劻议定,由奕劻出任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他任副总理大臣。
此案一出,官场风波顿起,众臣几乎群表反对。
为避免更大的动荡,清廷不得不宣布了官制改革中的“五不议”:第一,军机处之事不议;第二,内务府事不议;第三,八旗事不议;第四,翰林院事不议;第五,太监事不议。
朝廷最终裁定中央新官制只有少数旧部被裁并,但多数未动,最多只是改名,军机处仍旧保留而不设责任内阁,宗人府、翰林院、钦天监、内务府等满人所掌管的部门全部保留。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尚书中,满人占7席,汉人仅占5席,蒙古1席。其中外务部尚书规定由汉人担任,但在外务部尚书之上又设有管部大臣和会办大臣,均同满人担任。以“满汉不分”的名义打破了“满汉各一”的旧例,虽然以前的“满汉各一”也是满族人掌实权,但毕竟在形式上满汉平衡,汉族官员心理上更易接受。形式上的“满汉平衡”被打破,汉族官员的心理平衡也随之打破。几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不少汉族督抚宣布独立,可能与此不无关系。
这次官制改革,各路权贵、官员你争我夺,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激烈,导致政坛严重分裂。而且,还使人对清廷是否真准备立宪大起疑心,甚至有立宪派直斥其为“伪改革”、 “徒为表面之变更”。
事实无情地说明,这次行政改革的效果与清廷初衷正相反,彻底失败。不仅没有缓解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
晚清这两次本想以行政改革推动或导入“宪政”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失败,适足促人“逆向思维”:原以为行政改革只是局部性变革,阻力肯定要小于全局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当更容易,其实未必。行政改革将使某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益,而另一些部门和部分官员受损,受损部门和官员的抵制、反抗必然十分强烈。甚至保持原待遇不变,也不足以抵消无权的损失,对官员来说,权力大过一切;要裁撤一些部门和一些官员自然难上加难、难以执行。争斗的激烈程度,可能并不小于政治体制改革。近代以来,清王朝一次又一次想以并无实效的行政改革代替政治体制改革,殊不知成本和代价其实更高;而最高的成本和代价,则是耽误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而导致自己垮台。
(摘自《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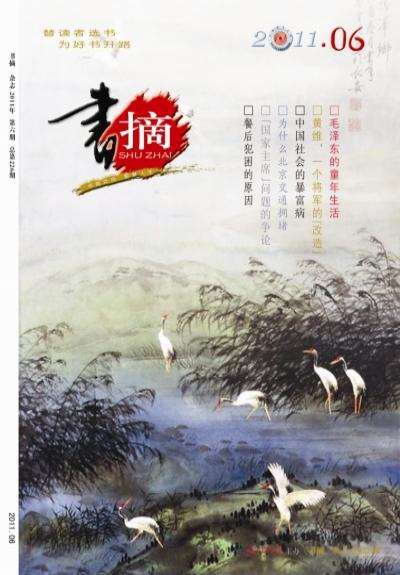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