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里老穆说他想去一趟无锡老家走走,盘算着过了中秋才回来。两三年前那篇《初八琐记》我写过老穆,写他是世外闲人,平日山居简出,只等星期天背着布包进城买书看朋友。二〇〇六年二月十二日农历大年初八,何孟澈医生下午来看我,送我北京傅稼生先生刻扬无咎蜡梅的紫檀笔筒,晚上老穆正巧来喝茶,看了笔筒还要看伊秉绶的梅竹书画扇子,一时感慨很多,说了许多人生花开花谢的无常。那天我家阳台上金桂白兰开得矜持,满室幽香,老穆说他渴念梅花,惦记笛声,害我深宵赶写《初八》一文收笔格外戚然:“梅影深处的牧笛渐去渐远,悠忽衰迈的竟是老穆和我了。”
无锡回来他带了两张乾隆宣纸送给我,说是他小时候老师的家人放出来的旧藏,连老师那件明代仿定窑白釉印池他也买回来了:“贵了些我并不介意,杜翁是恩师,难得临老我还有缘珍藏他案头的文玩,感动得真想哭!”老穆打开布包拿出锦盒里的印池给我品赏,瓷色如月,暗雕如绣,池中老印泥还闪着艳光,真是雅致的旧梦。我小心盖上池盖扣好锦盒要他收好:老穆满眼泪影,双手捧着一杯龙井默然无语。
人生遇得着一两位又严又慈又博又真的老师是造化。早年,伦敦老学长爱德华告诉我说,打完二次大战他回苏格兰故乡才听说他最敬爱的中学老师大战期间病逝了。他说那位老师教历史,相貌很像一九三九年Goodbye,Mr.Chips老电影里那个老教师,课堂上他是发光的鸿儒,下了课他是亲和的长辈:“那年头我们都穷得要命,”爱德华一口喝下半杯啤酒说,“小乡镇连日常用品都短缺,我上大学身上穿的一件大衣是老师衣橱里的老古董,料子很好,剪裁挺拔,他自己舍不得穿倒给了我了!”
他说老师的小房子是他少年时代的避难所,功课都在老师书房里做,天冷了煤炉上那壶咖啡冲完又冲味道淡了还在喝,喝的是那股窝心的暖和。“我替老师整理许多图书馆书上的材料,他是John Galsworthy专家,认识高尔斯华绥本人,还写过评论《福尔赛世家》三部曲的小册子!”爱德华说他在老师坟前哭了一个下午,天快黑了师母拉着他回家喝掉老师书房里小半瓶白兰地。一九七八年师母遽然下世,爱德华昼夜赶回故乡办后事:“我让老太太葬在老师身边”。他说,“她八十七,我老师只活到五十三”。
我还记得爱德华讲他老师的书房。他很会讲故事,老师的口音也学得滑稽,他说秋天窗外梨树长出几枚青梨的时候老师总是枯坐窗前不说话,谁都不敢惊动他:“老师在给青梨上课!”村子里的人说。我小时候的英文家教老师也喜欢跟树上的果子说话,说是树木有情,跟树木说话果实会甜些,说完闭目喃喃背诵几句济慈的《夜莺》。有一回,这位英国老先生带我到他家观赏他的小花园,一株苍老的菠萝蜜不算,满园是又矮又茂密的花树,艳阳下一派高更彩笔的胆识。“你试试。”老先生摘了一枚小橘子给我,入口润得要命也甜得要命,到老我再也没吃过这样奇怪的橘子。
林海音先生有一年说起她很想编一套琐忆师门的丛书,徐讦先生听了赞好,也许找稿约稿殊不容易,纯文学出版社好像没有编成这套丛书。新一期台湾《联合文学》出林文月专辑,林先生的学生何寄澎写的那篇《师门琐忆》该是林海音想要的文章。何先生说林文月那时节住在台北复兴南路的巷子里,两层楼的洋房,前院有个小小篮球场配个斑驳的篮球架,房子一楼是客厅、饭厅、厨房,右侧楼梯通往二楼,楼梯旁一间僻静的斗室是林老师的书房,书桌周围满壁皆书:“我常于午后探访老师,往往就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无所不谈。老师的书桌永远堆满了书籍、资料、卡片、稿纸,和所有的学者、作者一样,这样‘凌乱’的书桌,格外让人能定静下来。”林先生巷子里这所旧居我去过,十足老台湾古朴温暖的家园,那次吃过林先生烧的好菜还清赏郭先生珍藏的美玉,大家玩到深夜还舍不得走。过了好多年听说捷运施工政府收购拆除,林先生一家先是迁进新建的大楼,不久她退休随郭先生移居美国。何寄澎今年也六十多了,是台大中文系教授。
薪火这样传承确是动人的风景。老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家见过我的老师亦梅先生不禁又感动又激动,说老先生两道白眉毛已然一尊岸然的道貌,崇岭似的一管鼻子配上几朵老人斑,那是宋词里的一幅晚烟细雨:“信不信由你,”他说,“亦梅先生那股仙风四分像我的杜老师,端端庄庄坐在门口仿佛不屑多看世间几番蝇营几番狗苟!”听说杜老师原是他们学校的校长,一九四八年退下来在家里收了不少学生教古文,一心栽培老穆这个又用功又有天分的苦学生,替他交学费买课本还要补助他家的生活,天天要他到家里听课。老穆跟了老师三年半,初中还没有毕业逃来香港,从此师生通信十多年。
“杜老师家里其实也不富裕,残破的楼房只剩二楼书斋是老师的乐园,大冷天我去书斋上课,老师总也不忘从抽屉里拿出棉纸包好的一枚烧饼给我充饥,天天如此,怕我冷,怕我饿。”老穆一边回忆一边痴痴看着印池。他说这是老师案头朝夕相伴的文玩,政治运动紧了立刻放进饼干铁盒里埋在后院桂花树下,松了又挖出来,杜老师一九六六年下世,总算避掉“文革”的折磨。“那些乾隆宣纸旧报纸包着塞在床底下塞了几十年,老师显然舍不得用,临别给我写的那张《五柳先生传》用的是荣宝斋的民国旧宣。”那天晚上,我带老穆走下斜坡去吃四川馆子的小菜,他嗜辣,辣椒吃饱了人好像也没那么善感了。饭后陪他在车站等公共汽车的时候他悄声念了两句诗:“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车子来了他还回头补一句,“余英时给老师钱穆拜寿的诗!”
(摘自《青玉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定价:4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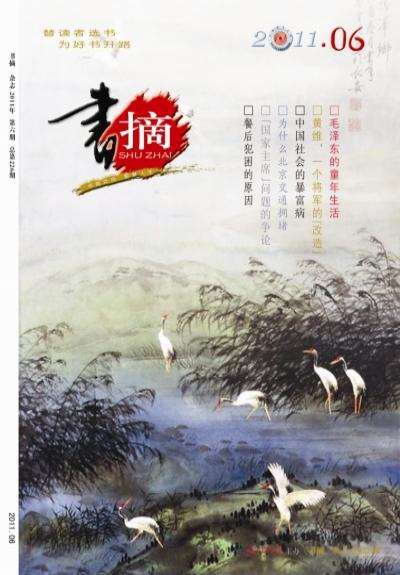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