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坚信,舞蹈就是二十世纪的仪式。”
——莫里斯·贝嘉
初到北京舞蹈学校
火车启动了,十一岁的薛菁华这才有了离家的感觉,随即哭出声来。一个孩子的哭,提醒了车上所有的男孩和女孩,立即加入进来,哭声响成一片。
车轮声响让他们意识到,真的要离开父母了。而奔赴的目的地北京,到底是什么样子,他们谁都不清楚。“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上有个毛主席像”,这是生长于上海的薛菁华对北京的所有想象。
薛菁华进入北京舞蹈学校是在1956年,是该校招收的第三批学生。那时候,十六岁的白淑湘已经在这里练功两年了。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 招收了首批学生,白淑湘便是其中之一。
视芭蕾为终身事业的赵汝蘅,最初只是因为在天津中国照相馆看到了一张小女孩穿着小裙子劈叉的照片,便来到舞蹈学校。关于芭蕾,她真正的认识始于练功。穿着小背心、小裤衩,站在练功的教室里,赵汝蘅立刻感觉到那种离开家的自由,“这太吸引人了”。
后来跳过“四小天鹅”、“吴琼花”的钟润良,排练的第一支舞蹈是《跳绳》。苏联专家伊琳娜要求全部用脚尖,带着她们在教室里来回跑。一天练下来,钟润良的脚和鞋基本粘在一起了。伊琳娜帮她脱下鞋子,告诉她不要怕,到食堂拿一个生鸡蛋,用鸡蛋膜贴在伤处,晾着睡一夜,第二天继续练。 当白淑湘、张婉昭、钟润良等都可以穿上脚尖鞋,能够半脚尖、立脚尖之后,比她们小一些的薛菁华将她们视为偶像。后来,当薛菁华开始练的时候,才知道有多痛,痛到没感觉,白袜子变成了一团红。
芭蕾舞演员对练功是既恨又爱。有一次,赵汝蘅的姐姐来学校看她,恰遇苏联专家伊琳娜正在给她们排练第一个实习作品《小鸡舞》,要求她们不断地练习半脚尖。做不到位的时候,老师会打骂。姐姐见此情景,就要去告这个学校的老师打人。赵汝蘅赶紧阻拦:“千万不要,老师打我,说明喜欢我。喜欢我,才这么严厉地对我。”
把白淑湘等人对练功的回忆拼凑在一起,就是一个芭蕾舞演员和着血的成长路程:脚尖磨破,带着伤继续练,一层层地结痂、生茧,最后形成厚厚的茧;脚趾甲脱落,生新趾甲,趾甲盖由软到硬,慢慢向前生长,坏死的趾甲脱落。期间,经受着疼痛难忍到不知疼痛、最后疼痛减弱的滋味,“那是只有舞蹈演员才能明白的滋味”,每一个演员都是在疼痛中最终实现芭蕾梦的。
中国第一代芭蕾舞演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女孩子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而男孩子多出身贫苦,看中的是舞蹈学校管吃管住的优越条件。
无论是懵懂还是清晰,这些孩子日后成为了中国第一批专业的芭蕾舞演员,创造了中国自己的芭蕾形象和芭蕾舞剧。
白淑湘
1957年底,《天鹅湖》正式排练。苏联专家在学生中挑选了三男三女,后来一人分饰白天鹅、黑天鹅的白淑湘便是其中之一。
还没来得及体味被选中的惊讶与兴奋,白淑湘便投入到紧张的、日复一日的排练中。对于她来说,最大的难度是要练黑天鹅和白天鹅两种功夫。白淑湘把黑天鹅喻为京剧中的刀马旦,白天鹅喻为青衣,颇为贴切。黑天鹅妖艳、妩媚,气质上要有诱惑力,因此要练力度、耐力;而白天鹅奥杰塔又是截然不同的轻柔与美,要展示一种抒情的、柔和的内在功夫。 白淑湘不会忘记这一天。下午在天桥剧场彩排,演员们中午便来了,把小白纱裙缝好,放在一边,躺在后台的毯子上休息。晚上七点,演出准时开始。对于演员来说,最紧张的便是上场前在侧幕等待的那一刻。白淑湘说:“出场之前,不要想我是白淑湘,我要去演白天鹅,就想我是白天鹅。当然,也担心舞蹈技术,脚尖千万别滑了,别摔了……类似的问题想很多。后来,我就不想这些,就想情景吧。”
最终,没滑没摔,《天鹅湖》第一次公演成功。由此诞生了中国舞蹈学校自己培养的第一位白天鹅。
演出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上台和专家一起坐着小板凳与演员合影。
白淑湘是《天鹅湖》的第一位主演,也是吴琼花的第一位扮演者。要从《天鹅湖》的四场,一下子提高到《红色娘子军》的六场,而且对打、开枪、射击等等动作繁杂,白淑湘的体力消耗相当大。不过,新奇的感觉远比排练的艰苦更吸引她。白淑湘说:“世界上还没有在芭蕾舞台上拿枪、拿刀的女子。而且我是中国人,演中国人自己的故事肯定没问题。”
1967年,白淑湘,陷入了一种无法想象的境遇。“我是第一个演娘子军的,当时觉得挺荣幸,但没想到演完这个就给我打成反革命了,不让上台,就天天挨斗。”白淑湘这样回忆当年。有一天,她刚走进礼堂,后边迅速站起一排人,大声喊“反革命分子白淑湘罪该万死,反对毛主席、江青”。
白淑湘被打成反革命,据说与两件事情有关联,这两件事集中于一个理由:得罪江青。
1965年初,在上海连续十场的演出,刘庆棠和王国华饰演洪常青,女主角由白淑湘跳晚场,钟润良跳日场。一次日场演出,中芭的院长、团长陪着江青在前排,白淑湘坐在江青的后边陪看。中场休息的时候,江青到休息室,白淑湘没敢进去。演出结束后,院长、团长送江青上车,白淑湘觉得自己不是领导,就不必去了。罪过就在此,不进休息室,白淑湘不打招呼,江青离开,白淑湘也没主动去送,“这架子也太大了”。
更严重的一次是,白淑湘“竟然卸了江青为她化好的妆”。对这次“事件”,白淑湘记忆深刻:“在小礼堂,化妆师王师傅已经给我化得差不多了,江青进来了,我赶紧站起来,她就让我坐下来,她坐我旁边,要给我化。拿起笔,她又站起来,我立即跟着站起来。她让我到另一边去,然后给我化,还说,好久不化了,还是你们自己化吧。然后化妆师就继续给我化。事实上,她进来的时候,基本已经化好了。化好后,跑去给江青看,她坐在沙发上,我就在她面前,都快跪下了。她说,这是谁化的啊?然后就把化妆师叫来说,我们合作得很不理想啊。回过头来又对我说,你会化吗?当时,我们也没在意,就说,会一点点。她说,给你半小时。我就赶紧跑回去卸妆。化妆间的人并不知道,以为是江青给化了,我自己回来就卸掉。那时候,全团的演员都化好了,就等我一个人。一个化妆师已经哭了,后来说是我给气哭的,但重新化一遍是江青要求的,应该是被江青气哭了。定妆后,我又给江青看。在定光区,她让我往前,我就往前,她说往左一点,我就往我的左边。她在我对面立刻就停下来说,怎么连左右都不分啊?虽然最后她通过了,但是第二天我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吓死我了。以后就不让我演了。”
就这样,白淑湘一夜之间被打成反革命。
薛菁华
1963年毕业的薛菁华,直接进入了芭蕾舞团,而且能够参与《天鹅湖》和《巴黎圣母院》在上海的演出,虽非主角,但已是非常荣幸与满足。因为刚进校的时候,十一岁的薛菁华身高一米四九,外号“薛大个”,成年后达到一米六九,为此,她曾一度怀疑自己不适合跳舞。1957年,苏联莫斯科大剧院来中国演出,主演之一普列契斯卡雅身材非常高大,但她在舞台上音乐节奏准确,舞姿潇洒,动作有力度,尤其把黑天鹅的阴毒、刁钻表现得非常突出,这让薛菁华茅塞顿开,甚至直接为她之后塑造吴清华的形象提供了参考。
在《红色娘子军》创作的时候,薛菁华原本演的是黎族舞的领舞。突然有一天,李承祥、肖慎团长把薛菁华叫到办公室:“薛菁华,给你一个任务,一个星期内把连长的舞蹈学会,准备上场。”
惊讶之余,薛菁华觉得这太困难了。出了团长办公室,她两腿发软,不知道怎么办好,一个星期就要上场,急得哭都哭不出来。后来薛菁华才知道,被选中演连长,是因为在此前的一次审查中,首长发现个子高大的薛菁华,便向团里提议:“这个孩子个子高大,能不能跳连长呢?”
审查的那天,薛菁华紧张得无以复加,感觉牙齿里面冒酸水,不停地想上厕所。领导们在身边不住地鼓励,给她念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她感觉到极大的安慰,当音乐响起之后,紧张感稍消退,上台后跟着音乐就一段一段地跳了下来。
终于完成任务,大幕闭合,薛菁华准备卸妆,远处一个高大的身形伴着洪亮的声音喊“薛菁华”,原来是罗瑞卿大将。“我当年就是连长,我的连长就是这样的。你很好,很像。”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第一次演连长,得到了首长的肯定,薛菁华知道自己塑造的这个角色与部队中连长的形象贴近了。演出后的座谈会上决定,连长以后就由薛菁华来演。
1965年在上海演出后,当过红小鬼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的肯定,再次激励了薛菁华对连长这个角色塑造的信心。之后的几年,薛菁华在演出中不断琢磨连长这个角色,她成为铁打的连长,身边的吴清华却流水般轮换,她都陪着练、跳。她专攻连长,从来没想过去演吴清华这个角色。
有一次,天桥剧场演出之后的座谈会上,研讨剧情与不同舞蹈片段的结合与变化,忽然周总理说:“薛菁华,你能不能演吴清华?”
薛菁华非常惊讶,当时便本能地站了起来:“不行,不能。”
总理问:“为什么不能呢?”
薛菁华回答说,有三点不能:第一是个子太高;第二是基本功还不够成熟;第三是身体不好,体力上不够跳主要人物,更何况吴清华的舞蹈不但多,而且表现也十分激烈。
总理当时没有表态,薛菁华和吴清华第一次联系在一起的事情就算过去了。之后隔三差五地审查,又有一次提议,都被薛菁华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第三次的时候,提议“连长与吴清华两个角色对调一下”,薛菁华又急忙说:“不行,不行,连长要高一点,吴清华要矮一点。”她话音刚落,空军司令吴法宪接过来说:“为什么啊?我个子就很矮啊,但我是司令嘛。所以连长也可以矮,吴清华也可以高嘛。”大家全笑了。
即便到这个时候,薛菁华认为毕业刚两年的学生,能胜任第二女主角已经是很大的挑战了,因此从各个角度考虑,依然坚决认为自己不适合演吴清华。
有一天,薛菁华接到通知“到团长办公室,找你谈话”。到了团长办公室,领导说:“今天给你个任务,准备一下,用一个月的时间,把吴清华排完。”随后领导又给她念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语录……
1971年元旦,中国第一部彩色芭蕾舞剧电影《红色娘子军》全国上映。薛菁华也因吴清华成为上世纪70年代红透大江南北的“芭蕾舞明星”。
影片拍摄完成后,芭蕾舞团送戏下乡的同时,经常会带上电影拷贝,白天现场演出,晚上为群众放电影。因为电影的放映,《红色娘子军》成为全世界观看人数最多的舞剧。
表面上,薛菁华演吴清华,在老乡的心目中是一个形象高大的英雄人物,是他们最喜欢的人物。但是,在背后,薛菁华还得做思想检查。
在电影拍摄过程中,北影厂的导演、摄像也是在不断地创新、完善。拍摄到最后,回头看序、第一幕,黑丝绒幕的背景与之后的灯光、幻灯等相差很多,提议重拍。剧组开会讨论,没有结果便汇报总理。总理组织研讨会,剧组成员,刘庆棠、于会泳、浩亮等皆在场,坐在后排的薛菁华忽然被提问,对于是否重拍发表意见。薛菁华便表达了赞同北影厂重拍的提议,可以使得电影前后统一。最后,总理说:“就这么决定了,序、第一幕重拍。”
薛菁华根本没想到,她的意见与刘庆棠的有出入,刘以团里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为由,不太同意重拍。会后第二天早晨,薛菁华拿着餐具去食堂,准备用早点,一踏进食堂的门,抬头一看,吓了一跳,满食堂都是她的大字报。她吓得直哆嗦,饭也不敢用,便哭着回了宿舍。
“下乡的晚上,躲开老乡的屋子远一点,在汽车上面,披着大衣开始念自己的检查。”薛菁华过着台上台下两种人生,在台上,吴清华醒悟、勇敢、坚强地走上革命道路;在台下,薛菁华反省、检查、受批判。这是当年中芭每天必须经历的事情。
1972年2月23日,《红色娘子军》为访华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演出。作为国家任务,薛菁华万分小心,也异常兴奋,吃好、睡好、练好,做好一切准备。她清晰地记得自己的这场演出中的各个细节,现在回忆起来,她依然欣慰,是因为这场演出是所有演出中最完美的一场,而且这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红色娘子军》的全剧演出。 此后,薛菁华因病有整整五年的时间离开舞台,而且是每隔半年休整,时间跨度是十年。
薛菁华恢复练功的时候,肌肉已经退化到和普通人一样了,最大的感触就是力不从心。一切从头开始,像最低年级的学生一样,从第一个动作开始练,从基本功练。加强运动,从走路开始,到跑步、游泳,增强肺活量。先在家里练到基本可行,然后才到教室做第一个动作。心中想的就是一定要上台,不一定跳《红色娘子军》,即便是个小角色都好。终于,薛菁华能够重新登上舞台,在《杨开慧》中跟着跳一个群舞。即便如此,薛菁华依旧是如愿以偿的心情,她说:“那天,比我跳所有的舞都开心。以前都是替补,或者给我任务,我去完成。这个不一样,是我自己努力要做到的,而且如愿了。”
(摘自《读库1004》,新星出版社2010年9月版,定价:3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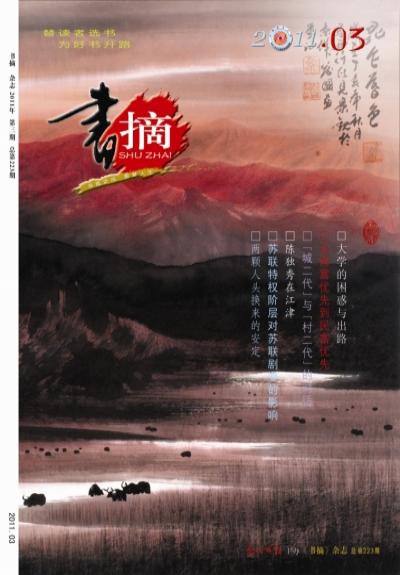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