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实在话,从小到大,无论是哥哥还是我,与父亲交流并不多。我们小的时候,他整天都忙,顾不上和我们说什么,就连喝酒、吃饭的时候也常是边喝、边吃、边看书看报,不怎么理睬我们。等到退休,不那么忙了,他喜欢一个人看书,看电视、喝酒,吃饭也经常与家里人不同步,就像我女儿上小学时在一篇日记中写的“我们吃饭的时候他睡觉,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吃饭”,在一起说话的机会不多。或许他觉得我们对书、对他喜爱的出版工作知之太少,和我们没什么可说的。只有当同事、朋友来到家里,无论年老、年少,聊起和书有关的事,他才兴奋起来,话也特别多。
记忆中,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学业很少过问,顶多是学期末看一看成绩册,即便哪门功课成绩不大好,也未见很着急。完全不像我们这一代人和现在的年轻父母们,对子女的学习那么上心。可能他们认为学业方面的事自有学校和老师操心。
不过父亲对我们的成长并非不关心。记得上小学之前,每晚睡在床上,父亲都会给我讲一段《格林童话》或是《安徒生童话》中的故事。他还给我订了《小朋友》和《儿童画报》两份杂志。那时儿童读物品种很少,有条件订阅的人家也很少,这两份杂志成了我和小伙伴们共同的精神食粮。
20世纪60年代初,我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则有关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激起一场全国上下学游泳的热潮。父亲在那个时候学会了游泳。接着他就兴致勃勃地教我游泳。那年暑假里,他先是让我在家把脸泡在脸盆的水里学憋气、吐气,然后又利用每天午休的时间,带我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游泳池教我游泳。就这样,这个假期里我也学会了游泳,教练就是父亲。
对我们课余做些什么父亲也不大过问,但是对看不惯的行为他是要说的。1966年我初中毕业那年,发生“文革”,学校停课,没事可做,同学们有时在一起打扑克牌,我不会打,于是买了一副牌学着打,被父亲看到,立刻遭到他的批评。他说打扑克太浪费时间,有时间应当多看看书、练练字。那以后我就没再玩过扑克牌。
父亲也反感吸烟。1968年,我下乡去了东北的黑龙江农场。1969年,哥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内蒙古赤峰市工作。同年,父母亲去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一家人在三处,靠书信保持联系。可能是为了省时间,父亲写给我和哥哥的信有时用复写纸一式两份。有一次父亲的信中有劝哥哥不要吸烟的内容。想必那时父亲发现哥哥学会了吸烟。哥哥听进了他的劝告,没有再吸。
那时父亲的来信中有时还夹带着先前我写给他和母亲的信,里面的错别字和病句都被他标出并做了修正。可能是出于做编辑工作的职业习惯,也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在文字方面给我一些指点。
二
父亲爱书,爱到了吝啬的地步。家里书架、书柜上的书,都是他一手摆放的,哪本书在哪里他非常清楚。如果发现有人动过他的书,就会追问。我每次从书架上取书看都是小心翼翼,尽量让书籍摆放保持原样,但是他总是会发现,不知道他做了什么记号。
有的人向他借了书看过不还,时间一长记不清是谁借的,找不回来,他很心疼。于是他用纸订了一个借书本,记录哪本书被谁借走了,连家里人也不例外。从他那里借书看,过些天他就会催要。有时外人借书他忘了登记,事后想不起是谁借的,就会一遍遍追问是不是我们拿了。所以我宁愿到单位的图书馆借书看。
他倒不是反对我们看书,只是担心书被弄坏、弄脏。借阅他的书有很多规矩:不准把看到中途的书打开扣着放,不准卷握着书看,也不准折书页角。所以每次看他的书我都包上书皮,准备一个书签,一时找不到书签就用纸条代替。后来从图书馆借阅书,不论是新书旧书,我也是这样做。
除了爱书,父亲还有很多喜好,例如,看电影、听音乐、吹口哨、收集有趣可爱的小玩意、养金鱼、做爱吃的小菜、种花草、集火花(火柴盒上的贴画)。走在路上,他嘴里时常吹着歌曲。他曾收集了几大本火花,有时还与其他火花爱好者通信交换各自多余的品种。这几本火花集前些年送给了南京一位火花爱好者。
父亲喜爱孩子,特别是抱在手上的幼儿。见到小孩子他就很开心。哥哥和我长大以后,父亲经常把住在近旁的年轻同事的孩子抱到家里来玩。1981年我的女儿出生,产后最初两个月住在父母家,父亲时常抱着我女儿哄逗。那时还没有纸尿裤,有时被她尿湿了衣裤,父亲不但不着急,反而高兴地说,再往后就没机会闻到小孩子的尿味了。
父亲不喜欢体育活动,从不主动锻炼身体,叫他出去散步从来叫不动。不像母亲,每天一早就到室外散步、打太极拳。游泳是他唯一喜欢过的体育运动,1972年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后,晚上下班后他还经常去游泳。直到后来患了一次比较严重的中耳炎导致耳膜穿孔,医生告诫耳朵进水中耳炎易复发,那以后他不再游泳,也不参加任何其他体育活动。
但是他喜欢看足球比赛。离休后,每逢足球世界杯赛,他都会守在电视前整夜地看。其实他并不懂足球比赛,只要看到进球就大声叫好,也不管进球的是哪一方。
三
父亲的很多朋友说父亲慷慨好客。
他有时给报刊投稿,文章刊登后能得到点稿费,每次拿到稿费,他就请上几个老朋友或是小朋友,找家小馆子一起吃顿饭。离休后,他每到月初都要张罗三联书店的老朋友们聚一次,吃吃饭,聊聊天,每次都是他用自己的稿费付账。
母亲有位侄女,从江苏远嫁到广西,生活不宽裕,母亲生前每到过春节会寄些钱给她。2000年母亲去世后,每年春节,父亲都替母亲继续寄钱去。
父亲的单位每年最后一个月都给职工发双份工资。父亲对家里雇用的保姆也实行这个政策,每到年末也给双份工资。有一年他到香港去访问,回来时给家里每个人都带了份礼物,其中也有买给保姆的毛线衣。
从这些事看,父亲是慷慨的。但是对家里人,他有时又小器得很,一些吃的、用的东西,喜欢独自享用,不让别人碰。
朋友送给他的巧克力糖、奶酪、点心,他都收得好好的,自己一个人慢慢吃,只是在偶尔高兴了的时候会拿点给孙女或外孙女吃,但是如果孙女们自己拿着吃,他就会说:“我还要吃呢,你们留点给我。”不像多数老年人,孙子辈的要什么给什么。因此,哥哥的女儿和我的女儿饿了或是馋了,会向我母亲要吃的东西,从不向他要。
哥哥的女儿喜欢吃奶酪,母亲有一次拿了些别人送给父亲的奶酪给她吃,父亲发现了很不满。母亲说奶酪已经放了很久,再不吃会坏的,父亲说:“坏了我自己会扔掉!”他有时就是这么不讲理。
朋友来了,他会忙着泡茶、煮咖啡招待。可是他的茶叶、咖啡家里人是不准随便动用的。就连招待客人的玻璃杯、茶具,他也不让家里人用,怕打破了。
女儿小时候,我先生给她买过一只漂亮的玩具雪球,她很喜欢,父亲看到了也喜欢,拿去放在书柜里,从此只能隔着书柜的玻璃窗看,不准拿出来玩。以后女儿一看到外公走过来,就赶紧把手里正玩着的小玩具藏起来,生怕被他收去。
父亲的酒就更不让人碰了。有段时间我们一家与父亲住在一起。我先生出差带回在飞机上没有喝完的红酒,父亲看到问也不问就收进酒柜,我们如果喝一点,他会说:“你们为什么喝我的酒?”总之,他的东西我们不可随便动,家里别人的东西只要他看上了,也成了他的。
与父亲相处时间不长的人都说他是个和气、幽默的老头。但是家里人却感到他很不好说话,脾气大,急躁,任性,固执。
他要我们帮他做事时,不管我们正在忙什么,都得马上先办他的事,行动慢点,他就在那里不住地唉声叹气。
他中年时患上气管炎(真正的气管炎,而不是“妻管严”),逐渐发展为肺气肿。医生一再叮嘱要避免受凉感冒,因为感冒会导致肺气肿进一步加重。每到春秋季气温变化较大时,我们都提醒他注意添衣保暖,不要着凉。但是他偏偏很贪凉,该加衣服时就是不肯加,几乎每年春秋季都要大病一场。
最令我们伤脑筋的是,他生病了不肯去医院。等到病由轻拖到重,还要劝说一两个小时才肯去看病。住进医院不等痊愈又天天吵闹着要出院,连医生都拿他没有办法,只好在出院单上注明“病人自己坚持要求出院”。
家中的事一般是他说要怎么办就得怎么办,不容商量,如果不照他说的做,他就会发火。他认准的事,家里人很难说服他改变主意。
1994年,因为原来的住所拆迁,父亲搬入方庄一座楼内第十层的单元房。这套房子南北两面都有阳台,北京经常刮大风,阳台上满是灰沙,加之楼层高,晾晒的衣物也容易被风卷走。母亲和我们都主张给阳台加装玻璃窗,而父亲坚决反对,理由是《新民晚报》上有篇文章里说过,封了阳台会妨碍居室通风透气,他完全没考虑南北方在气候上的差异。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向他的老朋友求助,请他们帮忙说服父亲,当然不能让父亲知道。后来听了一位老朋友的“建议”,他终于同意给卧室外面的阳台加玻璃窗。往往就是这样,同样的事、同一个道理,家里人对他说他根本听不进,而从老朋友口里说出来,他会欣然接受。
我们有时当着母亲抱怨父亲脾气不好,母亲总是说:“他这个人像个小孩子,别跟他计较。”在母亲眼里,不但我们永远是孩子,父亲也永远是孩子。
母亲对父亲极好,好到溺爱的程度。母亲比父亲年长三岁,生活上处处照顾他,什么事都依着他,迁就他。父亲喜欢吃的东西,母亲都舍不得吃,留给他,直到他吃得倒胃口。父亲喜欢每天喝点“二锅头”之类的白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副食品供应紧张,“二锅头”也难买,母亲虽然明知喝白酒没什么好处,还是到各处商店里去寻觅,有时也派我去找。
父亲要母亲帮忙做事时,不是走去对母亲讲,不看母亲在哪个房间,在做什么,只管在自己的房里“仙宝(母亲的名字)!仙宝!”地大呼小叫个不停,直到母亲听到。而母亲从不怪他。相比之下,父亲对母亲的关心和为母亲做的事情少得多。这大概也是独生子女的通病,生活上习惯于别人的照顾,不善于照顾别人。2000年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在医院里母亲的病床前,父亲流着泪跪到地上拜别,嘴里不住地说:“她对我太好了,她也是我的妈妈。”
母亲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失去了母亲的悉心照顾,没有了可以说话、撒娇的老伴,他非常不适应。白天,我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他一个人十分寂寞,除了读书、看报,只有与电视为伴。一两年之后,他的心境略好了些,又振作精神编辑了几本书,写了一些散文。
近几年,父亲明显衰老。他本来兴趣广泛,整天忙忙碌碌闲不住,但是这两年变得对什么事都很冷漠,什么事也不想做。除了上卫生间,一天到晚都睡在床上,怎么劝都不肯下地走动,与以前判若两人。过去他虽然很少与家里人讲话,但是经常与老朋友电话聊天。近年由于听力越来越差,电话也不打了。
父亲走后的这些天,我回想起来才明白,他最后这一两年整日躺着不肯下床,饭也吃得很少,实在是受疾病困扰,没有力气,没有胃口,并不完全是任性。
1994年父母搬到方庄居住时,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为了避免休息时互相干扰,他们各住一间卧室。母亲去世后,按照父亲的安排,母亲的骨灰瓶存放在她生前的卧室中,父亲也住进这间卧室,伴着母亲的骨灰度过了生命的后十年。
父亲留下遗嘱,遗体捐做医用。2010年9月17日送别父亲前,我们从他脑后剪下几小撮头发包了起来,因为遗体捐献后是拿不到骨灰的,我们把这些头发与母亲的骨灰放在一起,让他们永远相伴。
(摘自《书痴范用》,三联书店2011年1月版,定价:35.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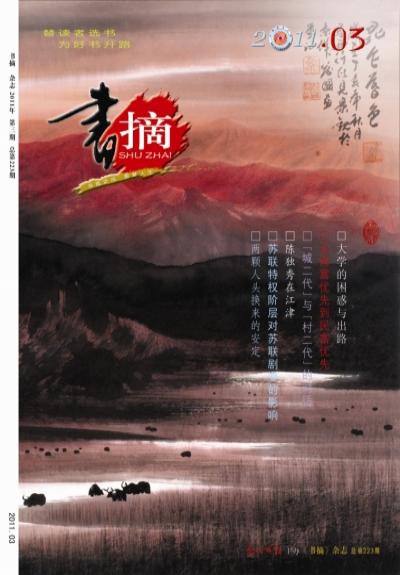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