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舞蹈圈内,不少舞者或编舞者声称“舞蹈是我的生命”或者干脆说自己“是为舞蹈而生的”,很感神秘。我则凡俗,干上舞蹈是“一失足”,不过说不上“千古恨”,干什么不是干,不必“千古恨”。干什么干着干着总会有它令人感兴趣的一面,快乐地干吧。
跳舞了
一九四九年随“三野”进入上海,是年十六岁。
解放军进上海最经典的镜头就是全体官兵睡人行道。但我们没有,总是照顾我们年纪小吧,陈毅军长安排我们住进了一座豪宅,淮海路1449号(现在是韩国总领事馆)。大开眼界:大厅端庄华美,单边的楼梯,一层又一层,一间又一间,当晚我们忙坏了,奔着上楼跳着下楼,不厌其烦地转这间房转那间房,还有密室,保险箱大得可以住好几个人呢……庭前草地大片,月色下草地又蓝又绿,小溪环绕,小溪上还有小桥,葡萄架下石桌石凳,情调得很……不过,还是睡地铺,那么多人可没有那么多的床。
没过多久,陈军长为仍年少的我们着想,要我们重新读书。全团上下都要分出去上学。有去上速成中学的,也有进音乐学院、美术学院的……
在决定我去向的那刻,我正朦朦然无所事事地从楼上一蹦一跳玩楼梯,全然不知头头们正坐在大厅一角讨论上学分配名单。我玩楼梯“噔噔噔”声惊动了头头,头头们抬头上望,哦,这丫头腿长,学舞蹈去吧。就这么决定分配我上北京中央戏剧学院舞蹈班了。
真够随意的。就那瞬间,我的一辈子被注定送给舞蹈了。
通知我时,说我的爸爸妈妈在北京呢,我的爸妈因为是第四野战军,进的是北京,六年未见爸爸妈妈了,好吧,去北京,见爸妈。
这就是我进入舞蹈这一行的缘由。
《小刀会》成名之后
舞剧《小刀会》拍成了电影,忽然满大街都是我了。
我在照相馆的橱窗里招摇,我在书报封面上拿姿作态,甚至百货公司日用品比如脸盆、餐盘,也印着那执弓挽箭的我……
这是成名成家了吧。
第二天醒来,太阳竟然还是往日的太阳。我当然也依旧是原来的我,并且依旧得起床,得去练功、排练,早饭依旧不知上哪儿对付……
进得剧院大门,忽见好朋友恽迎世正走在我前面。
换成往日我会奔过去猛地从背后箍住她双肩,吓唬她。然后两人一起去更衣室换练功衣,一起进练功房开始当日的练功。这时却拔不动两腿了……
《小刀会》的女主角原先是她,不是我。
她在《小刀会》创作初期做了一个很精彩的小品,引得排练厅一片赞叹,创作组长随即看中了她,确定由她扮演女主角周秀英。
当时我的事儿是编舞,后来大出风头的《弓舞》就是那段时间编的,还编了一些其他的舞……反正组长派到哪儿我编到哪儿。
编舞任务完成后,我当了周秀英B角,兼跳群舞,必要时还女扮男装当清兵……
决定由我担任《小刀会》电影女主角的那天很突然。当时我正大汗淋漓在练功,被通知去院部办公室。
“快点换衣服,去电影厂试镜头!”
“试什么镜头?”
“周秀英。”
“周秀英不是恽迎世吗?”
“要你去你就去!”
嗨,这等美事儿还有什么犹豫的,即刻将自己打扮起来。
去电影厂的路上闪过许多往日从电影中看来的各式各样的女主角的特写镜头,都很美。我也要上电影了,这一下可以大大美丽一番了。要知道当时连拍张照片都是很难得的事。
结果样片出来,斗鸡眼。
我居然是个斗鸡眼!一瞬间灾难临头,像遭遇洪水,斗鸡眼问题如滚滚而来的浑浆缠上我,毫无思想准备,从不知道自己是个斗鸡眼,生个肺病或者胃病即使耳聋哑巴也行,为什么偏偏斗鸡眼呀,在这拍电影当口。
那几天看人都是只看人家的眼睛了,发觉个个人眼睛闪亮神气十足,个个人都比我幸福。
不能斗着两眼拍电影,不能出这个洋相。
于是,溜出电影厂,直奔剧院二楼院部:我不要拍电影了!
院长和书记吃惊:吵什么吵!那是任务,高兴拍就拍不高兴拍就不拍?自由主义!摄影师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么,你应该配合。接着,他们命令:别在这儿磨蹭,回电影厂上班去!
到了电影厂,恽迎世搂着我,劝我,她说:不要慌,不要太夸张了,你只是右眼有点斜视,镜头是一个一个分拍的,注点儿意,我也帮你在旁边看着,不会让你出丑的。
恽迎世的劝慰是关键性的。自此整整六个月在片厂,好友恽迎世,名正言顺是周秀英A角的、眼睛又大又亮的恽迎世,专心致志地去跳群舞了,“花香鼓”中有个大特写,就是她。但凡我拍戏了,她就站在我身边,留心着我的视线,不断提醒我,不断安抚我,使我能够坚持。
电影拍完,似乎《小刀会》就是舒巧,舒巧就是《小刀会》,《小刀会》和恽迎世不搭界了。虽然她是原版她是A角她比我演得好并且她仍在不断地演。
接着我和恽迎世在舞蹈界的地位也明显地拉开了差距,我变成了全国舞蹈家协会的常务理事,接着又变成副主席,她却是普通一会员。全国舞代会副主席的我醒目地坐在主席台上,恽迎世混在台下一片人群中,我很尴尬;同行们围着我说好话,恽迎世被冷落在一边,我很尴尬;记者约我写文章,不找恽迎世,我很尴尬……
我悄悄向老书记打探,我问老书记当初究竟是什么原因要我拍电影而不是恽迎世,她是A角我是B角,她是原版我是学演,并且,她眼睛又大又亮不斗鸡。
老书记笑了,老书记笑我:又单纯业务观点了吧,党考虑问题是从大处着眼的,要突出政治,党要培养的是又红又专的干部,不懂吗?
“单纯业务观点”是当时用来批评我们专业人士的常用语,意即只想自己的专业而不突出政治。对于这样的逻辑,现在看是莫名其妙,不过当时的我们由于千百次聆听,很习惯了。究竟专业人士怎样才算是“突出政治”,没细想过,也想不清楚。
可是我怎么面对好朋友恽迎世。
我觉得在她面前我像个欺世盗名者,我掠夺了本该她拥有的。
她若就此不理我也罢,可她却一如既往地对我好,更令我惴惴不安。
举一个例子:
《小刀会》在拍电影后依然演出频繁,这时我因为拍了电影,已由B角变成了A角。那次演到外省城市,练完功放大家上街看市容。撒鸭子一般,我逛街,吃排档,东游西荡,直至天色暗下来了,才猛然记起下午是要走台的。
把正事忘了,闯祸了,走台缺主角还怎么走?
想象着剧组找不见我,走台被搅乱,每个人会有的狰狞面目,惊出一身冷汗,我连滚带跑往回赶,缩紧脑袋准备迎接劈头盖脑的责难……
谁知,进后台竟一切正常。演员、舞台工作人员、导演捧着瓷碗正吃晚饭呢。还有人与我亲切地打招呼:吃完饭啦!
这时恽迎世一把将一脸茫然的我扯进化壮间:快吃饭,吃完饭化妆。她已为我打了饭。
见我仍魂不附体,她揍了我一拳:马大哈!玩疯啦?我听周秀英出场的音乐已到却不见你出场,我就出场了。放心,没人看出来。她朝我眨眨眼,导演问,舒巧呢?怎么不走台?我告诉他,你在呢,是我想走一走台,有点生疏了得练习一下,导演信了。我很机动灵活吧。
刚要跨出门她又返回来:口径统一哦,别穿帮!
就这样在好友的包庇下我轻易过了关。
那晚演出我藉着刘丽川(剧中男主角)之死在台上大哭了一场。朋友护着我,我却无以回报。对那既成的事实我无以弥补无以挽回无可奈何。
有许多演员,因一个什么戏得了奖成了名之后,会说,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天分,是这个戏给了我机遇,感谢导演感谢编剧……云云。
我可不感谢《小刀会》。
《小刀会》给我带来的麻烦大了。
先是在心上压了如此一块大石头,时不时心里沉沉的,以后就更加糟糕。
夏衍部长救我
建国后所有运动,除了“三反五反”时因年龄小,并且每月仅九块钱包干费,反贪污反浪费实在反不到,至于反官僚,连小组长都不是,更没份。到了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就开始轮着了。
“肃反”是肃清美蒋特务反革命运动,怎么会轮着我呢?听者莫不满脸一个大问号,“肃反”干你什么事?
确实,我十一岁参加新四军,十四岁入共产主义青年团,虚岁刚够十八就入了党。父母均是革命军人中共党员。全家正宗革命派,还正宗老革命呢。按说“肃反”是和我浑身不搭界的。不过有时曲里拐弯的事不稀奇,“肃反”时揪“胡风反革命集团”,我是因为这被牵进去了。
至于胡风先生和“肃反”运动怎么就搭得上边?那我就弄不清了。
其时我二十二岁,舞蹈员一名,完全不知道“胡风”是个什么人。即使知道也不够资格认识胡风先生。
正忙着出国演出呢,那是我第一次出国,而且是印尼、缅甸、印度三个国家。问题出在这三个国家的演出并不是一气完成,之间两次在北京修整待时。说修整其实除了练练功没什么事儿。北京的同志们回家,我们上海的就到处乱玩了。鬼使神差,我玩着玩着竟玩进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大院。
后来知道那里算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支——吴祖光“小家族“的“老窝”。钻到反革命老窝里玩,自然要玩出事儿来了。
记得那些朋友称吴祖光先生为大哥,称吴祖光夫人新凤霞为大嫂,互相间称四姑娘、小弟、小妹等……大概就因为称兄道弟的所以被冠以“小家族”的名头了。其实那个小群体自称“二流堂”。
去他们那儿玩,听他们谈天说地,觉得很有趣。还渐渐由欣赏、仰慕,到爱上了其中一位在我看来是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名叫杜高,“小家族”的人叫他二哥。
那么快就爱上了?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爱作家还是爱杜高。因为从小爱看小说,总觉得作家挺神秘的,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好像真是爱上了。
待不到一个月,演出团又出发了,去印度。思想中演出完毕马上回来的,所以与杜高及“二流堂”的朋友们并无离别感,兴高采烈带上行李登机……
临上机时夏衍部长把我叫离人群,悄悄叮嘱我:千万不要写信回来呀!
我对这句“千万不要写信回来”完全没听懂。不知道夏部长为什么要这么说。
不过,夏部长不叮嘱我也不会写信的,从印度往回寄信?都不知印度邮筒什么样,邮票去哪儿买,信怎么个寄法……麻烦死了。我这个人这方面有点懒。
要不是自己怕麻烦,夏部长说不要写信就不写信啦?没这种事的,我可没那么乖。
结果,这懒救了我一把。
出国回来,魂惊魄散!
青年艺术剧院,大院还是那个大院,杜高及昔日的朋友们却如从来没存在过似地消失了。他们的宿舍里住着别人了,住着些问什么都聋哑人似的没有反应的人。
最终是传达室的老伯伯把我拉出大院,姑娘快走吧,别问了,都是手铐铐走的。
这使我迷糊起来了:青年艺术剧院那个大院存在过吗?我所见的杜高、小弟、四姑娘等人存在过吗?有那么一群秀才,被手铐铐走了……是我做的一个梦?
于我,像个梦。于“二流堂”的朋友于杜高可就不是梦了,是一个残酷的真实。
非常地偶然,三十多年后的某日我居然会与杜高在上海的96路公共汽车上迎面相遇。
那天我如平日一样挤车上班去,一步跨上车,抬眼就见到他——杜高。曾经那样温文尔雅的他,又黑又瘦又邋遢,裤腿一高一低地卷着,脚上一双廉价跑鞋,大概是怕周围的人嫌他脏,整个身躯就那么缩在车厢的拐角处。如此仓促的相见,顾不得惊讶来不及寒暄,我将一大堆问题抛向他:你这三十多年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你这是要到哪里去?
看,还是那么个急性子。他打断了我的急切,温婉地笑了。当年我对听不懂的问题打破砂锅追究时,他总是这样说:急性子,真是个急性子。笑容软化了他脸上僵硬的线条,遥远的一丝书卷气息袅袅飘来……这是一个在二十岁就有作品被翻译成好几国文字的青年才俊呀。他告诉我,三十几年都在劳改农场服刑。先是在北方而后转来南方。几年前刑满,但没地方可去就在劳改农场找了份工作,现在是劳改农场的采购员。他侧过肩头给我看套在肩上的一大捆电线,这不,到上海买电线来了。
匆匆的,一到站头他就向车门挤去,我喊:那你现在住哪里?给我你的电话号码!也不知听没听见,他逃也似地快步下车了……唉,那时“文革”虽已结束,“胡风案”却还未平反,他那处境怎么会给我什么“电话号码”呀。
这才明白夏部长叮嘱的用心良苦,救一个算一个呀。我因时间太短,除了杜高没来得及与其他“二流堂”成员有深交,而与杜高又没落下白纸黑字,就没被算作正式的“二流堂”分子,只算外围。只在回上海后开了我几天批判会。
记忆中那是歌剧院第一次开这种批判会,大家都没经验,都很紧张。我的感觉是,他们比被批判者的我还紧张,个个比我先到场,个个正襟危坐目不旁视。现在想来,他们应该都是莫名其妙的,但又必须积极发言,多困难。主持会议的是平日待我很好的我的支部书记,他也紧张,脸绷得死紧,说话都变了调。我知道,他想把会议开得像模像样些,像个阶级斗争的样子。
其实发言者都和我一样根本弄不清胡风是怎么一回事,说起胡风像在说一匹狼,至于“小家族”?那就是一窝小狼。我也是第一次经受以我为主角的批判会,很想好好配合,很想能交待一些什么。无奈,实在是知道得太少,结果一问三不知,眼看着会场渐渐松散,书记面有难色,我心里有点抱歉。但我除了听到雨果、莎士比亚外又没听到什么诸如接头暗号、暴动策划之类能耸人耳目的惊险情节或话语,怎么办?
会议一天比一天散漫,终于熬到任务完成,大家都松快了。
我更是撒鸭子般散了会就去练功房练功,呆坐了好几天,关节都快锈了,踢腿下腰满头大汗人就爽快起来。丝毫未觉着那次受批判的分量,不知道后果。
直到前几年去探望早已离休的病中的老书记(就是当年批判会的主持人),闲谈中问起:就是从那次开始我的档案有了问题了吧?入了另册成了“内控”对象了吧?评级、加薪、提干就都不行了吧?
老书记笑我:四十多年了,这才想起来呀?
同时,从老书记处才得知,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名额本来也有我的份。但因为那年《剑舞》被中央文化部选中参加国际比赛,我是编舞兼领舞,编舞倒是可以一脚踢掉的,领舞却短时间内很难替补。于是右派的名额就配给了谢容明同志。
(摘自《今生另世》,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9月版,定价:49.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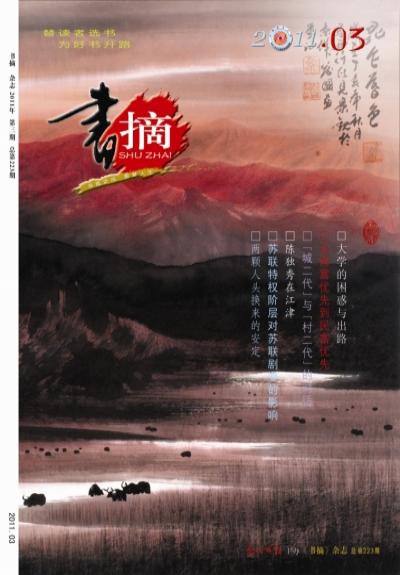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