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冯纪忠说:
与林风眠交往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我太太和我结婚以后,1952年、1953年就学画了。起初在陈盛铎画室,那时候他已经是同济的教授。陈盛铎一面教课,一面办个画室。后来我觉得她在修养方面应该再提高。我看到傅抱石的画很好,就想让我太太去南京学。后来才发现了林风眠的画,那张画是刊登在我女儿看的《小朋友》杂志封底上的,很好,我欢喜他的画。我以前不知道林风眠,也从未看过他的画。陈盛铎说:“我跟他熟得不得了啊。”因为林先生在杭州任国立艺专校长的时候,陈盛铎是法籍画家克罗多的助教。陈盛铎就介绍我们认识了林风眠。
林风眠愿意收我太太做学生。为什么呢,因为她有一张油画花卉参加过上海美展,林风眠看到过这张花卉,说这个人有色彩感。巧了,陈盛铎一介绍,哦,就是那个有色彩感的人。就收她做学生了。不过他说:“你先要学学国画。”于是林先生又介绍了她去跟张石园学了两年国画山水。另外陈盛铎那儿她也没停。
1958年我们搬离同济新村以后,经常上林先生那儿去看画,聊天。1962年搬到了茂名南路上,离林风眠南昌路的家更近。我们带着女儿冯叶差不多天天去。小孩子,尽听我们在那儿讲画,老是听,又都跟着看。我们自己是培养她弹钢琴的,她却不声不响自己画画。林风眠一看,哎,不错么。很喜欢。好的,这样就教她。教她也是随时教,随便画,同时讲这个好那个好。还教她美术史、古诗。他住的地方后面算是画室,前面他自己在那儿画,她就在后面画,画好了,就给他看,他评点一番。后来林先生又让陈盛铎教她画素描。
我们见面当然是很多了,没事去他那里坐,一起吃晚饭。有时候,我也请金经昌一块上去看画,有好多张现在刊登的林风眠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我们当然聊得很愉快。他画画是在晚上,他喜欢晚上一个人静静地画。我们在一块儿时,他拿出来的都已经是完整的了。不过他教我女儿画画的时候,是当场示范的。画画功底很重要,他的功底就是非常好。举一反三,建筑也是这样,基础一定要好,另外就是修养的问题了。我们反正是什么话都谈,有时候他画画我在旁边看看也有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风眠被关了四年多冤狱。坐牢时是不准我们见面的。当时真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抓他,是因为他曾经救过共产党员学生呢,还是什么?很难说。不过我始终对我太太说,他肯定是被冤枉的。这是我们交往多年得到的感觉,这点信任我有。林先生的夫人是法国人,上世纪50年代初她受不了这儿的情况,就走了,带着女儿、女婿。女婿是外国人。在法国他们没地方落脚还是怎么的,就到巴西去了。她们平时跟林风眠也不常通信。“文革”的时候不用说了,根本不是你想通信就通信的。在牢里更是不准写信了。
林风眠被抓起来的时候,我已经被隔离审查,关在学校里。我太太和女儿着急,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他只有一个人在中国。天凉了,听邻居说,林先生被押走的时候,穿的只是汗衫短裤,怎么办?没有音讯啊,就去他的单位找。找当然找不到了。也去公安局看守所监狱问。那个时候光这一点就不容易,因为当时的政治气氛是,有多少人赶着与他划清界限都来不及的,那以前,就有人在路上遇到都不敢点头打招呼的呀。后来公安局来电话找我太太,她才有点害怕。怎么回事啊?说是林风眠在牢里面的生活用品,每个月牙膏、草纸、衣服这些要你送,你肯不肯?那当然是愿意去的了。原来公安局看守所监狱问了林风眠:“你外面究竟有什么人可以送日用品。”他说找我们家送。
这件事,林风眠当然是很犹疑的,“我找她送等于牵连她全家”。我太太这边呢,横竖横了:“没什么大不了,他家里没人,我们不相信他犯了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既然叫我去,我就去。”所以她每个月去一趟。那是规定的,每个月只有一天,他们才允许我们到看守所监狱里去送一次日用品,不允许见面的,把东西送进去。送得进去,就知道他这个人还好着。我女儿也自己缝棉袄给他。
那个时期,我还在“隔离审查”,只剩我太太和女儿两个人在家,“文攻武卫”十几二十个人,拿了大水管铁棒,半夜三更打门,冲进去“调查”。后来为了到看守所送东西的事,我太太还在我们家街道居民的什么运动中,让人贴了大字报。我“隔离审查”被学校放出之后,也接替着去送过。差不多有四年半吧,一个月去一次,没停过的。后来,一天傍晚,林风眠突然出狱了。他从监牢里被人带回家,衣裳都没换,就赶紧走到我们这儿来,立刻就来看我们。一开门见到他,那心里头简直是什么味儿。
到了1977年,“四人帮”倒台后,批准他出国去探亲。他出国了,出去以后就想我们的孩子。那个时候她是我这个大学教授、“反动学术权威”的女儿,上不了大学的。她中学毕业,下乡插队五年,大学不能上。怎么办?只有出国。林风眠说:你们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义女嘛。所以就是他帮我女儿申请出去的。那时真是太难受了!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老实讲,女儿走了等于是割掉我一块肉。我和我太太送她去广州上的火车。一走就是十几年没回过上海。
因为林风眠知道我为了“方塔园”的设计又被人整了之后,下决心不再回来了。他担心为了逼他回国,我女儿回来看看以后会出不去。整他、整我的人太多,实在是很莫名其妙的。那时还有人大年三十晚,派人上门特地送上一本香港左派机构出版的、污蔑我们的书给我。真弄不懂他们居心何在。
女儿一走多年,我当然想她了,在当时的环境下,出国探亲是非常非常难批准的,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后来隔了四年多以后,还是因为德国洪堡基金会邀请我们全家访问德国,才再见上面了。那年,为了拿到我们出国的护照签证,我上海北京两头飞,千辛万苦地冲破各种阻扰,真是困难。可是呢,当时送我女儿出国的时候,我就想她本身只有出去这一条路了。另外,林风眠既然有这样的话,后来还写了好多信来,我女儿是他从小看大的,他老头也要有人帮帮喽。她虽然年纪轻,总还担得起些责任的。
女儿冯叶说:
小时候,感觉爸爸很亲切,特别喜欢我,很多话可以和他讲。我总觉得他太辛苦,每天大清早,差不多6点钟,就去上班了。从我们家到同济大学,路上得等车换车,要一两小时,公交车很挤,他很早就得去。我妈常常要在外边教些课,我就等着爸爸晚上回来。天黑了,看他特别瘦,拎着包。摇摇晃晃地回来。他把包放下,就开始做饭。然后我就睡了。他就又拿他的书稿,进小厨房去了。我有时候半夜会醒,就看到那厨房的门缝还透着灯光。
小时候,我也给他添了挺多的麻烦,每隔一两个星期我就发一次高烧,一烧就40度,我爸每次回来门一开,看我躺在床上,他就说,妞妞又病了,然后一量,啊,又是40度,就很紧张,每次我扁桃腺一发炎,就发高烧,那给了他很多困恼吧。
“文革”前,有“设计革命化运动”,他被整得很厉害,虽然他一生坚持不问政治,不加入任何党派,但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系主任,成了同济建筑系重点批斗对象,当时其实也只整他一个人。好不容易松一点,又来了“文化大革命”了。他又是建筑系里第一个让人给抛出“揪斗”,又斗又打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66年“5·16通知”发表那天。那一天,我的老师,也是我的义父,林风眠,拿了那张报纸来我家,说,纪忠先生会没事了,没事了。我们说为什么没事了。他说,“5·16通知”出来了,他们不会乱搞的,这个命令是挺好的,没事了,今天晚上我请客,大家出去吃顿饭。我们就等我爸爸回家,等了半天,我爸没来,我们就留张纸条,说见了纸条速到饭店来。结果一直等到我们吃完饭,他也没来。我们回了家,他才摇摇晃晃地回来了,身上都给撕得一条条的,泼的红墨水,那天他给人打得特别厉害,又游街,那就是1966年“5·16通知”发表的那天!
我还记得,还有一次天很黑了我在担心他。我特地做了个小三明治,等我爸,他也是身上被打得乱糟糟地回来,我说:“爸,您吃。”他说,我不想吃,我吃不下。这就是我记得的。
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他被隔离审查。隔离审查的时候,天冷了,他去的时候还只穿着单衣衫,我就背了两条被子,去同济大学送东西给他,那是个很差的地方,我进同济以后,就到处找我爸,有人押着我,结果发现,我爸就在路边,很瘦很瘦,就在路边扫地,拔草,收拾厕所。我看到他以后,我就告诉我爸,我给你放了一包糖,一小包花生糖在你的被子里。我轻轻跟他讲,不能给人家听到,他就跟我说,好。他跟我讲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爸好像身体特别虚弱,摇摇晃晃的,我回来好担心,跟我妈说,我爸可能撑不住了。
我的老师和义父林风眠1977年离开上海出国时,跟我爸要求说,他想继续培养我,第一,他觉得我学画画,去国外可以看更多一点,眼界更广一点;第二,他需要一个帮手。他就跟我爸爸提了,希望我能出去,但是对我爸来说,我是独生女,但我爸跟他好像特谈得来,所以我爸就同意了。后来,他准备去法国开展览,让我帮他到巴黎做一些事情。1978年我申请到了香港,洪堡基金会邀请我爸1984年重访德国的时候,我由香港跟着去了。我爸接着去开一个国际建筑师年会,在那里讲旧城改建。我记得最清楚,那次探讨的题目是公众参与,并不是旧城改建,只有他一个人讲的是旧城改建,他说的是应该怎么保护旧城市,因为这是我们上海很迫切要关注的,上海的居住条件,我当时记得他讲的好像是每个人不到4平方米吧!他说,这样的居住条件是很差的,我们要把居住的生活质量提高,但是城市的文化底蕴还得要保持,我记得他讲的基本是这样。他讲完后,有好几个国家的建筑师代表都来跟他讲,你讲得太好了,对我们很有启发。所以后来一届的题目就是讲旧城保护、旧城改造。我爸发言讲旧城保护和旧城改造,因为他早已经带着学生探讨了好多年了。他带有六批学生,做了七个毕业设计方案,都是探讨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当时确实是很迫切的,很遗憾,并没完全实现他的理想。我爸一讲到上海城市建筑,就如数家珍,这个怎么,那个怎么,好像都在他脑子里,就好像讲某某人啊,挺熟的一位老朋友的感觉。他当时跟我讲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好像也就听听而已,其实当时他的这些想法对中国城市发展特别重要。
我1978年离开中国大陆后,十几年没回来过,因为我知道,我爸在规划设计方塔园的时候,又让人整了,在市人大、市政协的会上批斗得很厉害。咱们刚刚挨过一个“文革”,跟着没多久,又要批判他了。什么他设计的方塔园的地面铺了石块也是“资产阶级精神污染”的“罪行”,是“放毒”,应该“用水泥铺路才对”等等。他写信来,特紧张,他们又斗他了。我想这对我老师和义父林风眠不再回中国大陆,实际也是很有影响的。林风眠后来,再没踏进过大陆,在他在世的时候,我也没踏进过,13年里,没再回来。
我觉得我爸爸有一种意志力和对专业的执着,他认为对的就始终坚持,他的这种态度,很让我敬重他。另外,就是他对朋友的信任。“文革”当中,林风眠被抓进牢里了,关了四年零四个月。但是我爸鼓励我们坚持每个月到牢里给他送东西,他也去送过。在那种恐怖的状况下,有人来讲,他有事,别管了。当然人家讲那话也是出于好心。我爸他平时讲话挺温和的,那时候,却坚定地大声说:“没事的!我认为他没事的!没事的!就是没事的!他是冤枉的!一定是冤枉的!”他对林风眠有那种信任。我从小就一直听他们俩聊艺术,聊历史,他们有时在厨房里,边煮饭边聊,我觉得他们互相有信任与尊重,他们对自己的专业都有一种执着的信念,互相之间有一种信任感。所以我父亲才会认为,那一定是冤狱,担惊受怕也要支持他,这点上我很钦佩我父亲。
(摘自《建筑人生——冯纪忠自述》,东方出版社2010年3月版,定价:3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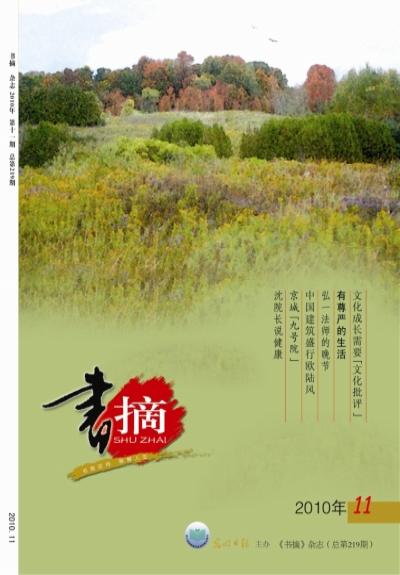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