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雪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何永飞的诗歌选集。一个“选”字,背后是诗人自我认同与外界阅读反馈之间双向的判断、梳理、总结、确证,既能够较为全面展示出诗人创作的谱系、理路、框架,同时凸显出我们对特定诗歌写作者最集中的印象与预期。何永飞的诗歌留给我的印象,一直是鲜明且独特的。要建立这种独特并不容易。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通信发达、经验膨胀、情感共享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人与人之间、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之间,可以用最小的成本、最低的能耗,产生最强烈的能量交换,形成最宽阔的内容交集。世俗生活之树因此而枝繁叶盛,但我们内在的精神景观,常常会变得彼此近似,以致在某种意义上失掉了辨识度,或者说,难以找到自我表达的独特语词。诗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树立起个体观看世界及生活的新角度,是为了找回自己的语词,乃至找回自己的语气。何永飞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他的诗歌拥有鲜明的个人风格特征,他在诗的世界里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那片神圣疆域。他的诗歌写作是有根的,因而也是有底气的。
这种底气,源自他诗歌创作的“原生土壤”,也就是云南边地的独特自然环境,以及由此生发而来的独特人文景观。雪山、村落、江河、高原湖泊、荒野生灵,在何永飞的诗歌世界里是反复获得书写、绽放出独特光彩的对象。在他的笔下,洱海是宁静而有力的,能够使“硬的肠子变软,软的骨骼变硬”;雪山景观是标志性的,“雪山高过千年,高过尘俗/就像神灯,白光擦亮硬骨”;高原上的一条河,它的源头是“英雄的一滴血”“美人的一滴泪”“我的前生,或来世”。何永飞熟悉这一切,正如他笔下写到的人们一样,擅于“在这片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山水间行走”,甚至“能给天气把脉/还能辨识哪座山有善骨,哪座山有恶相”。
这是何永飞笔下绚烂的、充满神话感的边地风景。值得注意的是,风景并非仅仅是客观、物质性的存在。对风景的观看,是一种选择性、策略性的行为动作,一个诗人去写一系列“物”、写一种特定的风景,他的“写什么”与“怎么写”,背后是充满能动性的:那是从本性、从文化无意识中不断进化而来的主观审美选择,在文本中具化为独特的感受姿态及表达姿态。何永飞对自然生灵、边地风物的书写,并不仅是向外摹画的,更是向内开掘的。许多人在评价何永飞诗歌写作的时候,都会提到“灵魂”这个词,这指的正是此种“向内”的维度,指向由自然物象中不断投射或阐释出的人内心的价值、坚守、力量和光芒。在诗人的理想世界中,“有不穿伪装的花草,有流水做的琴弦”。面对自然之神,一个人要交出内心的高傲与怨恨,以此“赎回春光、睡眠、慈悲泪/扶起踩倒的小草,原谅绊倒自己的石头”。他甚至愿意把自己的肉身交出,“将全身骨头,一根一根拆下/整齐地排列在草地上,用溪水清洗”,为的是洗去尘灰、惊恐和软弱,把洁白和坚韧“彻底还给骨头”。
作为一位在自然怀抱里成长起来的诗人,何永飞显然是在对自然的抒情和表现中,注入了其对人生与世界的根本的认知方式、表达途径、情感态度、价值判断。对诗歌而言,这一切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既是审美之“叶”也是伦理之“根”。作为一位少数民族诗人,何永飞的诗句背后,是古老而巨大的、深具民族特性的审美习惯和文化伦理。例如,我们能从中看到超时间性的、来自古典时代的那种对生死的体认方式,“碑上的青苔/是生命再次前行踏出的脚印,去向自有安排”。有的诗歌具有浓厚的民族神话色彩,人在特定文化视角下对世界及存在的理解,在其中得到了集中彰显。不同于现代工具理性支配下的分类学思维,何永飞在诗里追求的是人与自然世界、祖先世界的同一,是“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当然,何永飞的诗里,除了“古老”也同样有“当下”。他能够把高原景观同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结合在一起,“筑路人的硬骨,擂响高原铜鼓/……金色的种子,将贫困一层层撕去/将山间的白昼一层层拓宽”。《普拉河》《滇西安魂曲》等诗作,则处理了与当下生活一脉相连的地方历史。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何永飞诗歌更加丰富的层次感和多元性。他的写作,可以是“虚”的也可以是“实”的,可以是浪漫的也可以是现实的。
(作者:吉狄马加,系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主任)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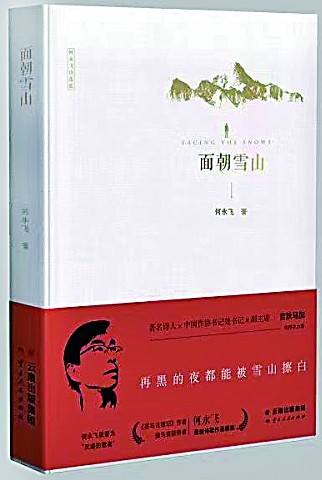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