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书者说】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物质文明,技术发达、工艺先进、产品丰富。但是由于古时掌握知识和话语权的文人阶层认为技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文献中对技艺、技术的记载微乎其微。体现在出版印刷领域,虽然我们是印刷术和印刷史的故乡,但留存下来可供研究的材料却屈指可数,这让今天的研究者时有捉襟见肘之感。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当今中国印刷史研究在学科建设、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大有建树,但限于材料,很多研究只能原地徘徊,部分现有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更甚者,因为可用材料有限,研究者或有因为对材料的不同解读而成分裂的阵营。艾俊川《中国印刷史新论》提出研究中国印刷史的“四重证据法”,犹如一声呐喊。他强调对中国印刷史的研究,要把文献记载同实物考察、科学检测和语言学词义辨析研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判断,这样才不会限于“视野盲区”和“语言陷阱”。
用实物细节辨别“活字”与“铜版”
艾俊川在肯定了当今印刷史研究的成绩后,指出了印刷史研究和任何学科的研究都存在的情况——未解决的问题和已经在研究讨论但结论仍需要进一步补充订正的问题。在他看来,导致目前印刷史研究不足之处的原因,既有缺少材料的客观因素,也有研究者“视野盲区”的主观成分。
艾俊川所指的“视野盲区”,是指对待已有材料,过于依赖文字记载,而忽视实物材料。他认为“印刷史是一门技术史,研究技术和工艺的兴废变革,与单纯的文史研究比起来,其研究对象和论证依据更加丰富,既有实物,又有文献。实物包括印刷工具和印成品,文献则包括对技术、工艺的说明和一般记载。”他特别强调印刷史研究不能缺少实物研究环节,正如他在书中用大量的实物细节来证明“活字”和“铜版”问题一样。
在“实物考察”环节,艾俊川将古籍的版本和鉴定知识融于印刷史研究,他通过古籍版面上的断裂线、板框框线的宽窄、平滑度、断裂痕迹以及文字的字形、笔画、气孔、砂眼等方面来做对比研究,以大量的实证信息判断是雕版还是活字印刷,是铜版、木板,还是铜活字、锡活字,这样的功夫令人叹服。
比如在“运用雕痕特征鉴定金属活字本”一章中,艾俊川从木头和金属的物性、木字与金属字的制作方法以及它们在纸上印痕的不同,来鉴别“铜活字本”。他以《武元衡集》为例来分析说明。
从大处看,《武元衡集》的版面版框围合严密,未出现木活字常见的遇水膨胀进而导致版框四角散开的情况。而且版心鱼尾面积缩到最小,与弘治、正德时的大黑口对比强烈。这是为了避免因金属拒水导致墨色不匀。从细处看,将文字放大,会发现一些活字的笔画被分成两段,并且左右或上下错位。如“古”字,竖画断开,左右错位;“夫”字,长撇和下面横画均断开、错位;“生”字,一竖断为三截,连不成直笔……而用木头雕刻的字,很少看到这种情况,究其原因,这是金属活字在雕刻时受物性和技术所限产生的瑕疵。同是雕刻,木字在遇到笔画交叉时,往往刀锋会通过交叉点,将相对的笔画刻断……而雕刻金属,薄刃的刀无所用力,需要使用刀凿锤击錾刻,刀凿刃厚,行迹皆为楔形,特别是金属没有弹性,无法弥合刻痕,雕刻时必须避免将笔画刻断……从这个原理看,上述《武元衡集》中活字的笔画断开、错位现象,符合金属雕刻的特点。
从艾俊川所做的研究分析,他所说的“视野盲区”,其实更像是专业壁垒,是研究者因知识和视野限于本领域不能博通的缘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越视野盲区,培养精专且博通的学者,任重而道远。
白纸黑字的记载也有很多“语言陷阱”
“语言陷阱”是艾俊川强调的第二个问题。他指出,学者在利用文字材料时,如不能对古人所言所记的真实性和真正含义进行考实,就会落入“语言陷阱”,误导研究结果。“古今语言虽有延续,语义却在不断变化,再加上文言浮夸不实、含义模糊,令人不能准确理解,容易形成误读和误解。这可分为几种情况:一是某些词语的含义古今不同,今人失察导致误读;二是古人作文喜用典故,或使用习惯语言来形容新生事物,用词不准确导致误解;三是语出多歧,对同一事物有不同记载,令人难以抉择。”
文献材料容易导致的语言陷阱到底有多危险,他举了一个文献记载中看似明确,实际却全然相反的情况。
清人林春祺制作铜活字印书,自己屡称“镌刊”“刻有楷书铜字”等,从文字上看,其铜字系雕刻而成拥有“铁证”,实际上他的活字每个字的字形高度一致,是用模具翻铸的。“镌”“刻”云云,只是林春祺沿用的当时出版印刷业的习语,并非对技术的实际说明。
艾俊川在“再论‘铜板’一词同‘监本’”中强调,明清语言中的“铜版”不是代表铜制印版,更不是铜活字版,而是代表“定本”,表示“不可更改”的意思,“铜版”与“监本”是可以互换的两个词。他大量引证明清文献和世界各地图书馆所藏古籍为例,说明在明清时人心目中的“太学”(国子监)所刻书即为“铜版”之书。由此上溯明以前那些与出版有关的“铜版”传说更是令人存疑。
在厘清明清“铜版”的“语言陷阱”的同时,艾俊川提到另外一个问题——虽然明清书坊将“铜版”与“监本”混为一谈,但并不表明那些印上“铜版”二字的书真的就是根据监本翻刻的,或者与国子监有什么关系,相反,很多标榜“监本”的书,与国子监也没有关系,它们只是书坊浮夸的广告语。
有“白纸黑字”的记载都难以作为可信任的研究凭据,可见中国印刷史研究中的“语言陷阱”无处不在。所以,要还原历史真相,必须以实证为桥梁。所幸的是,“中国印刷史研究虽存在工具缺失、文献记载不足的困难,但也有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拥有书籍等巨量印刷品。它们是印刷技术的直接产物,其墨痕印迹保存了工具、工艺的各种细节,足以在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本书正是这种研究思路指引下的著作。
考证研究历来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但读完艾俊川《中国印刷史新论》,其践行的“四重证据法”令人震撼——他做研究的证据不仅涵盖了印刷史文献,也包括了古籍版本学、语言学、博古考证及印刷工艺技术等几个专精领域的学问。以笔者之见,艾俊川强调的跨越研究的“视野盲区”和“语言陷阱”,与其说是对印刷史研究的新突破,不如说是对整个学术研究的新思路指向。
20世纪,王国维倡导的历史研究“二重证据法”已深入人心,在古器物研究中,有学者提倡“三重证据法”,即从文献记载、目力观察和科学检测三方面入手寻找证据。如今艾俊川从印刷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四重证据法”,是学术思想在新时代的进步。在多种方法下得到多重证据架起实证之桥,是学者当有的严谨态度和求真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引导我们跨越“语言陷阱”和“视野盲区”,接近和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贾雪飞,系中华书局副编审)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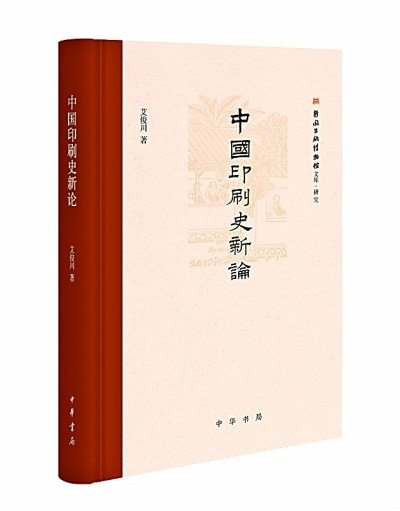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