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载:“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孔子答道:“举用正直的人,置于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了;如果把邪曲的人,置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服。”
显然,在孔子看来,人民并不是服从权势,而是服从真理,服从公平正义。把不公正和不符合正义的东西强加到他们头上,他们不会服从。权势的压服并不能改变天赋的良知,哪怕人们不得不暂时屈服,心中仍然向往光明。
同一章里,还记有鲁国执政大臣季康子内容相似的提问。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估计季康子感觉到他在百姓中的威望不高,于是有此一问:“要使百姓恭敬我,忠于我并勤勉努力,应该怎么办呢?”孔子说:“你对百姓庄重,他们就会恭敬你;你孝敬老人,慈爱子女,他们就会忠于你;你举用好人,教育不好的人,他们自然会互相鼓励劝勉了。”
关系是对等的。作为统治者,你对人民庄重而不轻佻,人民才会敬重你。你用正当的政策,才会有正当的回报。你希望人民正直而不邪媚,善良而不邪恶,坚持真理而不屈从权势,人民才会对你正直,忠诚,勤勉,上进,公正。
可是,法家不这么看。如果鲁哀公拿这个问题问韩非,韩非的回答一定是:你有权势,有国家机器,不怕人民不服从。
我的根据来自于《韩非子·五蠹》,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
他的主旨,就是要说明,治理天下,靠仁义不行,权势才行。我挺佩服他直面现实的学术勇气,但是,他这段话确实太下流了。一个人,崇拜权势,可能是他自己的事,但他把权势崇拜理论的基础建立在普通人民的人性之上,宣扬什么“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则作为民之一分子,我首先就不服他对我本性的鉴定。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可能不得不在一些特定或特殊的情境之下屈服,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心甘情愿,更不会让我们感恩戴德。屈服往往是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下的选择,如同让我们在断一指或断一臂之间选择,我们选择断一指,难道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吗?甚至还要对它给予我们这样选择的权力感恩戴德?其实,法家的政治诀窍,就是在服从之外再加一个更加严厉的选项,以使人民选择屈服。屈服者,屈辱之服也。
以一个下等君主君临天下,而“境内之民莫敢不臣”,这本来就是不正当的社会和政治,韩非对此不是批判控诉而是津津乐道,这已经显示出法家政治良知的薄弱,而把天下太平建立在人民的“不敢”上,从境界上讲,就已经比儒家低了一层,在古代,它除了建立表面上的所谓“太平盛世”外,人民不可能幸福——因为幸福不可能在人的自主选择之外,幸福更不可能与屈辱薰莸同器。在今天,这样的理论,不仅在法理上不能通行,在人民那里更不可能被放行——公正,源自人心,人心,天然向慕公正。而人心,是最后的决定胜负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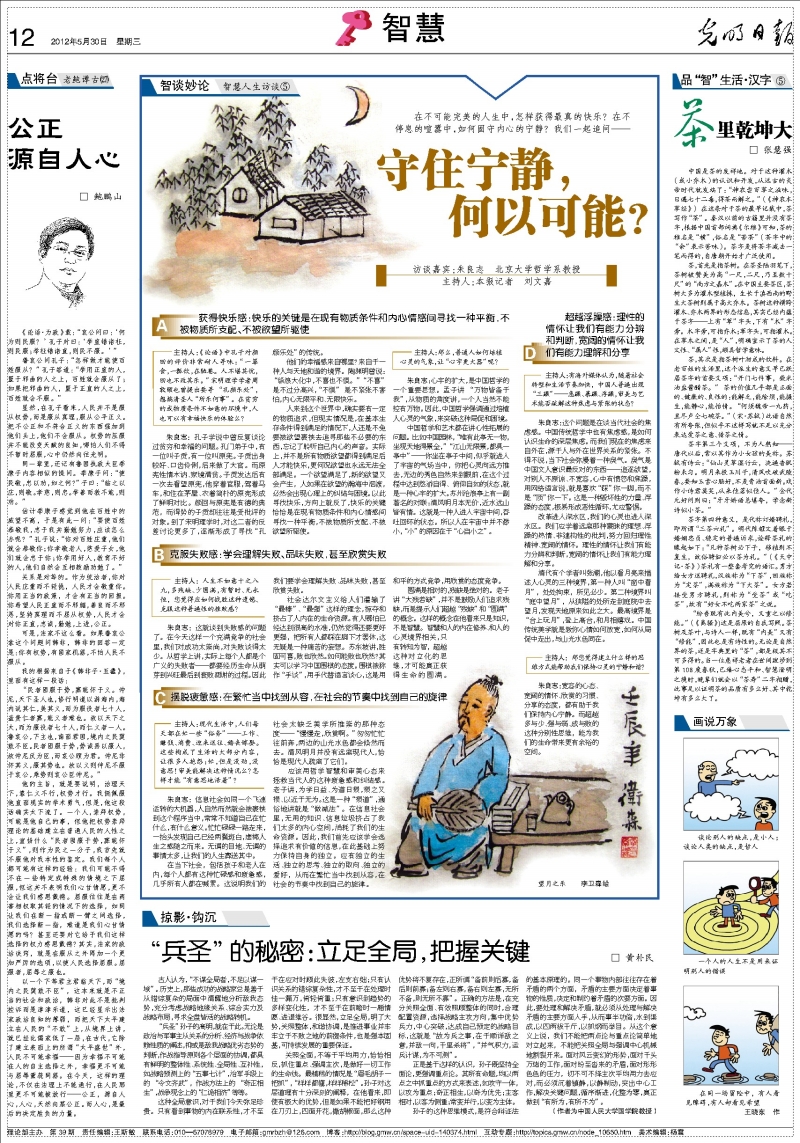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