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中有这样一类现象:“请勾践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国语·越语上》)句中“女”既指称女儿,又陈述将女儿嫁给某人的行为。该现象涉及彼此紧密相关的两个重要课题:上古汉语名动词类的区分、上古汉语名动转类现象。我的博士论文《〈国语〉名动关系研究》以此为研究对象,以先秦重要典籍《国语》为基本语料。
从博士二年级选题到论文完稿,其间自有一番苦乐。我最深的感受是,做论文是劳人心志筋骨的活儿,但遇到一个有价值又有趣的题目,在浩繁的语言材料中获得新知,又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在选题上孙玉文老师给了我很大的自由。我找他谈想做的题目,他说,有想法不错,但不能一会一个想法,想做哪个题目就要沉心去做。这种自由让我能始终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做研究。
我选这个题目最初是上古汉语中相应的语言现象对我的吸引。本科时我问孙老师怎么学古汉语,他让我好好读原典,从跟着他做本科毕业论文开始,他一直强调要从材料出发做研究。硕士阶段邵永海老师带着我们读文献,任何一段文句都要字字音义落实、语法分析到位,虽常有争议未定之处,但培养了我们对待语言材料的基本态度:重视语言材料,尊重语言事实,理论方法为语言材料服务。
博士阶段,我读上古文献时,“君君”“君国”这类现象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去和孙玉文、邵永海两位老师谈对这个现象的认识,他们鼓励我从中选学位论文题目。孙老师的音变构词研究中也分析过这类现象,例如“饭”“树”由动词转化为名词,发生了变调构词,这加深了我对这类现象的兴趣。朱德熙先生的《关于先秦汉语名词和动词的区分的一则札记》篇首谈道:
说古汉语没有词类,恐怕要比说现代汉语没有词类的理由更多。因为古汉语里词类“活用”现象十分常见,最明显的是名词和动词可以互相转化。
这也使我意识到处理好名、动关系问题是解决上古语法基础性问题、深入探究上古语法体系必须攻克的课题。胡敕瑞老师指导过两篇研究名词动用的学位论文,我向他请教选题是否合适,他认为这是可以继续深挖的课题,也鼓励我选定这个题目。
我的论文属于古汉语专书语法研究,选择专书语法研究主要基于我们研究汉语语法史的一个基本理念:“要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史必须以专书语法研究为基础。”(见郭锡良《〈古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序》)我的硕士论文《〈山海经〉语言特点及其成书年代考》也属于专书词汇、语法研究,从硕士到博士阶段,我对专书语法研究的重要性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只有踏实做好每一部重要典籍的语法研究,才能构建起古汉语各阶段的语法体系,系联起整个汉语语法史。这是学界先贤和我的老师们的理念,何乐士、管燮初等先生曾经率先力行,邵老师的博士论文对《韩非子》句法作了深入的研究,孙老师也曾想遵何乐士先生嘱咐做《国语》语法研究,因全力研究上古音而耽搁了。我选专书时便选了《国语》。
选择研究《国语》名动关系,和该问题在专书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也有关系。郭锡良先生的《〈古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序》指出:“词类系统解决了,句法结构和句式的研究也就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学界对上古汉语名词、动词关系的认识有很大的分歧。传统观点认为名词、动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词类,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例如沈家煊先生认为动词是名词的次类。因此,我的论文试图深入剖析《国语》名词和动词共性、特性,对名动转类现象进行精细而系统的研究。
想在该项研究上有所推进,必须在以语言系统性为纲的基础上做精微的个案研究,将大量个案串联起来揭示属性和规则。怎么做颗粒度小的个案研究呢?首先要对字词文句有正确的解读。在通读《国语》的基础上整理文本,确定词语的形音义、判断语法性质。这是基础工作,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却不那么容易。例如,《国语·周语上》中耳熟能详的“道路以目”,其中“目”是用作动词表示“用眼色表态示意”吗?《汉语大词典》作这样的解
释。我们仔细分析,发现“目”仍是名词。又如《国语·吴语》中“王枕其股”的“枕”能否释为“以之为枕”?它是临时性的所谓意动(或“处动”)用法还是新的动词?这要从形音义、整体句法表现的角度仔细辨析。在研究方法上,我吸收了孙老师的研究成果,将句法分析与音义研究相结合。每写完一章我就呈孙老师过目,有时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经过讨论甚至是争论后,我们对具体问题才达成一致意见。最终,我的论文以个案研究为主体,详细分析了200多组名动配对词。我们发现掩盖在名动同形表象下有不同性质的现象,包括由名动转类构造的名动配对词和依赖于语境、修辞的临时“语境词”。同时也看到《国语》中名、动范畴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名词做谓语和动词做主语、宾语有句法、语义上的限制。
论文提交答辩后,虽然得到答辩委员的认可和鼓励,但我自知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于是博士后阶段也继续做上古汉语名动关系研究的课题。学位论文可以体现我们的学术修养和耗费的精力,实际上这种学养来源于一路上带我们问学的诸位先生们。在学养和理念上的传承,是我们把学问好好做下去的动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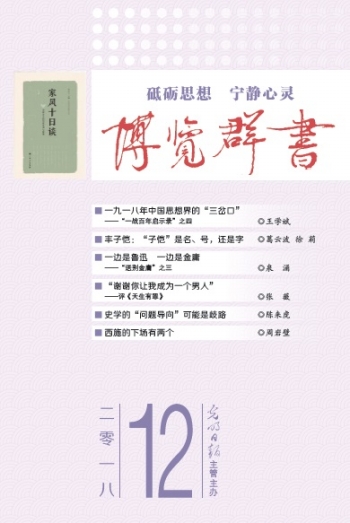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