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那是2007年,我在硕导骆瑞鹤老师的带领下,借孙老师在武汉开会的机会,第一次拜见了孙老师,并表达了我想考博的愿望。一路走回珞珈山庄,我说我正在整理谐声字,孙老师用他特有的语气提高了语调说:“好!”本来对考北大还忐忑不安的我,顿觉好像被注入了一股真气,信心大增,2008年能够顺利考入北大,离不开当初孙老师的肯定与鼓励。
但当我成了孙老师的门下弟子,跟孙老师提博士选题的时候,孙老师却让我先放一放,叮嘱我要把各方面的基础打好,不要着急定题。
在音韵学的学习中,孙老师一直强调不能光看书,要亲手实践。有一天,他问我:“《广韵》的韵图作过吗?”我本科的时候学过音韵学,万献初老师布置的作业就是做《广韵》韵图,所以我很高兴地回答说:“做过啦!”“那就再做一遍!”我一下子就傻眼了,原本以为会听到一个“好”字。想当初可是做了一个暑假,但也没办法,师令如军令,我只得又老老实实做了一遍。不过这一次跟本科时候不一样,因为有了一定的基础,对一些问题能理解得更加深入。另外,韵图也是一种声韵调配合表,在做表的过程中,我也体会到了语音结构的系统性。
孙老师还建议我去补自己的“短板”,学术研究的视野不要局限。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博士前两年,我补修了方言学和古文字的相关知识。选修了项梦冰老师的《方言学》,并和北大方言小组一起远赴福建泉州进行方言调查。后来又花了一段时间梳理了古文字材料中的一些谐声字的考释结论。这一段经历对我的博士论文写作有很大帮助。特别是到了论文后期分析历史性音变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看方言中有没有共时材料可以参照。出土文献资料层出不穷,一些谐声字的构形又得到了重新的解释,不少材料也都融入了我的博士论文中,这也构成了我论文的一个创新点。工作以后,因为之前的接触,我对这两个领域的一些最新成果也持续关注,也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思考,后来以此修改了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2017年以博士论文成功申请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应该也得益于后期的不断修订。
北大的博士培养,在论文开题之前要进行中期考核,要求是撰写一篇论文,通过答辩来综合评判学生的学术涵养和研究能力。跟随孙老师学习两年之后,我渐渐了解声母领域存在的一些争议,发现不少学者所用的谐声材料大多来自董同龢先生的整理,并且是举例性质的,如果穷尽性地加以统计,并进行系统考证,或许会有新的发现。因此我选择了疑母和心晓母发生联系的谐声字作为研究对象,撰写了论文《上古疑母和心晓母特殊谐声关系研究》。从材料的使用范围,论证的过程和最后结论的得出,全文的写作思路都可以算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雏形,得到了中期考核小组老师的肯定。正因为有了这篇论文作为铺垫,我才坚定了博士论文的选题方向,经和孙老师讨论,选定《上古牙喉音特殊谐声关系研究》作为论文题目。
在上古谐声系统中,和牙喉音发生联系的声母分布最广,为了穷尽性地搜集特殊谐声的资料,我首先做的事情是制作《说文解字》谐声数据库。以大徐本《说文》为底本,参考江沅的《说文解字音均表》,并且借鉴了孙老师《谐声系列与上古音》(2010)、《谐声层级与上古音》(2011)中的相关意见,对谐声字分出了层级,以谐声系列进行统计归类,并标注上古音韵地位以及声符谐声字的关系。数据库完成之后,和牙喉音发生联系的特殊谐声字很容易就筛选出来,再以声母类别分出章节,以声符区分,对特殊谐声字一一进行考证。考证的过程是将谐声字的形音义相结合,重点考察声符的真实有效性,注音的客观匹配性,特殊读音产生的原因,以及特殊谐声字读音形成的时代。文章紧紧围绕汉语的内证材料,从上古文献中的经师音注、读若、假借、异文、连绵词等材料发掘宝贵的语音信息,力求还原这些特殊谐声字在上古
的真实语音面貌。研究发现,在牙喉音的所谓特殊谐声字中,有相当一部分其读音的产生与规律性的历史音变无关,而是受同义换读、同形字、误定声符、音变构词、语流音变、读音类推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如果考虑到谐声层级,剔除跨层级的一些特殊谐声字,则真正的特殊谐声字数量很少,并且绝大多数的特殊谐声字其读音上古已经形成,当前一些复辅音构拟在解释汉语的一些内证材料、历史语音的发展演变以及音系的声韵配合上存在一定的矛盾。
此篇论文的结论是基于一个一个特殊谐声字的考证,以事实为依据,又有科学的数据统计分析,避免了以往上古音研究中将特例看作通例的弊端。文中借鉴古文字研究成果,对一些许慎认定的声符进行了重新分析,承认了文字早期大量的“同形字”现象,事实上已经对复辅音构拟中的一些诸如“告-造”“辥-薛”“-歸”等经典案例进行了批判,但这些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一些文章仍将之处理为特殊谐声字,不能不觉得是一种遗憾。不过这些现象的存在对我也是一种鞭策,促使我早日把论文修改出版。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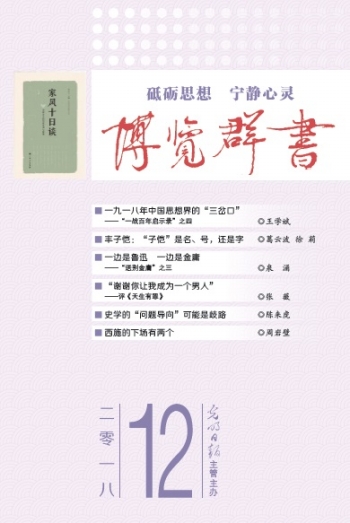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