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孙玉文老师教诲是在2010年。那时我读本科二年级,录取了北京大学古典语文学项目,选择古代汉语方向。孙老师是教研室主任,他把我们几个同学聚在一块,讲了两个事情:第一件,王力先生高小毕业之后,做了几年家庭教师,熟读学生家中所藏14箱古书,奠定了扎实的国学根基;第二件,“文革”以后王力先生给学生讲“如何读书”,不能只陷在一个很小的领域中,要广泛地阅读。孙老师随后介绍说古代汉语有文字、音韵、词汇、语法、修辞几个分支,不可偏废,并希望我们能培养出阅读古书的能力。当时听起来还懵懵懂懂,后来才意识到,从王力先生到郭锡良先生,再到孙玉文老师,治学的经验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老师在古音学领域曾写过一些的辩论性质的文章。他总说,学术争论才能促进学术进步。让我想起《孟子·滕文公下》里的一句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在学习这些文章时,老师都让我先去掌握论争另一方的体系。“欢迎来辩!”也是常说的一句话。因此我也总是站在论争另一方的立场去和老师争论,并听他一一化解。只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把问题点出来,才能避免自说自话。后来,我也在老师的指导下写了两篇辩论性质的文章。我想,正是在这种出招和接招的辩论中,认识才会深入,一些学说的问题也能被充分地暴露出来。
到2016年,我升入博士阶段,正式进入孙玉文老师门下。老师知道我的特点——喜欢东搞搞,西弄弄,一会儿看看音韵,一会儿做做语法,缺乏定心,便一反平常“拓宽视野”的讲法,每次谈话都围绕专精展开:大学者都有自己压箱底的著作,段玉裁有《说文解字注》,王念孙有《广雅疏证》,都是围绕一个专题、深入钻研之后的成果。应建立起做学问的根基,不应该浅尝辄止,更不能随波逐流。每次看到他案头翻断编的“十三经注疏”和《经典释文》,心中就会想到孔子韦编三绝的故事,感慨做学问的定力很重要。
正因为如此,入学不久,老师希望尽快确定博士论文选题,建议研究古代汉语中的词义引申。老师的巨著《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在词义引申上着墨极多,是古汉语词汇研究的宝库。他翻出一个例子——“错”条(P629),条目下列出了11条古代文献中“安置”与“存放”义相联系的例证,从而证明闽方言“房屋”义的“厝”应源自“安置”义的“措”。老师进一步说,规律总是会反复出现;出现平行的词义联系,证明背后有词义规律在起作用。汉语词义演变的规律,目前挖掘得还不够,希望能够推进。听了老师的逻辑,我完全被说服,内心昂扬的斗志也被点燃,于是满口答应下来。
等到自己真正开始研究时,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甚至无从下手。词义引申的文献,古今中外;古汉语的词条数也相当可观,用例都蕴藏在海量的典籍中。“学海无涯,回头是岸”,这句博士生中流行的话又时不时从脑中冒出来。也许当初老师挑“错”这一条,本来就是告诉我要多试试错吧?
老师抽丝剥茧,道出了其中的真谛:考虑选题要从大处着眼,开展研究和写作要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选题能在学术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小处着手,要踏踏实实地摸每一条材料,并从中抽绎出规律,不要从理论到理论,更不能空对空。应该反复琢磨《说文解字注》《广雅疏证》对每一个字、每一条故训的考释,提炼研究方法。再按照一定的条理,比如词的义类或句法功能,逐词逐词地搜集材料,总结规律,才能推进对语言现象的认识。回想之前读了不少词汇学和语义学的研究文献,却总在整理各家的理论体系,忽视具体材料,因此常在五里雾中,听了老师拨云见日的一席话,顿有豁然开朗之感。老师对论文的期
待应该是:既有绣花的功夫,也有建楼的本事。从很小的地方着手,发现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或者开创一个新的研究方法。老师的研究也是这样进行的。
我按照这个原则,不断地摸索材料,缩小研究范围,最后决定重点观察上古汉语动词的句法和词义演变。在研究过程中,通过观察语言细节,也有不少发现。比如《左传》中的动词“怨”,有一处用例是“何怨于人”,这一例看似由介词引出“怨”的对象宾语。细绎材料,只有在“何动于X”这个反问格式,“怨”后面才出现“于”,其他情况都是直接带宾语。因此,“于”不是为“怨”引介成分,而是为“何怨”引介成分。虽然这仅是具体动词归类的小问题,却反映出对“于”的认识还不到位:“于”字介宾结构的粘附性很强,但仍有一定的独立性。“A之于B”格式,也能映证这一点。
与前面几位已经毕业的师兄师姐不同,我的博士论文目前还在建设中。当然,非常希望自己能写出一篇好的论文,不辜负孙老师的指导,并真正为中国语言学作出贡献。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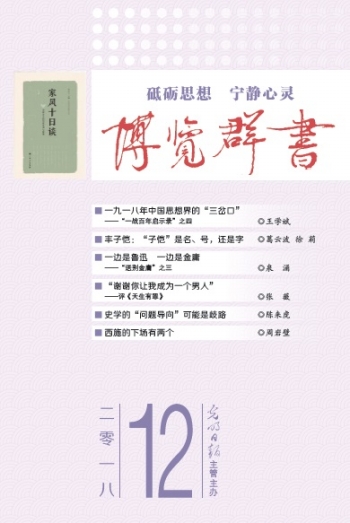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