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的写作,据杨绛回忆,“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钱锺书在《〈围城〉序》中也说“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乱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才“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完稿之后,自1946年2月25日,开始在郑振铎、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第1卷第2期连载,至第2卷第6期。首期《编余》中,李健吾写道:
可喜的是,我们有(又)荣誉(幸)连续刊载两部风格不同然而造诣相同的长篇小说,弥补我们的遗憾和读者的怨望。李广田先生的诗和散文,有口皆碑,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载誉士林,他们第一次从事于长篇制作,我们欣喜首先能以向读者介绍。
两部长篇,一部是李广田的《引匀》,另一部就是钱锺书的《围城》。后《围城》被列入《晨光文艺丛书》,1947年6月交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单行本,1948年再版,1949年3月三版。初版本出书前的广告云:
(《围城》)人物和对话的生动,心理描写的细腻,人情世态观察的深刻,由作者那支特具清新辛辣的文笔,写得饱满而妥当。零星片段充满了机智和幽默,而整篇小说的气氛却是悲凉而又愤郁。
1947年,在《钱锺书杨绛夫妇》一文中,赵景深说:“《围城》已经成为我们家中的favorite(最爱)了,我的儿子、内侄、姨女、内嫂以及我自己都争夺般地抢着看,消磨了一个炎热的长夏。”
同样“有如饕餮”的心情也出现在柯灵笔下:
《围城》最初是读手稿,因为那时连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文艺复兴》和《周报》同在一处出版,《文艺复兴》每期发稿以前,大家有机会先睹为快,读得兴高采烈,满室生春。(《钱锺书创作浅尝》)
近日,翻阅黄成勇《幸会幸会,久仰久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中有《曾卓题跋——七月书旅之曾卓篇》,谈及20世纪40年代,《围城》刚出版时,方典就著文嘲讽那是“打翻了香粉铺”。所谓“方典”,王元化是也。乃按图索骥,始得其详。1948年2月,方典在上海《横眉小辑》创刊号上,发表《论香粉铺之类》。文中写道:“你在这篇小说里看不到人生,看到的只是像万牲园里野兽般的那种盲目骚动着的低级的欲望。”作品“有的只是色情;再有,就是雾雨下不停止似的油腔滑调的俏皮话了”,“作者对于女人无孔不入的观察,真使你不能不相信,他是一位风月场中的老手,或者竟是一个穿了裙子的男人!”“令人读了如入香粉铺”。
又读姜德明《金薹小集》(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同代人”文艺丛刊》一文,竟牵扯出类似言论。“同代人”文艺丛刊,第一集《由于爱》刊出张羽的《从〈围城〉看钱锺书》,称“作者俨然是个上帝”。只有“装饱了肚皮,闲着没事做的绅士和清客,才会在这五光十色的市场上演幻术,为那些遗老遗少们寻开心,替那些妖姬艳女们讲恋经”。文章认为钱锺书是超过冯玉奇和张资平的新鸳鸯蝴蝶派,《围城》是“一篇有美皆臻无美不备的春宫画,是一剂外包糖衣内含毒素的滋阴补肾丸”。在张羽笔下,钱锺书者,“帮闲文人”而已!李辉认为,“张羽”这一名字,也是王元化所“化”。在《黄永玉个人传奇与历史风云相会》中,我们还可以看见大段引文:
……而少数人,钱锺书所属的那些绅士,清客及他的集团,则感到恐怖,消沉,彷徨,在这为骚乱的气氛所围绕的环境里,苦于无法解脱,只好把这颗“芳心”寄托到醇酒女人身上,想从这块小天地中,透出一口闷气,以求心灵暂时的轻松,片刻的安慰。可是这些连灵魂都冷却的绅士,他们所热中(衷)的是金钱,洋楼,女人。而这些阿谀绅士的,抱着绅士的屁股眼亲嘴的清客们,只好捧上了这最能适合绅士的胃口的东西来献媚了。尤其是连钱锺书这样的帮闲文人,除了一付(副)僵尸架着件玄色马褂,摇头摆尾,苦吟着世纪末的哀歌的丑角们,除了逢迎绅士,交出定制的货色而外,还能作(做)些什么呢?
继之,1948年7月,王任叔(巴人)在香港《小说》创刊号上,用笔名“无咎”发表《读〈围城〉》,指责作者“态度傲慢,俨然以上帝自居”;“只看到一切生存竞争的动物性,而忽略了一切生存竞争的社会阶级斗争意义”;“‘两个妖精打架’的故事,也成为我们上帝唯一的创作主题”;“抓取不甚动荡的社会的一角材料,来写出几个争风吃醋的小场面”;“世界在他面前是赤裸裸的一个女性模特儿”。《围城》实在是只“有粪蛆似的有生命的东西在蠕动,在翻滚”。
有感于上文对钱锺书的责难,《观察》5卷14期(1948年11月27日),刊发了林海的书评《〈围城〉与Tom Jones》,认为《围城》与英国小说《汤姆·琼斯传》近似,但“《汤姆·琼斯传》中的事实多于议论;《围城》刚刚相反,议论多于事实”,“《围城》是一部彻底的人性大观”。尤其是“书中第五章记方鸿渐旅行所见,那些情景,抗战期中常在内地奔波的,谁没有经历过?可是当代小说家中,除钱氏外,还有谁能写出这样惊才绝艳的一章?”“其实,钱氏的野心是决不止于做做‘上帝之梦’的,他还想更上一层地去做上帝的改革者。李长吉诗云:‘肇被造化天无工’。钱先生的真正野心是想拿艺术去对抗自然,把上帝创造天地时的疏忽给弥补起来。《围城》一书,除了臭人丑事外,还特地排出宇宙间最惹厌的一些东西,如鼾声,狐臭,跳虱,饥饿,梦魇,胡子,喉核,厕所之类,来加工描写,揣作者的心意,无非想化腐臭为神奇,拿粪窖中的材料来盖造八宝楼台。”《围城》实为“学人小说”。“钱先生是以博极群书著名的,他这部作品所取法的西洋小说不知有几派几家,书中甚至连有些比喻都有出处!详细的注释应该留给未来天下太平时的学者去做”。《围城》“感觉的灵敏和笔墨的精妙”,“是无论如何难以否认的”。“批评《围城》的人,如果连这一点也把它抹杀掉”,那就完全失去了“公道”,“不是眼光出了毛病”,便是“把心肝偏到夹肢窝里去了”。林海,即郑朝宗,与钱■书“清华曾共学”。钱氏闻之,称郑是小说的“赏音最早者”。
郑朝宗的文章,在西南一隅激起反响。1949年1月,在成都《民讯》第4期,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陈炜谟以熊昕之名,发表了《我看〈围城〉》,对郑文逐条辩驳。
以整个的文章,《围城》所给我们的印象,仍不免是堆砌过火,雕琢太甚。从好的方面说,它真的珠光宝气,花团锦簇的,在某一种意义说来,确实是美丽的;从坏的方面说,写得无论怎样美,只不过是供有闲阶级消遣的玩意罢了。
……
其实,《围城》的作者倘能够放弃一些狭隘的成见,从法国的文学作品(如巴尔扎克的)或者俄国的作家(如高尔基),吸收一些优良的写法,再勇敢地面对人生,正视社会,他的造就,当是不可限量的。
《围城》为世人疏漠既久。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该书“濯去旧见,以来新意”,最后爆出绝响: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小说,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是,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
……
除了讽刺外,《围城》亦有“流浪汉小说”(picaresque novel)的风险味道。在这方面它和十八世纪英国小说的相类似殊非意外。
……
在所有战时和战后的小说中,《围城》最能捕捉到旅途的喜趣和苦难。
自此,众皆刮目相看。1990年,《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播出,钱锺书终于破土而出,龙飞九天,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昆仑”。
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界与传媒逐渐流行“北钱南王”一说,即“北有钱锺书,南有王元化”。而王元化的回应则是:
钱锺书是前辈,我各方面的学识都比不上他。社会上有种种说法,事前我并不知道,我没办法。每个人对自己都应有恰当的评价。我作出了一点小小的成绩,但不能过分夸张。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去世。王元化认为,钱先生的离开,标志着出生于本世纪初的那一代学者的终结。钱■书也曾用“博雅”二字评价王元化的《思辨随笔》。2006年3月,三联书店出版汪荣祖《史学九章》,第166页影印“钱锺书致汪荣祖书”,推翻前说:
来信所言在沪交往四君,皆旧相识,王君尝化名作文痛诋拙著,后来则刻意结纳……弟亦虚与委蛇。要之均俗学陋儒,不足当通雅之目。
2004年,文汇出版社出版《清园近作集》。内中收录王元化写给吴布鼎的七封信,表达了他的不满:“我也不喜欢钱锺书的《围城》。朴素地说话,真诚地写文章的人太少了。”该信约写于1946年,此次刊出,大有宣示初衷之意。
2008年10月,三联书店刊行吴学昭《听杨绛谈往事》,第221页云:
《围城》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遭到一伙人围攻,每天在报刊上痛骂《围城》是“香粉铺”,是“活春宫”。不久,巴人(王任叔)在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声明骂《围城》的不是共产党,他代表共产党发表此文。巴人的文章见报后,毒骂《围城》的一派人偃旗息鼓。巴人上世纪50年代,恰好与钱杨在文学研究所同事,大家相处甚好。
《围城》在问世之初,所受的批评,多为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政治话语,且不乏谩骂之词。这些书写的痕迹,一路行来,不免会被抹擦,甚至有改窜的趋势。但作品的有迹可循,使读者藉此重返历史,一不小心,也闯进了知识分子的心灵。谨以此文纪念钱锺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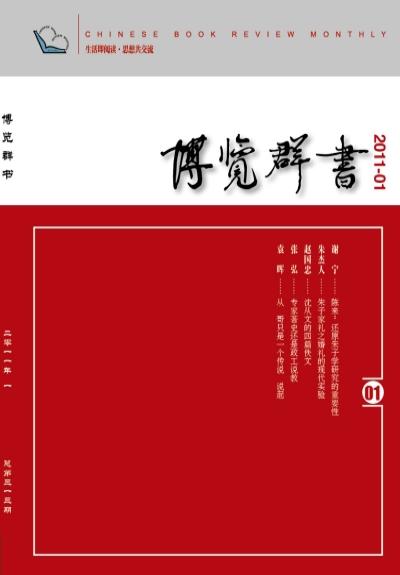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