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庵认为师山是巴金
前段时间,我分别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和“巴金文学馆”网站上读到日本著名学者、巴金研究专家坂井洋史先生的文章《巴金——丰富生命的追求者》。据文末的说明,这篇文章初稿于1993年,于2005年5月修改。坂井洋史在文章中说:
我们当时把一套40年代刊物的复印件放在中间谈下去。这个刊物叫《中国与世界》月刊,创刊于1940年7月,主编为师山(此人情况不详。第3期后与林憾庐合编),“中国与世界社”出版。特约撰搞人名单上列有巴金、陈范予、叶非英、林憾庐、朱谦之、黄凌霜、梁冰弦等18名(后来有出入)及“中国自然哲学研究会全会员”。从这个执笔者阵容及刊载诸文内容判断,该刊无疑是安那其主义者的一个阵地。S指出这个刊物的政治背景有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然后叫我注目于第3期内容。第3期专篇栏上果然有巴金的《蒲鲁东的道德学说》一文。此篇不外是巴金自己20年代翻译过的《克鲁泡特金伦理学》中第13章的再录。同一期上也有乃济翻译的《关于爱玛·戈尔曼女士》,是纪念同年5月14日逝世的安那其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追悼文章。原来巴金和高德曼早在20年代开始通信,曾有一次甚至称过高德曼为“精神上的母亲”。一直尊敬她的巴金终于没有公开发表过一篇追悼文章,这个沉默是费解的。
我当时就手边的资料(如钦鸿等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查询了一番,确实没有找到关于“师山”其人的记载。但通过唐沅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吴俊等编《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发现在林憾庐主编时期的《宇宙风》杂志上,有署名为“师山”的十多篇文章。我手边收藏有一些民国杂志,仅找到了刊载有署名为“师山”的《希特勒主义》(90期)、《如此波兰》(91期)、《向吸血鬼抗战》(94、95期合刊)和《动的时代》(142期)四篇文章的《宇宙风》,其余的大多数篇目则没能见到文章本身。
前几日,我偶然读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书前有周黎庵(劭)所写的前言。文末说:
林憾庐最志同道合的好友是巴金,在沪时年近不惑的巴金差不多每天来看他,在编辑部门前霞飞路上按巴黎人的的习惯喝咖啡,也给《宇宙风》写些文章。……林、巴两人在沪时还合办了一个刊物,叫做《中国与世界》月刊,每期卖不出几本,全是退货,巴金写了不少没有稿酬的文章,署名为“师山”,这段文坛掌故,知道的人现在几乎没有了。(P8-9)
我读到这段话时,大吃一惊。周黎庵是与《宇宙风》、《论语》等海上刊物及林语堂兄弟渊源非常深厚的人(见《宇宙风》“百期纪念号”上周黎庵《宇宙风与我》一文)。他曾经参与编辑早期《宇宙风》,也是《宇宙风乙刊》从第20期至54期停刊时的主要编辑者。毫无疑问,周黎庵是当年“文学现场”的亲历者之一。如果他所述情况是真实的话,那么,我们不但新发现了一个巴金从未被人所知的笔名“师山”和十多篇佚文,而且巴金与林憾庐共同主编无政府主义刊物《中国与世界》之事,也将为巴金传记增添许多新的内容。这将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发现。
师山应是梁冰弦
周黎庵的说法仅仅是一个孤证,还得寻找更多的证明材料。
我首先从《中国与世界》月刊入手。据丁守和等编《抗战时期期刊介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页“《中国与世界》”条:
《中国与世界》(1940.7—1941.2)/师山编,上海中国与世界社出版;抗日宣传刊物/总1-6
考虑到这个刊物与林憾庐的关系,我仔细翻阅了手边所存有的1940、1941、1942年《宇宙风》,果然有了一些发现。在这段时期内的《宇宙风》上,登载有《中国与世界》月刊一至六期的“要目”。从目录可见,巴金在每一期上都有文章发表(见表、图),可见其与该刊的关系非同寻常。
并且,我在《宇宙风》第116期上,读到了林憾庐《我应当告罪》一文。文中详细讲述了《中国与世界》创办和停办的有关情况:
去年夏天,我回到上海,创办了两个刊物,一个是《中国与世界》,一个是《西洋文学》。我的计划,原是等出版一、二期后,各项就绪了,我便可以放开,专为本刊努力。不意《中国与世界》第一期印出,工部局无问题,但邮寄国内的三千多册,却全为日方扣留(因为里面的文章,有好几篇,如:发刊词,健全的民族思想与世界主义、中华民族的世界分布等,骨子里都有东西,虽不昌言抗日,但在精神上算是反日与反法西斯的)。那一期的损失,给一个新办的刊物以很大的打击,但我不灰心,决定仍办下去。因为:我总以为我国出版界的空气太过消沉,而且沪上一些低级趣味和娱乐的杂志,加之汪派又在活动,所谓“有毒”的刊物也很多。我很不相信读书界喜欢看那些东西,而学术思想的高级读物会不行,所以,我决定维持下去。
……
关于《中国与世界》,一些朋友都说水平太高了,……而且华北各地竟然有很多人来定阅,定户并不比《西洋文学》少。这给我的鼓励和慰籍不小。可惜,这个刊物现在不能不暂时停刊了。当然,这个刊物是一直赔本的,只是我因为希望可以邮寄国内,便能勉强维持,所以一期一期出下去。现在邮寄内地,连香港也不可能,只好暂时停刊了。这是我对《中国与世界》的读者万分抱歉而无可奈何的事情。(《宇宙风》第一百十六期,页二三三)
考虑到巴金与林憾庐之间的密切关系,巴金以“师山”笔名为林憾庐创办的刊物担任共同主编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奇怪的是,我遍查《巴金全集》、《巴金的一个世纪》以及巴金本人和林憾庐后人的回忆文章等资料,却没有见到有巴金与林憾庐曾经合作主编过刊物的任何记载。当然,由于历史原因,巴金在新中国后一直刻意回避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问题,在后出的文本中,看不到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交往也是正常的。巴金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例如,在《怀念非英兄》一文中,巴金就谈到了他删改文章刻意抹去有关“福建几个朋友”的痕迹的事情。
但是就我手边已有的师山在《宇宙风》所发表文章看,有几处疑问实在无法解释:
1、《如此波兰》(91期)一文开头,“记得十一、二岁刚废掉八股改兴时务策论的时候”,废八股的时间是在1901年左右,因此,作者的出生时间应在1890年前后,而巴金出生于1904年。
2、《动的时代》(142期)一文开头,“往年编著过一本近代文明小史,大多取材于英人某氏的十九世纪欧洲史”。遍查有关材料,也未发现巴金编著过“近代文明小史”之类的书。
3、《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这本书中,收录有署名“师山”的《岛上的悲风——悼吾友许地山先生》,里面说到“民国二年,孤零零作客缅甸,谈得来的仅二三人,地山其一”。民国二年,巴金显然不可能作客缅甸。
关键的问题,是要找到署名为“师山”、发表于《宇宙风》的纪念林憾庐的两篇文章:《伤逝——哭于憾庐之墓后作》(133期)和《又来这么几行——憾庐先生逝世周年纪念》(138期),与巴金本人怀念林憾庐的文章对照。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获得了《伤逝》和《又来这么几行》两文。阅读这两份材料后,我确认“师山”不是巴金。
同时,通过这两份材料中的几处论述,我可以确定:“师山”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
在《伤逝——哭于憾庐之墓后作》中,作者说:
1、“民十二,我重到厦门大学管理出版部,兼主编鼓浪屿的《民钟日报》。”查《民钟日报》,首任名誉社长许卓然,林翰仙为经理兼编辑主任,总编辑或编辑主任有傅无闷、梁冰弦等。
2、“民十三四间,我在上海办出版合作社。”查“出版合作社”,曾刊行《吴稚晖学术论著》及其“续编”、“三编”,编者均为梁冰弦。而吴稚晖也曾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
3、“语堂住在九龙饭店,憾翁拉我过访不遇,我们在咖啡座豪谈起来,话题是五四运动中请出来的德(民主)赛(科学)两位先生……那回的谈话,倒便宜了我粗记起来次日交卷,塞责了一期本刊的杂感与随笔。”查《宇宙风》102期,“杂感与随笔”中有署名“仌(冰)弦”的《赛先生和德先生》一文。
4、“我那名义是儿子我却作为思想伴侣的企善,憾老尤其奖借诱掖,不遗余力。”查“企善”为梁企善,曾在《宇宙风》和《中国与世界》上发表多篇文章(如《宇宙风》第127期七周年纪念号有梁企善《“自由之什”前记》等)。
而前面提及的《动的时代》(142期)中,那本“近代文明小史”,可能是指上海出版合作社1928出版的梁冰弦所著《现代文化小史》。
因此,周黎庵(劭)在《午夜高楼(〈宇宙风〉萃编)》的“前言”中所说巴金与林憾庐合编《中国与世界》,以“师山”笔名为《宇宙风》免费写稿的事情不是事实。
巴金与梁冰弦
1、 梁冰弦其人。
按照《如此波兰》中的那句自述,梁冰弦应是出生于1890年前后。他是广东人,老同盟会会员。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载,“在《中国报》先后承乏笔政者,自王君演、卢少岐、丁雨宸、梁襄武、何冰甫、何雅选、卢信、廖平庵诸人”,梁襄武即是梁冰弦。在1918年9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3号上,有署名“冰弦”的《蔗渣谭》。1919年7月下旬,梁冰弦、区声白等撰稿的《民风日刊》在广州出版,从8月10日第12期改为周刊。1919年12月,闽南护法区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漳州创办《闽星》半周刊和日刊。半周刊在《启事》中说:“本刊的宗旨是提倡新文化,建设新社会。”陈炯明在《发刊词》中说:要以“新文化运动,即是思想界的改造,使人人都随着我们在进化线上走出”。这个刊物由梁冰弦担任编辑,刊物内容,一方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阶级斗争,报道苏联革命,说“社会主义表现出来,资本主义必然打倒”;另一方面,大量刊登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主张“实行互助主义,去谋人类平等的幸福”。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陈铭枢等人都为它写过文章,行销甚广。1920年,维经斯基到上海和陈独秀等酝酿建党时,他的两名工作人员米诺尔和别斯林,由李大钊推荐北大粤籍学生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来到广州,介绍给区声白、梁冰弦等人。他们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创办《劳动者》工人刊物,并成立共产党小组在工人中活动。据梁冰弦的回忆,陈炯明在漳州时,曾接纳梁的建议,拟聘请陈独秀到漳充任教育局长,但陈因有别事不能来漳到任。后来,陈独秀到了广东,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五十年代,梁冰弦撰写《解放别录》,以笔名“海隅孤客”刊载于香港《自由人报》(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重载于《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九辑》(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据梁冰弦在《解放别录》中记载:直至1922年“6·16事变”前夕,陈独秀还在劝说陈炯明加入共产党组织。晚至1978年,梁冰弦还在台湾《传记文学》上撰写过回忆文章。其后的情况未能查到。
2、师山有无可能是巴金和梁冰弦的共同笔名?
我所读到的以“师山”署名的几篇文章,文本内容本身都能证明不是巴金的作品。在巴金的作品和书信等材料中,也从未谈到“师山”。“师山”这种笔名,不像“乔木”那样有可能出现多人使用的情况。另外,即使巴金和林憾庐关系非常密切,但巴金以文为生,而林憾庐的杂志一直销量不错,似乎也没有必要让巴金免费写稿。综合以上的看法,“师山”不太可能是巴金和梁冰弦的共用笔名。
3、巴金与梁冰弦之间有无直接交往?
根据《巴金的一个世纪》中的记载:1927年8月,巴金“据英文、法文、日文三种版本和人人会同志的中译本以及白性、冰弦、凌霜的中译章节重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作为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应该知道梁冰弦这个比他大十五岁左右的前辈的名字。
梁冰弦在《伤逝——哭于憾庐之墓后作》中说,他于林语堂与鲁迅到厦门大学之前(1926年)就离开了厦门,而巴金迟至1930年才到厦门认识了林憾庐、王鲁彦。因此,巴金和梁冰弦在1930年之前应该没有直接的交往。
1940年前后,也就是林憾庐和梁冰弦合办《中国与世界》那段时间,巴金多在上海居住。巴金在每一期《中国与世界》上都有文章或译文发表,他应该知道主编师山是谁的笔名。而作为林憾庐共同的友人,巴金和梁冰弦是否一起在霞飞路上共饮过咖啡,那就只有等待进一步的查考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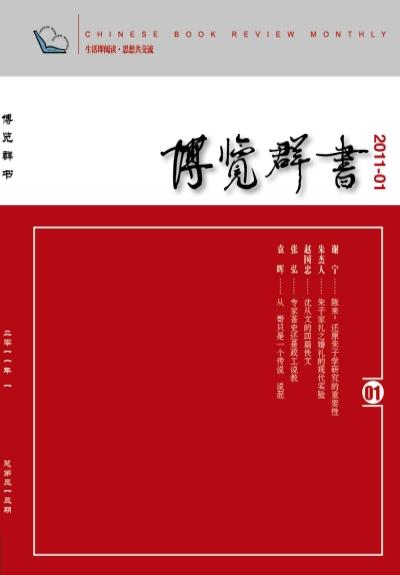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