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江户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阴(1830—1859)在《讲孟札记》一书中说,中国之臣“择其主之善恶而转移”,好像是“半季渡之奴婢”,和日本之臣“与主人同死生休戚,虽至死也绝无可弃主而去之道”不同。他即认为对于君主的单向服从在日本是臣下的义务,在中国则不然,由此批评中国之臣的形态。但一读李若晖教授的《久旷大仪》就得知,吉田松阴的观点不完全是正确的,即使可适用于战国以前的臣民,也无法适用于秦汉以后的臣民。
《久旷大仪》关注“儒者是否真正奠定了儒学之国家制度”的问题,深入探究汉代儒学和帝制之间的互动。根据本书的观点,汉代儒学和帝制的互动,就结果来说,是汉朝帝制使儒家思想转向的历史。西汉初中期,因为汉朝政制继承秦朝的律令体制,所以儒者试图依其以礼治国的理想建造经国大典来革新汉制,但结果是失败的,到了西汉晚期以后,儒学屈服于皇帝的至上权威,接受眼前存在的体制而转向。换言之,面临中国帝制草创期的儒者,起先努力打造基于德与礼的新帝制,但结局则是,儒家内部出现否定这种努力的学说,也就是说,帝制却使得儒学具有承认及维护现有皇权的新倾向。
本书所设想的儒学转向主要是儒者尊信的伦理规范之变质,亦即从“双向性”到“单向性”的转变。双向性伦理是对任何一个人伦关系中的双方都要求尽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单向性伦理则是只对其中的某一方,通常是居于下位的一方要求尽责任和义务。作者即认为,西汉初中期的儒者要求居于上位者,尤其是皇帝尽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到了西汉晚期以后,儒者渐渐不再谈论其责任和义务,以致中国形成单向性伦理为主导的社会。
本书从周礼体制的权力结构谈起,说明在此体制下的人们秉持双向性的伦理规范,周天子也不例外,承担保护臣民的义务,其权力受德与礼约束。但到秦朝统一天下,依法治国的秦制取代周礼体制,其中君主高于法,以暴力与强制行使权力,从而形成了臣民单向地服从君主的伦理规范。汉朝承袭秦制,儒学源于周礼,汉初儒者试图复兴以礼治国的政制,以使皇帝尽保护臣民的义务,但后来在儒家内部出现维护单向性伦理的倾向,本书主要从所谓“今古文之争”的视角叙述之。今文经学将以汉代通行的文字写的“今文经”,古文经学则将以秦以前的古文字写的“古文经”作为学术基础,但两者之间不但在所依经典的字体上有差异,而且在对于政制的见解上各有所持。
本书指出,儒学并未传承一套完整的周礼国家体制,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瓶颈。西汉时期流行的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儒生希望以礼代法,改造汉朝所承袭的秦制来恢复双向性伦理,然而,结果是未能制定一套完整的礼制。古文经学儒生批评这点,虽然古文经中也没有记载一套完整的礼制。他们采取的道路则是,以单向性伦理替换双向性伦理,因循现有的汉朝旧典,以儒学缘饰秦制的依法治国、尊君卑臣。对吉田松阴来说,尊君卑臣是正面的伦理规范,但在作者看来则不然,古文经学的作为是“将儒学改造为专制君主的顺从奴仆”,“使得秦制之国家暴力笼罩并规定了儒学之仁德”。儒学并没有成功奠定儒学的国家制度。
本书在论证的过程中博引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非常利于我们了解汉代儒学的情况和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汉代儒学和帝制互动的状况,也就是思想和制度互动的具体情形。李若晖教授的《久旷大仪》为我们提供相关知识和资讯的同时,引导我们进一步深入思索“国家和德性”“国家和暴力”“思想和政治”等重要问题,可以说是一本好书。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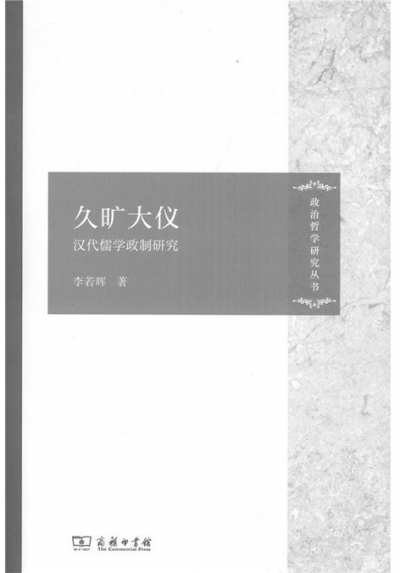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