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收到一封来信,发自一个国家级贫困县。那时我从新闻系毕业不久,任职于某部委机关报,几天前刚从当地采访回来。信捏在手里很沉,当我掏出里面厚厚的一沓信纸,双手立刻像被火烧了一样灼热——这是一封告状信,字体工整,语言连贯,写信人应该至少具有初中文化。这封信被我慌张地塞进抽屉,直到一年后离开报社都没再打开。此后数年学院生活,我很少想起它,像是甩掉一个记忆中的“红字”,刻意地去遗忘。
近日,当我打开一本新出版的乡村研究名作《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读及作者萧公权的序言:“中华帝国的乡村农民绝大多数目不识丁。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所作所为通常不会引起那些能读能写的知识分子的注意,因而大部分未能记录下来。一些官吏和知识分子经常提到的‘民间疾苦’,可能只是重述一般性的看法,而不是展示乡村生活的真实情况。”——眼前立刻浮现出那封多年前的来信,它的愤怒、焦炙、渴切、期盼,连同清晰的笔迹一起,带着更沉重的力量,自记忆深沉的海底上升。
在这本乡村政治研究经典里,萧先生允切精当又不惮词费地剖析了19世纪的中国乡村农民。他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就像一种生来即主动消声的被迫性存在。两广总督王庆云记述:“农民伏处田野,畏官府如神明。不幸遇灾,唯有坐而待殍而已。其抱牍而泣请者与聚市噪讙者,必非农也。”人类学家杨懋春给出观察:“人民在公共事务方面一直是愚昧、驯顺和胆怯的。”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如此描述了自己眼中19世纪中国农民的人生态度:“难以理解的是,一群群无家可归、饥饿难忍、处于绝望境地的逃难者,在遭受洪灾或饥荒沉重打击的土地上到处流浪,为什么不在自己遭受毁灭的地区团结起来,向有关州县官员索取一些救济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询问处于饿死边缘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这样做,所得的回答毫无例外,都是‘不敢’!”
萧先生批评明恩溥所代表的观点与那些和他对立的观点一样,过于简化,未考虑到中国农民的行为在不同历史和地方环境下所发生的重要变化。他指出,拥有读写能力,某种程度上对自己遭受的伤害更为敏感,表达自己的情感更加清楚有力,更为积极地想办法改变令人不满意的环境。萧先生未就19世纪农民的文化状况给出具体资料,他援引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卜凯的研究,“根据1920年代在中国分散地区的考察,农家子弟入学率不超过30%”。文化水平的低下确乎限制了人们对自身幸福的追求。
与“绝大多数目不识丁”的19世纪农民相比,21世纪的中国乡村,农民的文化程度状况如何?提高了多少?
资料显示,在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比例更高略),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比例为32.74%,初中文化程度为53.10%(大约是给我来信的写信人的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为8.85%,文盲或半文盲仅占5.31%。
学者的田野调查也发现,中国农民有了越来越强的权利意识,他们不仅清楚什么是自己的基本利益,而且也懂得了如何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基本利益。回顾鲜活的当代乡村史——凤阳小岗生产队18户农民偷偷“包产到户”(重庆荣昌楠木沟村包产到户甚至比小岗村整整早了两年),18个红手印展示的正是应激表达的最基本途径:要么说,要么行动。
本书提供的文献里,一位英国派驻东南亚的高级专员在回答“公众舆论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时表示,“所谓公众舆论,通常是指生活在城市、大型城镇和其他中心的公众的意见,这些地方拥有报纸、广播、政治活动等……务农的农业人口,没有同样的条件来形成一种意见”。这呼应了杨懋春的判断:“民意并不是指小农的看法,而是乡绅和族长的意见。”
今日中国,农民的舆论条件情况又是如何?
即使在十多年前的各省跑村采访中,我也已吃惊地发现,即便在宁夏、贵州等国家级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随机访问的农户也大都拥有一台哪怕是黑白的电视机。而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据最新统计,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共7.72亿,其中农村网民为2.09亿,这一数字还在以更快的速度攀升。
1955年,萧公权在大洋彼岸完成了《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英文原稿。63年之后,它的母语版终于回到了作者的故国。
要特别一提的是,虽然这是一部学术专著,但它并无通常专业阅读要求的高门槛。只要认得字,大体就能成为它的读者。当年萧先生有意把它当作一部“开荒”的初步著作,“不希望在书中提出高深广泛的学理。我只想把寻得来的资料经过整理之后贡献给读者”。
今年初,知名非虚构作家李辉等人发起青年“返乡画像”书写行动,在我读完《中国乡村》的这天傍晚,书写营正巧推送了上海大学博士王磊光的一篇新作——正是他引发了近年“返乡体”书写热潮。在文章结尾,他似乎不经意地提到自己65岁的父亲,“一个人在家乡做一笔溪岸,快要做完了,他推一块石头,石头太大,推不动,用力过度,自己反而扑在了石头上,撞伤了嘴唇和牙齿,已经两天不能吃饭”。这一场景仿佛19世纪中国农民的某个缩影,催人泪落。
2010年夏天,我前往美国印第安纳波尔州立大学访学。当飞机降落,汽车带我驶离机场,大道与田野依次展现在眼前,凝望着路边摇曳的青草,我忍不住轻轻地颤抖,想起了少年时热爱的诗句,诗人阿垅的《无题》:“要开做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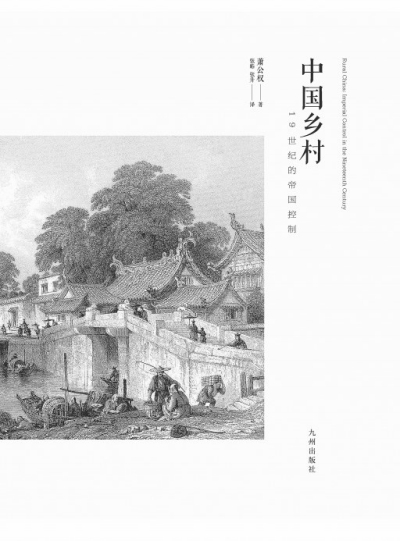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