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明代“四大奇书”之一的《金瓶梅词话》(下文简称《金瓶梅》),自问世起便得到了万历文人的追捧。尤其是这部小说状摹人情之妙肖、铺陈物理之细密,更引来古今读者的击节叫好。然而,古今读者多深谙其于人情上之匠心,而多不解其于物理中之用意。扬之水新著《物色:金瓶梅读〈物〉记》一书,绕开大家熟谈之“人情”,转由看似不尽“人情”之“物理”入手,辨名穷形,索隐抉剔,进而推敲人情,商量世态,正可谓循“物理”而近“人情”。
这本书围绕《金瓶梅》中的十数种器物,一一结构篇章。诚如作者所云,这本书的“关注点差不多集中在物质文化史中的最小单位,即一器一物的发展演变史,而从如此众多的‘小史’中一点一点求精细,用不厌其多的例证慢慢丰富发展过程中的细节”。毋庸置疑,这一研究继承了作者一贯的长处,即十分娴熟地运用“二重证据法”将纸上文献与地下文物相结合,用考古文物还原小说物象的经验原型。作者以《金瓶梅》中一器一物的描写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各类材料——图像、类书、字书、考古文物、展览实物等——推敲、落实一器一物之形制与功用。如《金丝 髻重九两》一篇中,作者结合其多年来对明代女性头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又对《金瓶梅》中 髻的用法和变形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辨析,如作者注意到无论金丝 髻还是银丝 髻,“里外又可以衬帛、覆纱,一面仍是装饰,一面用来适应不同场合的不同妆扮”,《金瓶梅》中作为孝服的白 髻便属后者这一情形。又如《二珠环子和金灯笼坠子》一文,作者分别考辨耳环与耳坠在物质形态上的差别,同时又留意到《金瓶梅》作者写这两类物事时,往往颇见身分之别:耳环往往出现在对月娘等已婚女性的描写中,而耳坠则多用于对年轻未婚女性尤其是丫鬟的描写中。在这本书中,经由具体器物考证而获得的对小说文本更为细致、深入的理解和发现,可谓俯拾皆是。
尽管作者一再声明其旨趣在于借《金瓶梅》研究一器一物的物质史,然而,我们不难读出作者由物及人、品物论人的尝试,正所谓“‘物色’中的世味与人情,自不容轻轻放过”。在对一器一物的考察中,作者总是将器物的特征、功用与对《金瓶梅》情节铺排、人物性情的分析联系起来。因此,这十篇文章绝非《金瓶梅》的十个注脚。该书所选取并详加考证之物事,小到西门庆头上的网巾圈儿,大到“金”“瓶”“梅”三人的拔步床,物无大小,皆饶有深味。小说第十一回潘金莲骄恃新宠,要西门庆往庙上替她买珠子,要穿珠子箍儿;第八十三回,西门庆死后潘金莲与陈经济偷情,秋菊报知月娘来捉奸,金莲情急之下将陈经济藏在床里,自己坐在床上装成穿珠花的样子。扬之水留意到,“买珠子和穿箍儿,珠子箍一前一后的呼应恰好照映潘金莲在西门家的始入与将出”(《珠子箍儿》)。又如,春梅佩戴耳饰的变化,从金灯笼耳坠子到胡珠耳环,正暗示了她从西门宅内身为下贱的丫鬟到守备府夫人的命运变迁,扬之水指出这是“作者以穿戴变化写人物命运起落的一番深心”(《金丝 髻重九两》)。
有异于古典诗文以物抒情的传统,作者还十分敏锐地捕捉到,《金瓶梅》中“没有诗意也没有浪漫,只是平平常常的生活场景,切切实实的功用,成为小说中我最觉得有兴味的‘物’的叙事。……它开启了一种新的,或者说是复活了一种古老的叙事方式”。尽管此种“以物叙事”的方式是否当追溯至作者所说的《诗经》传统仍值得商榷,但作者对《金瓶梅》“以物叙事”的总结可谓冷静而独到的识见。正如作者对小说第六十七回小描金盒情节的分析中所言,“小描金盒里装的一番柔情蜜意,登时被悉数消解。而这才是《金瓶梅词话》独有的精采”(《单单儿怎好拿去》)。小说第二十八回潘金莲不忿宋惠莲,把西门庆偷藏的宋惠莲的一只睡鞋“剁做几截子掠到毛司里去”,此种描写中所谓“人间至情却是没有的”,扬之水却以为“这也正是它的独特之处”。在作者看来,《金瓶梅》“以‘物’叙事,笔墨俭省到无一字可增减,但若解得物色,其中蕴含的丰富即在目前”。小说第二十七回潘金莲不戴 髻、窝着“杭州攒”出现,针对这一描写,作者结合明代的图像资料,再现这种发型的具体样式及其所蕴含的丰富信息,进而得出这一结论,即“不必想象与夸张,止须妙用‘物色’照实去写,人物性情也便随着服饰一起出来了”(《二珠环子和金灯笼坠子》)。
由于《金瓶梅》对明代社会生活尤其是物质生活有着广泛涉猎和深入描写,因此传统名物之学始终是《金瓶梅》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然而,传统名物之学多为“纸上谈物”,即以文史互证的研究范式在不同的纸上文献之间辗转互证。辞典学注释体研究亦属此类,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金瓶梅鉴赏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其中“陈设器用”“服饰饮食”等类,在一手资料的搜集上嘉惠学林多矣,但对具体名物的解释止步于钩沉、补充文献信息,未能直观地还原、再现其经验原型。例如,辞典引用多种文献注解“瓦垅帽”,却未借鉴此前沈从文对瓦楞帽的介绍及其所引用之图像资料,因此满篇下来读者仍不知瓦楞帽具体是何形状。由于辞典学注释未能充分吸收考古发现和物质史研究,因此疏漏和错误往往不可避免。例如,辞典中将“金井玉栏杆圈儿”解释为巾环,而据扬之水的考证可知,此当为网巾圈儿。扬之水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与传统名物之学的一大区别在于,扬之水充分利用了她数十年间对考古发现的持续关注和在海内外的观展经历,将考古学界的最新发现和海内外展馆中“可遇不可求”的展览实物引入到这本书具体的考证、求索中,复活了那些封存在繁复、琐细文字描写中的器物,令读者得以窥见《金瓶梅》作者以物叙事背后的深意。
在这本书的后记中,作者总结她与文学有关的读“物”心得,即“《金瓶梅》开启了从来没有过的对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诸般细微之物的描写。不知道如此异乎寻常的关注何由发生”。尽管此种关注何由发生至今仍未有满意的答案,但《金瓶梅》对日常生活及诸种细微之物的描写热情,却是小说研究界的共识。《金瓶梅》中用以叙事之物,可谓无所不至。一件皮袄便可以伏线千里,预伏于第十五回的元宵佳节中,于第四十六回的雪天寻袄情节中复出,此后又在第七十四回到七十九回中挑起更大的风波。颇为遗憾的是,由于此书旨在发掘有“色”之物,因此对这一类在叙事上相当重要而色相不足道之物缺乏相应的关注。当然,这种不能面面俱到的“缺憾”,也正是该书的独特之处。
古人云“妙思触物骋”,虽然古人所言之“物”为自然之物,但若将其替换为器物或更为广泛的物质,亦可作为对《金瓶梅》叙事风格的总结。张爱玲在《红楼梦魇》自序中曾提到,“这两本书是我一切的源泉”。这两本书,便是《金瓶梅》与《红楼梦》。熟悉张氏作品的读者,当不难发现她对物质细节的着迷与《金瓶梅》作者何其相似。这样一种对物质细节着迷般的热情与专注,不仅见诸小说家,也出现在扬之水一贯的研究中。意大利文豪卡尔维诺曾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一书中提到,“对文学的未来的信心,包含在这样一个认识中,也即有些东西是只有文学通过它独特的方式才能够给予我们的”。《金瓶梅》的妙处,正是“把语言赋予没有语言的东西”,“在于止以物事的名称排列出句式,便见出好处”;而此书的妙处,也正是把语言赋予那些静默无言的器物,由一器一物迤逗出“满纸云霞”。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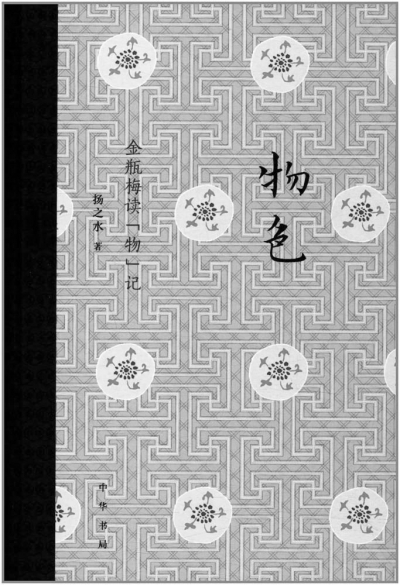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