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点燃了废墟。
火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会接受光吗?
有些人是特殊的存在。他们不惮于回望黑暗,凝视黑暗。他们书写黑暗,以燃烧的心。
从纳粹手中死里逃生的犹太诗人保罗·策兰写下《从黑暗到黑暗》的诗篇。
与策兰有相同创伤的犹太诗人奈莉·萨克斯,写下《夜啊,夜》。
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则以《爱与黑暗的故事》书写犹太民族与自己家族的历史。
黑暗是普遍的。
黑暗也是持久和危险的。“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尼采早就如此警告。战争结束了,策兰却始终未曾逃出黑暗,多年后自沉于黑暗的心湖。
而有些人,本可以安全地停留于黑暗之外。比如钟爱策兰的德国画家安塞姆·基弗。他出生于1945年的德国,20岁进入大学学习法律。战后的废墟与阴影犹在,但战争毕竟已成过去。命运却召唤他,以双手描绘黑暗,建造废墟,重燃火焰,烛照历史。
历史以剑与血铸造历史。血流成河,白骨蔽野。古往今来皆如此。诗人则以语言和韵律记录历史,诗即史。“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一千多年前的唐帝国,杜甫在北征途中,记下历史的一瞬。
画家则以线条、色彩、造型重现历史,比如基弗。但基弗的创作中有浓郁的诗意。有些意象反复出现:天空,原野,森林,洪水,河流和海洋,道路,鹰,蛇,石头,花朵,火与剑,书……铺陈比兴,状物叙事,寓意抒情。以形象去表现,却放弃外在的形似,追求内在的神韵。诉诸形象,直达本质,却又开放多义,这正是诗的特质。诗人们滋养了基弗丰饶的灵魂:里尔克的诗流淌过他的少年岁月;策兰直接启发了他的创作,他的不少作品以策兰的诗为主题,比如根据策兰名作《死亡赋格曲》所作的《玛格丽特》《苏拉密斯》系列;2005年,基弗在萨尔茨堡举办了“献给保罗·策兰”艺术展。策兰诗歌的主题、风格深植于基弗的创作,诗人王家新则注意到了另一种“肌理”的相似:“策兰后期往往运用一种灰烬、残骸、无机物的语言,即他自己所说的奥斯维辛之后‘可吟唱的残余’。基弗常用的材料包括油彩、泥土、铅、石头、灰烬,废品、残骸,模型、照片、版画、头发、树枝、沙子、钢筋、稻草,胶,等等。他将这些材料纳入到巨幅的绘画场景中,构成了画面特有的肌理。”据说基弗本想成为一个诗人,最终他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与策兰携手,徘徊吟唱于废墟之上。他被称为“第三帝国废墟上成长起来的画界诗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弗是一个出色的译者,将历史和诗歌译成画。
这历史当然不仅仅是过去,它也是当下,甚至是未来。谁敢说新千年的我们已走出了那浓重的黑暗?
身处遥远的东方,我们需要一个出色的译者将画重新译成诗歌和历史,我们将发现那废墟绝不遥远。幸运的是,有一位诗人替我们承担了这项艰难的工作。林贤治先生是学者与评论家,本质上却是个诗人。早年他曾写下诗集《骆驼和星》《梦想或忧伤》,而他的散文与评论也往往充溢着浓郁的诗意,或者竟是不分行的诗。比如这本以基弗作品为主题的《火与废墟》,绝非我们常见的文艺批评。从结构就可以窥见诗人的“野心”——引子;天空和大地;博物志;建筑学;政治考古学;艺术:介入和超越。每章又生出摇曳多姿的枝条,如《建筑学》一章分出:法西斯建筑,巴扎克,阶梯,廊柱,门,广场与密室……枝条上再开出疏密有致、情态各异的花朵:长短不一的片段,时缓时急、时轻时重的节奏韵律,段与段间的停顿和空白,或幽黯或秾艳的文字……有些语句索性分行排列,直接以诗的形式出现,如《天空》的开头:
在云飘过之后,
在鸟类和飞机掠过之后,
在咆哮的暴风雪安静下来之后,在太阳月亮和群星隐没了它们的光芒之后
……
这只能是诗,而绝非通常意义上的美术评论。
而在这“之后”之后呢?据说最后留在策兰书桌上的,是一本打开的荷尔德林的传记。他在其中一段画线:“有时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的心的苦井中”。而这一句余下的部分并未画线:“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启示之星奇异地闪光。”
废墟不应沉入忘川。废墟之上,仍有火光。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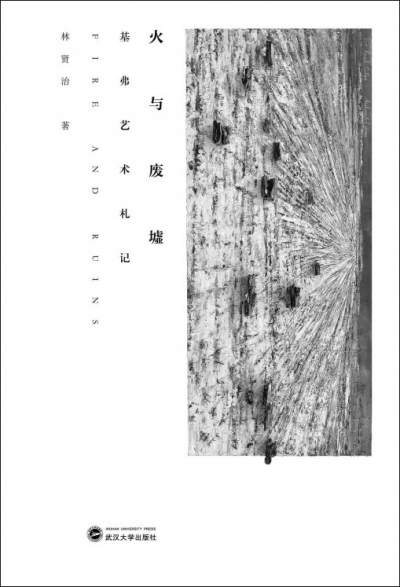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