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鲁迅开启中国现代文学的“归乡”模式以来,“离去-归来-再离去”的身体与心理、现实与幻景的纠葛状态似乎成为乡村写作的惯性存在。当代“寻根文学”中也有“怀乡”和“怨乡”的复杂情感,大抵是“农裔城籍”类作家身处之地与心居之所剥离状态的扭结。这些颇具意味的“逆城市化”文学倾向,极大拓展了乡村叙述的张力,也促生了一些真诚、疼痛、善意的作品。周荣池和他的散文集《村庄的真相》就是一例。
周荣池是在离开村庄多年后开始“回望”乡村的,这种置身事外的回望与反思更加的热切也更加的清晰。他说写作的责任是发现生活的苦难,并且尽自己所能去缓解这些疼痛,这是乡土写作最现实的意义。他希望在乡土中找到写作的价值与意义。尽管那个漫溢着生活苦痛的里下河土地曾是周荣池一直想拼命摆脱的背影,但他依旧“在城里凝望乡村的月光”,用“善意”拥抱疾苦,对给予他养育之恩的里下河风情、风貌、风物以及那里熬活的人们投去深情一瞥。
事实上,“在乡”写作理念早就深植在周荣池创作中。已经出版的散文集《草木故园》和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都是以“里下河土地”为话语中心,前者纪实乡村,后者想象乡村。那么,作为《草木故园》的姊妹篇《村庄的真相》(都起源于系列散文“诗经中的里下河”)是如何具象化展览“在乡”现场、又是如何叩问“村庄真相”的呢?这些“村庄真相”是周荣池的“自为之书”还是村庄全景式客观图景?是村庄现场的真实物事还是关于村庄的“情感真实”?还有,坚守“在乡”写作的周荣池真能回到他的村庄现场么?
村庄伦理是周荣池还原村庄的精神真相。被“开发”前的村庄几乎是静止的历史,村庄人的生存法则、乡村的道德伦理大都与善恶有果的“宿命”相关;节制和风俗作为村庄人的信仰,成为维系村庄日常秩序的恒定方式。巨大的村庄“在场感”在周荣池笔下荡漾着,拉拉杂杂的琐碎都是周荣池经历的选择,是他写作的母体和活水,也组成了他关于村庄记忆的博大信息库。马尔克斯在回忆录《为小说而生》开篇写道:“生活并不是我们的当下,而是一个人所记得的,以及一个人是如何为了讲述它而去记得的”;周荣池说:“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用文字建立虚拟而又真实的村庄史标本。”这是作家的“自为之书”,也是村庄客观图景的主观性表达。
“回不去”是周荣池隐藏在纸本中的另一个讯息。作为城市的“亚类属”人群,周荣池的“种”是村庄的,血脉中有着农人的基因;“属”是城市的,在城市生活、工作,浸润着城市的气息,享受着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便利与安逸。周荣池一再宣称,“回去有时候非常艰难”,村庄的“日子把人穷怕了”,饥饿甚至比死亡更为可怕,所谓的“尊严”“爱情”在贫瘠中可以随时撒手,所谓的“美丽”“诗意”在熬活的人们那里微不足道,“吃饱了”“实用”是村庄里最根本的生存真相,“苦尽甘来”是村庄生存真相的最高信仰……周荣池是诚实的,在物质匮乏中滞留太久的他,用尽气力靠“书包翻了身”,如受伤的野兽般奔向贫瘠村庄外的繁花似锦,终究不肯再“由奢入俭”似的回到过去,这是烙着个人体验和经验式的“回不去”村庄。还有一种“回不去”,是难以面对村庄当下的现实。它是转型时代复杂而普遍的社会心理给予个体生命的精神投影。农业文明和生产个体被强大的市场主义、技术主义击溃,工业化、城市化带来富足的同时也吞噬着村庄生态与古朴民风。“难以面对现实”是周荣池(们)理性的接受新农村与心理的排斥矛盾交织的实化。历史理性与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无法遮蔽的悖论,必然的,乡村写作也呈现出某种“在而不属于”的尴尬场面。写作主体们不能在短期内建立与新的乡村社会存在相匹配的心理机制,“回望”就成为一种普适性心理诉求。“回望”中存储着过往的经验,而写作就是对经验的有机提取。周荣池面朝那片熟悉的场域,建立起一个人的“村庄博物馆”。这个“村庄博物馆”,某种意义上,也是发展时代中国村庄的部分缩影。
无论是主观的意愿还是客观的现实,“回不去”村庄已是周荣池或是周荣池们的主体必然,也是历史使然。村庄,那个原本承载着痛苦记忆的地方,也许,在历经年数、距离、人世的飘浮后,会像鲁迅记忆中反复“美化”成“极其鲜美可口”的蔬果,也要哄骗周荣池们一生,使他们时时反顾润泽笔端了。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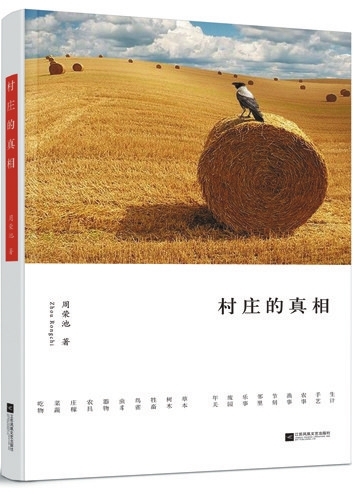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