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认为,自20世纪初纳蒂托·克罗齐的辉煌时代结束之后,意大利思想界早已被法国与德国在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批评理论及后现代主义等领域散发的耀眼光芒所遮蔽。然而事实是,意大利涌现出的新一代年轻思想家中不乏杰出人物,如翁贝托·艾柯、乔万尼·瓦蒂莫、卡洛·司尼、亚德里亚娜·卡瓦勒罗等人,马里奥·佩尔尼奥拉也是其中一员。
佩尔尼奥拉现任罗马大学第二分校美学教授,早年就读于意大利北部的著名学府都灵大学,拜在60年代意大利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大师路易吉·帕雷森门下,与翁贝托·艾柯和乔万尼·瓦蒂莫系出同门。老师帕雷森思想中暗含的“打破界限”的精神,深深影响着佩尔尼奥拉,以至于他的作品始终拥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批判精神。
佩尔尼奥拉著有多部美学著作,其中两部《模拟社会》(1983)和《过渡》(1989)的精华部分被译成中文,取名《仪式思维:性、死亡和世界》,由商务印书馆于2006年出版,成为佩尔尼奥拉著作的第一本中文译本。十一年过去了,他的第二本中译本《当代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终于款款而来。
《当代美学》是一部20世纪美学理论史。之所以将20世纪作为本书考察的时间区段,是因为作者敏锐地察觉到,在20世纪的上半叶,美学已不仅仅是一种关于美与善的趣味的哲学理论。佩尔尼奥拉认为,当代美学更像是一种文化哲学,而不是对美和艺术之本质的一种思考:生命美学获得了政治性意义;形式美学获得了媒介意义;知识美学获得了怀疑论意义;实践美学则获得了交往意义。美学在20世纪发生着整体性转向,而促成这种转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全球化”发展。
全书共18万字,分别以生命、形式、知识、行为、情感和文化等六个问题域各成一章。每一个章节中,会涉及具有代表性的美学家及其主要思想,例如威廉·狄尔泰(1833—1911)代表那些坚信审美经验和生命意义间有着密切关系的哲学家;沃尔夫林的无形式论、李格尔的艺术意志、沃林格的无机风格论构成了对古典主义成见的一种反抗,为美学拓宽了道路;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思想标志着形式美学从艺术哲学转向了媒介哲学。作者在取舍这些代表人物及其观点时,并不是倚靠其知名度和流行度,他相信,瓦尔特·本雅明的遭遇正好说明了,那些一度被边缘化的作者是如何在20年后逐渐获得其地位的。因此,大名鼎鼎的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在本书中只占了区区不到200字的篇幅,佩尔尼奥拉只是在讨论“性感受和差异”问题时“匆匆”提及罗兰·巴特“在快感和文学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佩尔尼奥拉扎根于意大利,却有着全球化的理论胸怀。在其多元视角和历史立场的影响下,他开始关注非欧洲国家的美学家们如何打破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关系,通过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传统来与西方相抗衡。这就形成了《当代美学》的第六章内容,也是全书最具开创性的部分。佩尔尼奥拉用瑞士历史学家卡尔·雅可布·布克哈特的观点来统领整个第六章,布克哈特敏锐地捕捉到西方审美文化即将衰落的信号,从而将目光对准欧洲以外的世界,提出了三个重要理论:一是文化的多元性,二是文化是与国家和宗教同样重要的三大力量之一,三是摆脱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研究方法,它们为欧洲以外的美学开创者们所用,由日本开始,继而是中国、穆斯林国家、巴西、韩国。
佩尔尼奥拉对梁漱溟等两位中国哲学家给予高度评价,并将中国当代美学纳入20世纪国际美学的框架中予以审视,这在整个西方美学界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他在本书的中文版序言中指出,“在希腊,美学与史诗和悲剧中所呈现的神话密不可分;而在中国,美学则与日常生活、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关系密切”。他认为,三大文明力量中只有国家和文化对中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宗教从未在华夏大地上真正存在过。
佩尔尼奥拉高度肯定梁漱溟所指出的关于中国迥异于西方和印度的文化模式的观点。梁漱溟认为,西方过于推崇经济发展,过于被掌握自然的雄心所蛊惑;印度又走向了西方的反面,只关心宗教,厌弃生命,脱离现世。而只有中国文化成功地把伦理和美学成功地连结在一起,这归功于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
佩尔尼奥拉作为一位西方哲学家,对非西方世界的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诚然是一种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阔大视野,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挽救正在衰落和瓦解中的西方审美文化。他在全书最后两个小节中,又回到了西方审美文化的现实问题上。他介绍了雷蒙·威廉斯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状况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除了宗教和国家之外,市场应当是第三个,而且其作用要比前两个大。他在警示西方同胞:最坏的事情就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解构,这一转变很明显转向了以经济利益为最高目的的追求,而这恰恰与任何审美经验都是对立的。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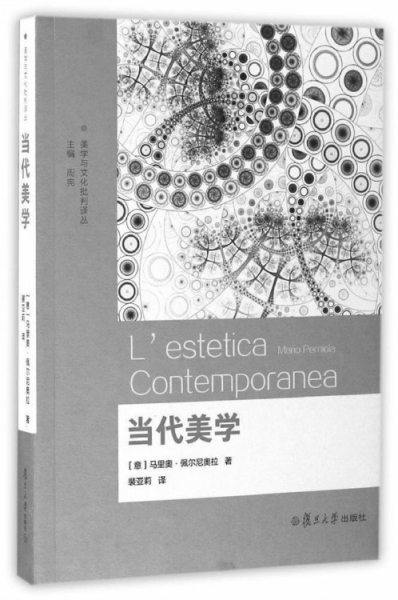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