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知识界,人们大都知道有一部被东西方历史学家和思想家高度赞誉的鸿篇巨制《西方的没落》。该书汉译本在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后,由于内外战乱等因素而沉寂三十年之后,1963年商务印书馆再行翻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安徽人民、湖南文艺、陕西师大、黑龙江人民、上海三联和浙江人民等出版社,都曾重出该书。但由于该书篇幅巨大,内容庞杂,数千年西方历史的典故沓至纷来地拥在读者面前,所以对于对西方文化缺少深入了解的“我们”,如何掌握该书的内容,特别是斯宾格勒的写作宗旨,实有些困难。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我国著名德国文学、哲学的研究专家洪天富教授以《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精粹》为题,对该书的内容进行重译和导读。该书除了介绍《西方的没落》的导论和最为重要的《经济生活的形式世界》外,还译出并导读了俄国著名社会学家达维多夫的《货币与社会:拜金主义的历史》,以及斯宾格勒回应社会对《西方的没落》批评所写的两篇论文:《人与技术》《悲观主义吗?》。这不是画蛇添足。有了这三篇有针对性的内容阐发,才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西方的没落》的思想内容。
《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出版于1918年,第二卷出版于1922年。此时的欧洲被战争摧残得千疮百孔,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更是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数年前还是野心勃勃的社会为何突然走到了死亡的边缘?它能不能被挽救而得以新生?斯宾格勒继承了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狄尔泰,直至歌德的思想传统,将生命哲学化为比较形态学的研究方法,对衰败了的工业文明社会进行了深入解剖,试以消散笼罩在人们心灵中的阴霾。
洪先生说:斯氏“首先是一个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一个生命哲学家,然后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将生命化的‘文化有机体’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以此去审视历史,去质疑过去的文明,去预断历史。作为斯氏思想来源之一的歌德,其观相术乃是用观察人的外在体貌特征的方法来预断人的内在个体特征、精神状态;斯氏将此“艺术”直接用于研究人类的历史,从而产生了“感情移入”,即以灵犀相通的方式直捣社会有机体的内部,以把握它的生命形态的特征与命运。这是一种“有机的逻辑”,而与通常研究历史的机械逻辑有本质的差别。“有机的逻辑是时间的逻辑,生成的逻辑;机械的逻辑是既成的逻辑和空间的逻辑。有机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机械的逻辑也就是文明的逻辑。”
那么,文化与文明难道不是一回事吗?当然不是。斯氏从比较形态学的观点出发,将世界文化分为八个文化圈: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古希腊罗马、拜占庭-阿拉伯、西欧、玛雅文化。不过,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生成、发展、成熟、衰落的阶段。就整个人类而言,当它还与自然界浑然一体,即并无自觉意识时,文化并没有产生。而当“一颗伟大的心灵从人类永远单纯的原始心灵状态中觉醒过来,自动脱离那原始状态,从无形的东西变为一种完型,从无限的和一成不变的东西变为有限的和暂时的东西时,文化便产生了”。洪先生解释道,斯氏的意思是:“当人类获得醒觉存在即意识的时候,文化就产生了。”以此来看,“文化像人和有机体(包括从最小的鞭毛虫到伟大的文化)一样,在经历了诞生、生长、成熟的阶段之后,最终进入了衰朽僵死时期,进入了机械运作的阶段”。一句话,“文明是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既然如此,对文化的认识就必须采用新的研究方法:“生成是处于流变状态的、尚待完善的东西,所以不能被肢解和概念化,只能靠类比的方法,即观相的方法去把握。只有那些业已变得静态和实现了的东西,即已完成的东西,才能够被肢解和通过科学的原则去理解。”
那么,用观相的比较文化形态的方法来认识西方文化、西方文明,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其一,西方文化如浮士德一生追求美好,最终却被魔鬼带入深渊的文化类型,它只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种,既非世界文明的中心,也不是所谓的最优等的文化,这种文化所表现的文明形式从拿破仑的时代就开始衰落。而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所造就的文明本身。斯氏认为:在史前时期,人类过着一种植物的经济生活,即依靠植物和用植物进行经济生活。当人类意识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立的另一极时,其理解力就开始摆脱了纯感觉,而“创造性地介入了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的关系”。凭借着这种经济性的思维,人们创造了农业,这样就把对自然的依赖变成了对自然的控制。然而,农业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即使有简单的交换,人们仍然不会考虑成本、利润之类的事。但随着交换市场一步步地发展而产生了城市,这个“第二世界”就让一部分人离开了土地而专门从事商业活动,“随着物品变成了商品,交换变成了销售,用钱的思考取代了用物的思考”。于是抽象的货币产生了,它成了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而主宰着世界的一切。如齐美尔所说:“金钱是我们的上帝。”也如萧伯纳所说:“对金钱的普遍重视是我们文明中唯一充满希望的事实。”一句话,“用钱思维就能产生出钱——这就是世界经济的秘密”。金钱掌握了政治,政治就变成了金钱;金钱掌握了技术,它就把原来作为谋生手段的技术,转变为掠夺财富的手段。洪先生总结道:“斯氏认为,作为浮士德式的文明之载体的技术,是西方社会一切灾祸的根源。人们感到机械就像是魔鬼;在信徒的眼中,机器意味着把上帝拉下马,机器让人听任因果关系的摆布,迫使企业家、工程师和工人成为它的奴隶。”不仅如此,贪婪的金钱让一切种族、一切政权听命于它的意志,到了此点,事情又产生了变化,即为了金钱,又引起种族间的争夺,结果“种族战胜了金钱”。“金钱的独裁权力以及在政治上的武器——议会民主政治,即将被恺撒主义所取代,于是剑战胜了金钱,主人意志再次服从掠夺者的意志。恺撒和恺撒主义就是战争和专制独裁的代名词。”斯氏的分析不仅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同时也被其后的二战所证实。
那么,作为西方文明标志的先进技术,是否就应该彻底否定呢?斯宾格勒并不持有这种观点。在1931年斯氏发表了《人与技术》的论文。“手”的产生,是人类生成的标志。而技术首先是人“手”的延伸,即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手段,而当语言文字产生促使大脑思维的发展,使人类得以有计划地从事集体的行动后,不仅使社会分化为天生的统治者和天生的对统治者言听计从的奴隶,产生了国家,导致了利益的争夺和国家间的战争,同时也让人产生“人定胜天”的妄想。这样,技术就具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它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和手段,因为有了技术,人对其他动物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成为自己生命策略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人的这种创举,同时也是它的厄运,因为人为了获得这种权力,不得不和自然分离,不得不一再地使自然“合理化”而屈从自己的意志。洪先生说:“斯氏指出,正是人对自然的无止境的掠夺导致人的物化,即人也被功能化,成了技术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换言之,人为了统治自然,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自由为代价。于是,世界的主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机器迫使人沿着它的轨道的方向前进,‘已被推翻的胜利者正被飞快奔跑的套在一辆车上的机头牲口拖向死神’。”这种技术就是西方的命运;换言之,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成为西方的厄运。
其二,西方真的就没有出路了吗?斯氏更不这样认为。这是他借助观相术将文化与文明作相对区别的根本原因所在。《西方的没落》出版后,一方面好评如潮,同时也有人以“文化悲观主义”来诟病斯氏,他著《悲观主义吗?》一文进行辩解。他说:有一些人把古希腊罗马的没落和一艘远洋轮的下沉混为一谈。其实,“没落”可以置换为“完成”,今天的“日落”就是意味着明天的“日出”,所以,“我的著作的真正目的在于向读者提供一个人们可以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图像,而不是人们在其中可以苦思冥想的世界体系”。他还说:“我向来非常鄙视‘为哲学而哲学’。世界上最无聊的东西就是纯粹的逻辑学、科学的心理学、普通伦理学和美学。”因为生活并不具有任何普遍的和科学的东西,而那些所谓的学问,恰恰是在死的、外在的事实中寻找所谓的真理。须知,事实与真理之间是有区别的。同样是“事实”,黑格尔式的绝对真理的追求者将其作为寻找无生命力的法则的材料,而在他这里,则是用以阐明一种思想的例子。洪先生解释说:“每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由于内在的目的性的确定性,遵照有机体的周期的法则,经历诞生、生长、成熟和衰败的过程。这就是人类历史中无法逃避的‘宿命’,这个宿命就是生命活动所固有的宿命。”这样,观相的方法,类比的方法,以及有机的逻辑和时间的逻辑方法,就成为体察宿命的有效方法了。这种方法,就是要依照有机生命的命运,来观察和分析历史的现象和文化的发展,来揭示历史的世界图像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的未来远景。这种方法,就会让人们产生历史的目光,看到历史疾病的对立面,以找到历史的借鉴,从而使文化得以新生。洪先生引用斯宾格勒本人的话说:“不,我不是悲观主义者。悲观主义意味着不再看到任务。而我却看到许许多多尚未解决的任务,我担心我们在这方面会缺乏时间和人才。”
斯宾格勒的研究方法未必不能商榷,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怀是值得肯定的。洪先生一生从事德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其思辨哲学更是兴味盎然,有多种译著问世。如今已82岁,垂垂老矣,然神采奕奕,闻道与宣道之心不已。今读是著,笔锋依健,思路清晰,我学界之大幸矣。祈先生有更多的著作问世,以飨读者。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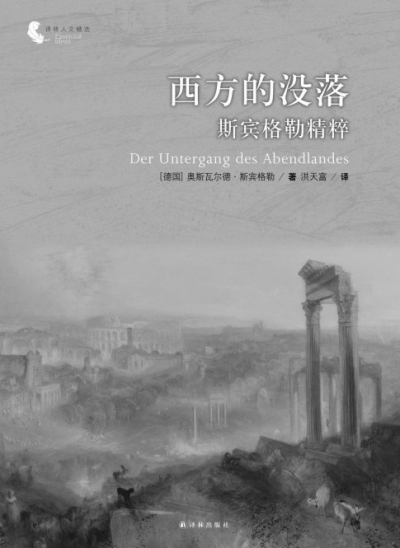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