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一部人物传记像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那样既享大褒亦遭大贬。
对这部著名作品的诟病由来已久。继尤西比乌斯之后崛起的教会史家苏克拉底批评道,此书的写作目的在于对君士坦丁作高度颂扬,而不是要准确陈述事实。这一说法深深地影响着后代学者对《君士坦丁传》的总体评价。如18世纪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在叙述君士坦丁的生平时,便含沙射影地抨击了尤西比乌斯:“有些人热衷谀媚奉承,经常把失败者贬得一文不值,将全部光荣归于获胜的对手。”19世纪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断言,尤西比乌斯为了把君士坦丁塑造成教会的第一位伟大的保护者和理想的统治者,不惜采用“歪曲、掩饰和伪造”等手段,因此他的作品不能作为决定性的史料来使用。与布克哈特同时代的不少学者均拥有类似的看法:克里维鲁奇认为《君士坦丁传》不过是一部历史小说;格里斯认为它的价值与当时流行的拉丁诗人的颂词差不多;曼索则认为它甚至比这些颂词“更加可耻和更加虚伪”。
与此相反,另有学者在极力称赞尤西比乌斯人品的同时,对《君士坦丁传》的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理查森和麦克吉佛特便是这类学者中的典型代表。针对上述各种指控,理查森作出了如是回应:《君士坦丁传》“是由一名有理智和道德能力、并且充满真诚的作者,借助丰富的材料,在没有蓄意造假和误解的情况下撰述出来的,它也许代表了当时的基督徒对于这位皇帝的基本看法,其准确度和诚实度不亚于后来的林肯传或威廉大帝传”。麦克吉佛特则用较为婉转的方式表达了对理查森的支持:“的确,尤西比乌斯强调了皇帝的优秀品德,他未能提及其性格中的黑暗点;可是据我所知,他并没有歪曲事实,他只是做了天下的人们通常都会做的事情而已,即称颂一位辞世的朋友。”
这部著名作品的确是以颂词的形式比较准确地描述了君士坦丁不平凡的一生,因此上述正反双方的观点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客观地说,在颂词充斥着整个文坛的帝国时代,恐怕任何作者都难以戒除掉夸耀和赞颂的文风;尤西比乌斯既然立意要竖立一位基督教皇帝的高大形象,其写作风格就不能不受时俗的影响。因此,评判《君士坦丁传》是否有“谀媚”之嫌,就不能仅限于分析作品中的措辞和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该作品的真正写作动机。“谀媚者”的一个最大特征,是为了谋求一己之私,无原则地讨好长上。在这里,谋私利是目的,讨好是手段。如果一个人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由于某种信仰的原因而对君王有过分溢美之词,则不能算是严格的谀媚。公元327年,安条克主教一职出空,叙利亚人联名致函皇帝,要求由尤西比乌斯来填补这一空缺,该要求虽然一度获得批准,却遭到尤西比乌斯本人的断然拒绝。安条克主教属于大区主教,对整个叙利亚行省的其他主教拥有管辖权,从一个普通地区主教升任大区主教,对于某些贪恋权势的小人来说自然是一件梦寐以求的美差,而尤西比乌斯却对之毫不心动。或许有人会说,他可能有更大的野心,例如谋求更有权势的亚历山大里亚或罗马大主教职位,但是根据当时教会的传统惯例,这种可能性是绝对不存在的,聪明无比的尤西比乌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推动尤西比乌斯蓄意讨好一名世俗君主的政治企图并不明显。
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告诉我们,尤西比乌斯与君士坦丁的私人关系并不像后来的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亲密。他既不是皇帝的廷臣,也不是皇帝的顾问,当然也算不上是皇帝的挚友。他常驻在恺撒利亚,与皇都君士坦丁堡相距有千余公里之遥,他不可能成为皇帝的常客。终其一生,他与皇帝最多见过五次面,所有这些会见都具有集体活动的性质,两人从未有过单独相处的机会。两人的信函来往也不多,皇帝写给尤氏的书函一共不超过六封,而且其中至少有一半是写给包括尤氏在内的巴勒斯坦人或东方主教的。这些函件充满着对收件人的尊重,但语调并不亲密。由此看来,君士坦丁无疑只把尤西比乌斯当作一位值得敬重的作家、学者和神学家来看待,双方交往中所表现出来的更多是礼节和客套,他们的关系并未超出一般君臣之间的限度。
尤西比乌斯对于自己一贯倾慕的皇帝及其亲属,也并非一味地曲意逢迎。实际上,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是颇能坚持原则的。例如,君士坦丁在一次演讲中,曾经长篇累牍地引述西比尔预言和维吉尔的田园诗,力图证明古代异教神谕早就预告了基督的降临、传道、死难及复活;针对这一标新立异的做法,尤西比乌斯并不认可,他质疑道:“(古时)有哪个预言家或占卜师能够预言,他们的仪式将随着一位新神莅临这个世界而消亡、全能君王的知识和崇拜将被自由地授予全人类?”又如,君士坦丁的妹妹君士坦提娅曾经给尤西比乌斯写信,要求他送给她一幅她所听说过的基督的画像;尤西比乌斯在复函中对她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强烈地指责了这种画像的使用,理由是,这会导致偶像崇拜。由此可见,尤西比乌斯虽则尊重帝王的权威,却同时把这种权威置于信仰的控制之下。换言之,在信仰与王权出现矛盾时,信仰仍被看作高于王权。
尽管在尤西比乌斯与君士坦丁之间不存在诚挚的私人交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神学倾向。尤西比乌斯对于三位一体论的理解接近于阿里乌派,在他看来,作为逻各斯出现的圣子虽然也是神,但他不能够与生他的圣父同等,他只能够从属于圣父。贬低圣子基督的客观后果就是相应抬高世俗君王的地位,最终把二者同列于一个崇拜档次之内。因此尤西比乌斯坚持认为,基督和君士坦丁都是上帝的工具,其中一个是宣布上帝王国的到来,另一个是确立一神教;就此意义而言,君士坦丁无异于第二位救主。尤西比乌斯的神学在君士坦丁那里获得了共鸣。这位皇帝在一次演讲中,极力赞扬和推荐柏拉图的二神论。柏拉图把第一神和第二神明确区分开来,让前者居于真实世界之上,后者低于并附属于前者,两者虽是一个单一的完善体,但他们有着不同的本质,而且第二神从第一神那里获得其存在。君士坦丁断言,柏拉图的这种二神论对于基督徒理解神学原理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由此看来,君士坦丁的哲学背景与尤西比乌斯是同源的。
十分明显,君士坦丁虽然在阿里乌争端中常常态度暧昧,可是出于政治上的考量,他最终不得不在神学倾向上偏袒阿里乌派,这是他与尤西比乌斯有效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就尤西比乌斯而言,由于有了这位皇帝的密切配合,他的阿里乌派信仰与其对君士坦丁的尊崇便获得了高度的统一;如今,他得以通过塑造一个人间基督教皇帝的形象,来与天上的耶稣基督相匹配,从而最终实现其阿里乌主义的愿景。总之,尤西比乌斯是出于信仰的原因撰写《君士坦丁传》的,他对君士坦丁的刻意吹捧和神化,不过是一种信仰本能而已,从这一角度看,他算不上是一名真正的谄媚者。既然如此,他的《君士坦丁传》就不能被视作一部献媚之作。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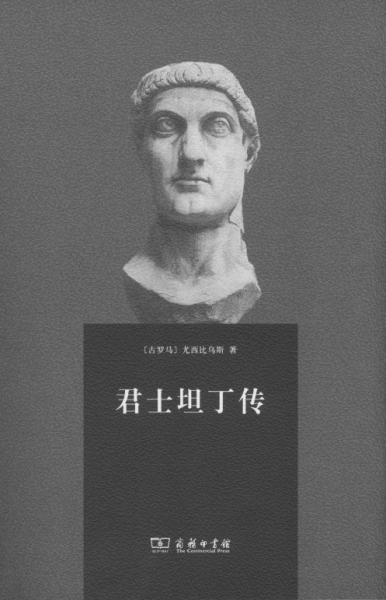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