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过于看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简单化地把它视作突然降临的一场挑战和冲突,结果遗忘、贬低了“变迁之前的变迁”。……在《晚明大变局》一书中,通过强调“晚明也有大变局”,樊树志先生希望讲述的是另外一种叙事。
中国历史上,晚明是一个风云激荡、光怪陆离的时代,并因此而持续地引人回顾、启人深思。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明清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无论是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探索,还是1980年代以来兴盛的“明清市场发展论”,都将晚明当作一个重要的时段;在社会文化史领域,海内外学者都注意到晚明的风俗世情、商业文化与消费观念相对于明代前期的嬗变,并从各个角度开展了引人入胜的分析;而对于思想史及中外交流史的研究者而言,王阳明心学的兴起,以及耶稣会传教士入华带来的第一次“西学东渐”浪潮,向来都是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全面讨论晚明“社会转型”问题的相关专著,更屡有问世,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热度”。
在前不久的“上海书展”上,樊树志先生的新作《晚明大变局》引起了高度关注,并获评“最有影响力的十本新书”,一度脱销。无疑,这是先生多年沉潜于晚明史研究,在这一领域内为学术界及广大读者奉献的又一力作。
《晚明大变局》一书最值得关注的一点是其独到的分析视野,全书对晚明海洋政策、贸易、社会经济、思想、文化交流、士人社会等方面的变革作了系统论述,尤其将这些变革置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强调“变”的外源性,这一点具有高度的启发意义。书名中“大变局”一词,充分体现出樊先生的苦心。他在正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近来人们常说‘晚清的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
众所周知,所谓“晚清大变局”之说,可上溯到李鸿章关于晚清“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认识,而他关注之“变”的核心,在于“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由西方基督教世界及新兴的工业文明带来的外在压力,导致古老“天朝”内部的紧张、焦虑、躁动、冲突等诸多乱象,终至于走向寻求更新和变革的道路,是这一“变局”的本质。将晚明的社会变迁或“转型”,理解为类似的“变局”,无疑是革命性的:它直接否定了李鸿章“数千年未有”的说法;而且,在传统的中国近代史观中,一直到鸦片战争,中国的国门才被打开,在惨痛的被侵略经验和日新月异的西方现代文明的影响下,突破旧体制的“大变局”似乎才能够到来。
其实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形:身居变革“大时代”的人,或许因为炫目于身边新人新事的纷繁层出,或许因为震撼于身历耳闻的苦难、乱离,以及短时间内经历的世事沧桑巨变,沉痛于新旧时代的更替与冲突施于人心的彷徨、挣扎与抉择,往往容易过度地强调本时代及与之相伴之变革的重要性,同时有意无意地遗忘、贬低此前的“平静时代”或“停滞时代”。李鸿章关于他的时代的看法,以及今天的人们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看法,也许正有着类似的特点。我们当然无法否认近代史变迁的激烈性和重要性,但同时应该认识到,以往对于这种“近代变迁”的解读,也许过于看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简单化地把它视作突然降临的一场挑战和冲突,结果遗忘、贬低了“变迁之前的变迁”。我们以为在此之前数百年甚至数千年的历史只是王朝更迭,缺乏“真正的”变化,尽管利玛窦、郑芝龙和揆一的名字如雷贯耳,却不足以改变我们对他们的时代的“定性”。
在《晚明大变局》一书中,通过强调“晚明也有大变局”,樊树志先生希望讲述的是另外一种叙事。在以往的研究中,无论“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转型”,都被视作主要是传统中国内在变迁的结果,这种变迁反映着某些新的历史因素,值得重视,然而它始终孱弱,无法在西方的入侵到来之前,使中国成长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樊先生则指出,“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也就是说,外来的、“全球化”的影响在这个时代已经出现在中国人面前,它至少部分地推动了“晚明变迁”,为“转型”搭台布景。《晚明大变局》以“‘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开篇,继而详述“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无疑正是要提醒我们,“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的故事,早在16世纪已经上演。与19世纪不同的是,此时的海上尚谈不上有“帝国主义”式的强权,然而,由中国海商、日本浪人和葡萄牙冒险家构成的海上走私集团,仍然与闭关自守的朝贡体制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嘉靖时期骚扰沿海十数年、为害极烈的所谓“大倭寇”,其真相不过如此。与19世纪相似的则是,海上贸易的大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新的利益集团与旧体制之间的激烈冲突,最终推动了闭关主义体制的松动。月港当然不是香港或者上海,但在晚明时代,它所具有的意义确实同晚清的上海相似。“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实际上已经是“天朝的崩溃”的先声。
国内商业与市场活动的发展繁荣,是各种“晚明变迁”或“转型”学说中都不能不提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樊先生以其关于江南市镇的卓越研究,已经参与到这一问题的讨论中来。将近三十年后,在“大变局”的视野之下,他以江南市镇为核心,对晚明商品市场的繁荣现象再作解读。同样的,他提醒我们注意这一现象背后的国际因素:“由于生丝、绸缎、棉布等商品的出口持续增长,这种‘外向型’经济,极大地刺激了东南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这种成长固然有其“内在动力”,但“由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日本人全面介入中国的对外贸易,把原先主要面向国内市场的商品生产,转化为同时兼顾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另一方面,早期全球化经济的一个著名后果,是白银从欧洲、美洲、日本和东南亚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这种贵金属“为晚明社会的银本位货币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对于明清时期的商业经济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来说,如果说货币——白银不是唯一的决定力量的话,至少它也是举足轻重的影响因素:白银流入,意味着繁荣,白银流出或者仅仅是停止流入,意味着危机与萧条。因此,即使是在晚明这样一个“传统经济时代”,国内经济形势、社会变迁与全球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比我们以往认识到的更为紧密。
早期全球化还将大群耶稣会传教士带到了中国,从而开启了位居欧亚两端的文明直接密切交流的时代。当然,说到底这也许并非当时思想界的主流,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具有“思想解放”意味的心学潮流,兴起于耶稣会士到来之前,无疑是儒家思想“内在”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和成果。正如樊先生指出的,“西学”在晚明能够得到较为顺利的传播,与王学的兴起造就的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界氛围有关。晚期王学的一些代表人物,特别是李贽,乃至实际上是站在王学的对立面“重整道德”的东林学派的诸多代表人物,与利玛窦及其同事多有接触,并颇有正面的评价。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当时儒学的发展方向?思想史上的命题往往不如社会经济的变迁那样,能够勾勒一个较为清晰的整体轮廓。但一个时代的风气仍能够在历史文献中留下端倪,樊先生毫不含糊地将受西学深刻影响的一代中国文人——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方以智称为“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如同后来的林则徐、魏源、徐继畬一样,他们是自己时代“大变局”的见证者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本好书的价值不局限在书的内容本身,而是能够进一步启发读者的思考。樊先生在《晚明大变局》中巨笔描绘了这一“变局”的主要方面,尤其揭示了它背后全球化时代的清晰潮声,——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大变局”一词用于晚明的历史意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许可以继续追问:晚明大变局与晚清大变局的关系如何?它们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阶段,还是具有相似面貌的两个历史过程?晚明的事情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应该如何评价?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樊先生也没有给出一个简单化的回答。只是在谈到从王学、西学激荡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人结社活动时,他做了这样的评论:这一历史现象“随着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在政治高压与文化专制的双重打击之下,已成强弩之末,日趋萎缩”。将这一评论扩充到整个“大变局”的历史命运上,当然是简单化的。我们需要注意到,与16世纪相比,17世纪见证的是全球化运动的暂时退潮,贸易与经济史家发现“17世纪的萧条”,东西文化交流史的探索则同时看到了日本的禁教锁国、耶稣会中国传教事业中的“礼仪之争”。两个文明体系的初步接触激起了火花与浪潮,但也迅速地面临着敌意和冲突,我们不知道17世纪的故事本身正是冲突的结果,或者倒是推迟了冲突的来临,给了双方积蓄力量的机会。事后诸葛亮地看,经过18世纪表面上的平静与繁荣,一场全球化运动的狂飙将在东西方世界同时展开,最终将中国带进下一个“大变局”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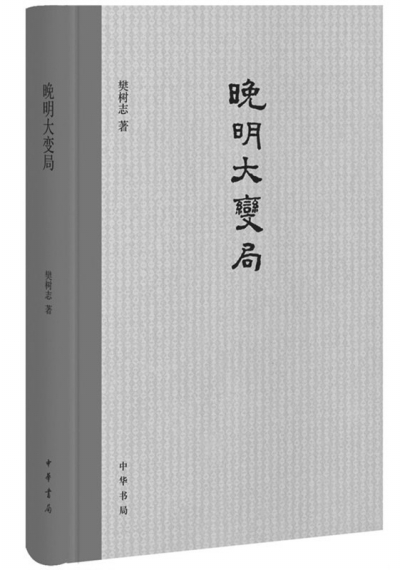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