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文革”过来的老人们再回首时如何判断和评价“文革”,是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众所周知,巴金在“文革”结束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忏悔。他的《随想录》一书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以罕见的勇气“说真话”,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树立了一座丰碑。而新近出版的《我不能不探索:彭燕郊晚年谈话录》则展现了另一种看待“文革”的态度。
彭燕郊(1920—2008)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文艺活动家和民间文艺工作者。青年时代曾参加新四军,后在桂林、重庆、香港等地从事创作和文艺活动。在此期间,他结交了胡风、冯雪峰、聂绀弩等人,被人们视为“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1949年后定居湖南,先后任教于湖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1955年,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彭燕郊被关押审查,之后下放到工厂劳动,几经磨难,直到“文革”结束,中间经历了长达22年的光阴。可以说,彭燕郊一生中精力最为旺盛的时间段都被无情地浪费了。
按道理说,彭燕郊对“文革”应该是深恶痛绝的,就像其他很多过来人一样,他大可以创作几篇“伤痕文学”出来。但事实不是这样,他对“文革”中的人和事似乎始终保持着一份理性和宽容。
这样的理性和宽容在书中随处可见:“我这个人觉得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历史规定了的,与他个人无关,有些人对我表现得很凶恶,哎呀,我觉得他也好像不能不这样吧。”“当时湖南师院中文系有一个教授,哎呀,这个人最紧跟了,每一次运动他都是最积极,好多人恨他恨得要死。‘反胡风’的时候,他当然也是积极分子,搞我也搞得很厉害。改革开放以后,他见到我很不好意思,但发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他非常感动,到处讲,彭老师这个人真是不一样。我何必去怪你,你不过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工具,是一个历史的卒子。我有本事我去恨那个头头,这个没有意思,头头我都不恨,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个人的事情。”这样的话语听起来轻松,甚至还略带些调侃。当时文艺界的状况是否真如彭燕郊讲述得这么轻松?显然不是。对于当年斗争的残酷,身历其事者皆有心惊胆战之感。彭燕郊自然也不例外。然而,诗人以他独有的赤子之心直视着发生在他身边的一切,他能很快把自己从当事人的位置转到旁观者的位置。“我总觉得,谁也没有围过我,外界始终没有影响过我,我挨过那么多次的整,你整你的,我无所谓。”
同时,写诗成了他在动荡年代里的寄托,是他“安身立命的地方”。在“文革”期间,他的很多诗都是写在碎纸上,“但也要防备,随时有被抄家的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仍然写出了《野史无文》等诗集,后来列入陈思和编的“潜在写作”丛书中。也正因保持着这份“诗心”,彭燕郊才能在晚年仍然坚持探索,并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他不断有《混沌初开》《眼睛》等长篇作品面世,并策划或主编了“诗苑译林”“国际诗坛”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丛书,被时人称为“彭燕郊现象”。
彭燕郊的这种宽容是源于他清醒的头脑和对历史通透的认识。他一再强调的“历史规定性”看似无奈之语,其实又何尝不是一种超脱?历史往往是由大人物来决定走向的,小人物只能选择跟从或者反抗。拿彭燕郊来说,他很早就参加了新四军,坚定地支持共产党、反对国民党。他始终相信他站在正义的一方,但当他深信的毛主席亲手发动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时,作为小人物的他,除了冷眼旁观,似乎也很难有更好的选择。正因为如此,“文革”期间,作为旁观者的他在别人忙于整人和被人整的时候得以继续阅读和写作,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在监狱的时候,他在心中默默写诗,每段用一个词代表,不断默记,出狱后凭记忆写下来。晚年回忆起这些事时,彭燕郊还不无自得地说:“‘文革’闹了没多久,造反派都打仗去了,武斗去了,他们抢了很多内部书,有些年轻人有这些渠道,他们搞到内部书就给我看,很有味的。”“短的小册子也出了很多……每本书都批判,反正随它批判,我们看了真是好舒服的。”无独有偶,彭燕郊的湖南老乡、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文革”时被关在秦城监狱八年,无聊中学做旧诗词。没有纸和笔,他就把受伤时护士给的龙胆紫药水和棉签藏起来,悄悄在纸壳反面记录下他写的旧诗词。出狱后,他把狱中抄写的旧诗词集为一册,名字就叫《龙胆紫集》。同时,因为这份清醒和通透,“文革”也并没有对晚年的彭燕郊产生太多消极影响。他有革新的精神,“一个人僵化了是最悲哀的”,“不‘变’,不探索,等于封笔”。与之成鲜明对比的是,曹禺在1980年代仍然缩在过去的袍子里不敢露出头来,因而才有痛批《苦恋》和痛斥“自由化”的事情发生。
彭燕郊又是个性情中人,晚年谈话中的故作轻松之语终究掩盖不了他内心的沉痛。大家都知道,彭燕郊走入文坛首先就得益于胡风的提携,因而他一向把胡风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文革”后有一次在上海开会讨论胡风,他“在台上就哭起来了”。还有一次,“我在家里看梅志大姐写的《往事如烟》,胡风被关进大牢,后来放回来,还在软禁中,梅志大姐煮鸡蛋给他吃,胡风就哭起来了,说你不要害我啊,他们晓得了可不得了了啊。胡风这个铁汉子被磨成了这个样子,我哭了好久。”
宽容也不等于放弃是非心,在宽容的同时,他保持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正义感。比如对于1949年后诗人臧克家的某些做法,彭燕郊就颇不以为然:“个人崇拜的力量太大了,他把毛泽东的信印出来就是‘克家同志’。好厉害呢。”“后来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他碰到我,说,我们大家要互相原谅。我心里想,我有什么东西要你原谅的。”而对于久负盛名的郭沫若,彭燕郊也有自己的想法:“郭沫若这个人啊,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的成分很大,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文学家,他不可能是一个文学家,也不可能是一个思想家。说他是政治家也好像还不够,毕竟是文人,从根本上是很理想主义的。”这样的评价可以说是知人之论。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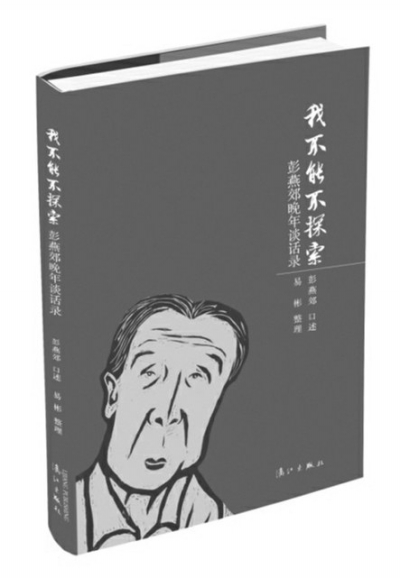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