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风景画往往是先有形式,先发现具形象特色的对象,再考虑其在特定环境中的意境。好比先找到有才能的演员,再根据其才能特点编写剧本。有一回在海滨,徘徊多天不成构思,虽是白浪滔天也引不起我的兴趣。转过一个山坡,在坡阴处发现一丛矮矮的小松树,远远望去也貌不惊人,但走近细看,密密麻麻的松花如雨后春笋,无穷的生命在勃发,真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是我立即设想这矮松长在半山石缝里,松针松花的错综直线直点与宁静浩渺的海面横线成对照。海茫茫,松苍苍,开花结实继世长!我搬动画架上山下山,山前山后捕捉形象表达我的意境。
崂山渔村
崂山一带渔村,院子都是用大块石头砌成的,显得坚实厚重,有的院里晒满干鱼,十足的渔家风味。我先写了一首七绝:
临海依山靠石头,
捕鱼种薯度春秋。
爷娘儿女强筋骨,
小院家家开石榴。
我便要画,在许多院子中选了最美最典型的院子,画了院子,又补以别家挂得最丰盛的干鱼。画成,在回住所的途中被一群大娘大嫂拦着要看,她们一看都乐开了,同声说这画的是✕家,但接着又都惊叹起来:“呵!他们家还有那么多鱼!”因她们知道这家已没有多少鱼了。
粪筐画家
在林彪、“四人帮”控制时期,我们学院全体师生在河北农村劳动,生活无非是种水稻、拉煤、批判、斗争……就是不许作画。三年以后,有的星期天可以让画点画了,我们多珍惜这黄金似的星期天啊!没有画具材料,设法凑合,我买了一元多钱一块的农村简易黑板,刷上胶便在上面作油画,借房东的粪筐做画架。我有一组农村庄稼风景画,如高粱、玉米、冬瓜……就都是在粪筐上画出来的,同学们戏称我为“粪筐画家”!河北农村不比江南,地形是比较单调平缓的,不易找到引人入胜的风景画面。同农民一样,几乎天天是背朝青天面向黄土,因此对土里生长的一花一叶倒都很熟悉,有了亲切的感情,我画了不少只伴黄土的野花。有一次发现一块形状不错的石头,照猫画虎,将它画成大山,组成了“山花烂漫”,算是豪华的题材了!
井冈写生
1957年我到井冈山写生,当时山中人烟稀少,公路仅通到茨坪。我黎明即起,摸黑归来,每天背着笨重的画具、雨具和干粮爬数十里山地。有一回在双马朝天附近的杂草乱石间作画,一个人也不见,心里颇有些担心老虎出现。总算见到来人了,一位老大爷提个空口袋,绕到我跟前略约看看我的尚看不清是什么名堂的画面,无动于衷地便又向茨坪方向去了。下午约莫四点来钟,这位老大爷背着沉甸甸的口袋回来了,他又到我跟前看画,这回他兴奋地评议、欣赏图画了,并从口袋里抓出一把乌黑干硬的白薯干给我,语调亲切,像叔伯大爷的口吻:站着画了一天了,你还不吃?
1977年,我第二次上井冈山,公路已一直通过我前次步行了四小时才到达的朱砂冲哨口。我在哨口附近作了一幅油画,画得很不满意,几乎画到了日落时分,才不得不住手。公路车早已收班,硬着头皮步行回住所去,大约要夜半才能走到。幸好拦截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木头堆得高高的,爬不上人,驾驶室里也已有客人,我勉强挤下,一只手伸在窗外捏着遍体彩色未干的油画,一路上,车疾驰,手臂酸痛难忍,但无法换手,画虽不满意,像病儿啊,不敢丝毫放松,及至茨坪,手指完全痉挛麻木了!
站
1959年,我利用暑假自费到海南岛作画,因经济不宽裕,来回都只能买硬座。从广州返北京时,拖着大包尚未干透的油画,而行李架上已压得满满的,我的画怕压,无可奈何,只好将画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手扶着,人站着。一路上旅客虽时有上下,但总是挤得没个空,谁也不会同意让我的画独占一个座位。就这样,从广州站到北京,双脚完全站肿了,但画平安无恙,心里还是高兴的!
乐山大佛
四川乐山大佛,坐着,高七十一米,是世界第一大佛,如他站起来,还不知有多高!不过,单凭巨大倒未必就骇人,主要是由于岷江和青衣江汇合的急流在他脚下奔腾,显得惊险万状。当我了解到由于此处经常覆舟,古代人民才凿山成佛以镇压邪恶,祈求保佑过路行舟的安全时,我于是强烈地想表现这种劳动人民的善良愿望和伟大气魄。迎着急流险滩,我雇小舟到江心写生,大佛虽大,从远处画来,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石刻,只能靠画中船只的比例来说明其巨大的尺度,但这只是概念的比例,逻辑思维的比例,并不能动人心魄。我于是重新构思,到大佛脚下仰画其上半身,又爬到半山俯画其下半身,再回转头画江流……是随着飞燕的盘旋所见到的佛貌,是投在佛的怀抱中的佛的写照,佛的慈祥安宁,似佛光的雨后彩虹……想让观众同作者一起置于我佛的庇护之中。
群众评画
我作画,追求群众点头、专家鼓掌。一般讲,我的画群众是能理解的,我在野外写生时经常听到一些赞扬的话:“很像”、“很好看”、“真功夫,悬腕啊!”这些鼓励的话对我已不新鲜,引不起我的注意。只一次,在海滨,一位九十多岁的老渔民坐在石头上自始至终看我作完一幅画,最后一拐一拐离去时作了一句评语,真真打动了我的心弦。他说:“中国人真聪明,外国人就画不出来!”估计他没有看过多少外国人的画,可能年轻当水手时吃了不少帝国主义的苦头,那强烈朴素的爱国主义感情使我永难忘怀!
塞纳河之溺
我年轻时在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有一年复活节,照例放假一周,一位法国同学邀我一同去塞纳河写生。
他的设想很美,我们两人自己驾驶一只小船,带上帐篷、毛毯、罐头……自然还有画具,沿塞纳河漂流而下,哪里风景好,便在哪里多住几天。他父亲在巴黎当医生,在乡间塞纳河畔有自己的别墅,周末和节日全家便到别墅度假。我们先在他家漂亮幽静的别墅住了一夜,夜晚观光了乡间的露天舞会。第二天一早,我那同学他自己扛起一只小船,什么船呀,几根细木条做的构架,其间用防水帆布蒙满而已,就像在海滨游泳时用的玩具小舟。他家保姆、弟弟和妹妹帮我们背着画具和用品送到河边去,他父母也送出了大门。
郊野的塞纳河可不是巴黎市内的状貌了,十分宽阔,浩浩荡荡,像江流一般,那小舟放到河里时,不过是一片小小的树叶,被波浪打得飘摇无主。我心里发寒了,但能表露恐惧吗?中国人害怕了?何况他家保姆和弟妹还正在高高兴兴祝贺我们这一趟别致的旅行呢。塞满什物,再坐进两个人,小舟里已无丝毫空隙,我们顺水而去。不仅顺水,而且顺风,我那同学立即又挂起了布帆,真有两岸风光看不尽,千里江陵一日还之势。可只飞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就遭了覆舟灭顶之灾,两人几乎同时抓住了半浮半沉的小舟,在波涛中挣扎。我童年在农村学过一点土法游泳,被讥为狗爬水,而且只能在平静的小河里爬那么四五公尺,此后再也没有下过水。生死关头人总要竭力自救,我先用一只手脱去了皮鞋,再想脱西装和毛衣,但脱不掉了。漂浮了大约二十来分钟,不见有船经过,我那同学说他先冒险游上岸试试,他放开小舟,冲着风浪向遥远的彼岸游去,我紧盯着他的命运,暂时忘了自己的命运,因他的命运也紧紧联系着我的命运。他抵岸了,他向四面呼喊,但杳无回音,不见人啊!春寒水冷,我已冻得快麻木了。终于有一只大货船经过了,在我们声嘶力竭的呼救下,大船缓缓停下来,放开它尾后拖随的小舟来将我捞起,送到了岸边的沙地上,其时我大约已在水里泡了五十分钟。得救了,打着寒战,回头看那可怕的江面,我们的小舟和毛毯尚在漂浮,还有面包,像泡肿了的女尸的脸。我们两人赤脚往村里跑,被人们热情地接待,烤火,打通电话后,同学的父亲开车来接我们回到了别墅里。
塞纳河是印象派画家们笔底最美丽的河流吧,我几乎就葬身在印象派的画境中!
偷画码头
山城万县面临长江,江畔码头舟多人忙,生活气息十分浓厚,是最惹画家动心的生动场景。
我1973年到万县,“四人帮”控制期间,规定码头保密,不让画,我不甘心。我这样构思:从后山背面画层层叠叠的山城气势,其间还有瀑布穿流,再将江畔码头嫁接到画面底部的山城脚下。在后山写生又比山城正面僻静,少干扰。我先躲在一个小弄堂角落偷画了码头,然后又提着未完成的油画急匆匆走偏僻小巷赶到后山去。发觉后面有人追来,我加快步子,那人也加快步子,他穿着一身旧呢子军服,像转业军人模样,我心想糟了,公安部门追来了,码头已画在画面上了!他追上了:“你是哪里的?”“北京。”“哪个单位的?”“中央……”“你叫什么名字?”我正预备摸出工作证来,他接着说:“我是文化馆搞美术的,这里画画的人我都认得,老远见你在画,没见过,想必是外地来的,你走得这么快!我们文化馆就在前面,先去喝点水吧!”
听香
1980年的春天,我带领一班学生到苏州留园写生,园林里挤满了人,行走很困难,走不几步,便有人嚷嚷:“同志,请让一让!”原来他们在拍照,那国产的海鸥相机大概价格便宜,很普及,小青年都在学照相。那些姑娘们拍照真爱摆姿势,有斜着脑袋扭着腰的,有一手捏着柳叶的,有将脸庞紧贴着花朵的,她们想在苏州园林里留下自己最美丽的身影吧!园林里有什么好玩呢?于是嗑瓜子、吃糖果、打扑克……与其说听音乐,倒不如说显示自己手提了新式录音机更得意吧,满园都在播放邓丽君的歌,邓丽君成了园林里的歌星,不,是皇后!学生们诉苦了,无法写生,我只好采取放羊措施,宣布自寻生路去罢!
到了晚上,我的研究生钟蜀珩不见了,她回来得特别晚。她曾躲进了园林里一个极偏僻的角落,藏在什么石头的后面,悄悄地画了一天,静园关门的时候值班人员未发现她,她也没注意园林在什么时候已关门了,当她画完时已无法出园。她在园里来回转了好几遍寻不到出园的任何一个小门,最后只好爬到假山上对着园外的一个窗户呼喊,才引来管理员开了门。她说,她在园里转了一个多小时,没遇见一个游人,她才真正感受到了园林的幽静之美。我没有这样的好运气,真羡慕她遇见了园林的幽灵!狮子林的走廊里写有两个字“听香”,道出了园林的美之所在。
速度中的画境
1972年,我第一次路过桂林,匆忙中赶公共汽车到芦笛岩去看看。汽车里人挤极了,没座位倒无所谓,但我被包围在人堆里,看不见窗外的景色,真着急。我努力挣扎着从别人的腋下伸出脑袋去看窗外的秀丽风光,勉强在缝隙中观赏甲天下之山色。一瞬间我看到了微雨中的山色,山脚下一带秋林,林间白屋隐现,是僻静的小小山村,赏心悦目谁家院?难忘的美好印象。我没有爱上芦笛岩,却不能忘怀于这个红叶丛中的山村。翌晨,我借了一辆自行车,背着油画箱,一路去寻找我思恋了一夜的对象。大致的地点倒是找到了,就是不见了我的对象,于是又来回反复找,还是不见伊人。山还在,但不太像昨天的模样了,它一夜间胖了?瘦了?村和林也并不依偎着山麓,村和林之间也并不是那样掩映衬托得有韵味啊!是速度,是汽车的速度将本处于不同位置的山、村和林综合起来,组成了引人入胜的境,速度启示了画家!
监牢被卖
1960年到宜兴写生,发现一条幽静的小巷,一面是长长高高微微波曲的白围墙,另一面也全是白墙,多属时凸出时凹进的棱角分明的垂直线。两堵白墙间铺着碎石子的小道,质感粗犷的路面一直延伸到远处的街口,那里有几点彩色在活跃,是行人。从高高的白围墙里探出一群倾斜的老树,虽不甚粗壮,但苍劲多姿,覆盖着小巷,将小巷渲染得更为冷僻。我一眼便爱上了这条白色的小巷,画了这条小巷。
事隔二十年,去年我再到宜兴写生,这条白色的幽静小巷依然无恙。这回是早春,这白围墙里探出的老树群刚冒点点新芽,尚未吐叶,蓬松的枝条组成了线的灰调,与白墙配得分外和谐,我于是又画了这条白色小巷,画成了我此行最喜爱的一幅作品。在宜兴住了一个月,画了一批画,临走时许多美术工作者和朋友们来看画,他们赞扬,因感到乡土情调的亲切。只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同志提醒我,说那幅白色的小巷不要公开给人看,因那白色的围墙里是监牢。
回北京后不久,中国美术家画廊邀请我在北京饭店举办一次小型个展,同时出售少量作品,售画收入支援美协活动。我同意了,展出作品中包括了我自己偏爱的那幅白色小巷,但说明此画属于非卖品。展出结束后,工作人员来向我交代,“白色小巷”偏偏列在已售出的作品中了,我很生气,他们直道歉,说一位法国人就坚持要买这一幅。我所爱的监牢就这样被悄悄卖掉了!
今年我因事又经宜兴,匆忙中又去看望一次白色的小巷,白墙已被拆除一半,正在扩建新楼了。
牧场与毛毯
我在新疆白杨沟的山坡上用油彩画那一目了然的大片牧场,一群学生围在背后看我作画。我画得很糟,可以说彻底失败了,我的调色板上挤满了大堆大堆的各种绿色,硬是表现不出那辽阔牧场的柔软波状感。心里很别扭,傍晚躺在床上沉思,探索失败的关键原因。同学们进屋来看望我,我立即坐起,偶一回头,看到刚被我躺过的床上有文章了!黄黄的单一颜色的毛毯覆盖着棉被和枕头,因刚被我躺过,那厚毛毯的表面便形成了缓和的起伏,统一在富有韵律感的皱纹中,这不就像牧场吗?牧场的美感被抽象出来了!
我于是便和同学们谈开了,总结了我白天的失败,认识到要着重用线的表现来捕捉牧场的微妙变化,一味依靠色彩感是太片面了,如绿色的牧场染成黄色的牧场,构成牧场美感的基本因素不变,毛毯给了我们启示,第二天同学们在色彩画中果然用偏重线的手法表现了牧场,效果比我画得好多了。
(摘自《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100.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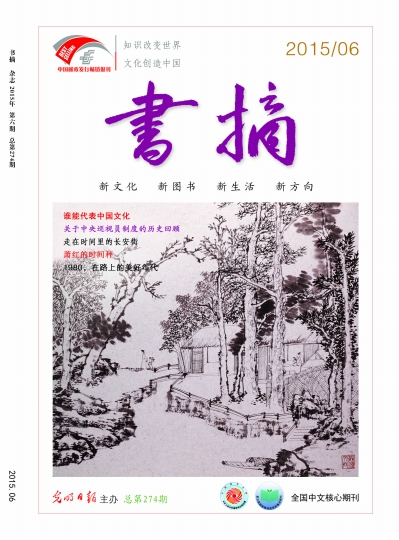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