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漪园时期,现在排云殿和其东侧的介寿堂都不存在,当时这一组建筑群均为宗教类建筑,名为:大雄宝殿和慈福楼。有供皇太后(乾隆母亲)礼佛的功能。这组建筑毁于1860年英法联军的大火,在1885年以后的复建中,慈禧太后根据新的需要,将佛香阁下面的主要建筑改为民用建筑,其中包括佛香阁下面的两边院落改成供百官朝贺用的排云殿和德辉殿,在慈福楼的基址上修建了两进院落改称介寿堂,供慈禧休息之用。
位于排云殿东侧的介寿堂为一组灰瓦顶的两进院落,平时因不对外开放而很难进入;这次因为有学生在里面测绘,才得以一探究竟。
这里朝向昆明湖的大门时常紧闭,要想进到内部,必须先沿着一条分隔排云殿与介寿堂两个院落的甬道由南端走到北端,然后通过角门先进到靠北的院落:院落呈扁长形,东西宽,南北窄,位于中轴线正中的五间北房呈凸字,前有檐廊,当是这组建筑的实际中心。围合四合院的东西配房各三间,也有防雨的檐廊,院中两棵高大的雪松长得枝繁叶茂,依然生机勃勃。
可从西侧过廊走到前院,也就是靠近湖岸的院子。
这个院子由于南北方向较长显得比北院宽敞,院中的东侧和南侧为游廊,仅在西侧和北侧建有房屋,北侧的正房曾做客厅和书房使用,至今内部还保留着一些室内陈设,包括条案、八仙桌、几凳等,从做工和材质看,当为清末遗留下来的旧物。
有几棵古柏依然挺立在院落中,其中的两棵古柏主干在中部相“搭接”,远处看犹如“介字”,据说这也是这组建筑被称为介寿堂的原因。
目前有些颐和园的工作人员在院子两侧的建筑里活动,或开会或办公,看来是作为园内内部办公在使用。后来了解,这里也是颐和园研究会的所在地。
民国时的1930年代,恭亲王奕的儿子溥滢育有二子,长子溥伟,二子溥儒(字心畬)。溥伟袭爵成为小恭亲王,热心于“恢复祖业”,后来卖掉城内的恭王府房产和内部珍玩以筹措军饷;二子溥儒无心政治,在日本人占领北平时期曾借住在颐和园介寿堂内十年。时近中年的“旧王孙”溥儒在这里读书、作画、写诗,靠手中画笔支撑身边人的生计,以诗文记录着他的“亡国之痛”。
在民国政府承认的“清室优待条例”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清朝皇帝让出政权以后,颐和园依然划归清皇室所有,当时也有逊帝溥仪搬离皇宫后迁居到这里的设想。由于后来军阀混战,民国政府的首脑频繁更换,“清室优待条例”并没有执行下去,由此发生了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手下的将领“逼宫”,匆匆离开紫禁城的事件。实际上,这时的军政府已经无法容忍溥仪搬到颐和园,他只能先借住在老家醇王府,随后躲避到天津的张园和静园,再后来在日本人的扶持和控制下,去长春做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面对清室的退位诏书,清宗室内也有很大争议,肃亲王(善耆)和小恭亲王(溥伟)等一干人并不甘心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先是通过组织宗社党,后是筹措私人武装,企图想恢复祖业。尽管面对“气数已尽”的大清王朝,这种努力看似徒劳,但他们却是很认真地去实施着一些举措。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溥伟(溥儒的哥哥)将恭王府连同里面的古董分别出售给北京城里的教会和一些外国商社,用这些换来的钱款去搞“复辟”大业。
1924年,溥儒结束在北京西山戒台寺的隐居生活搬回恭王府时,已经只能住在王府后面的花园“萃锦园”中。由于生计断绝,从这时起,他开始靠典卖祖传文物和鬻书卖画,好在他画的宋人风格的山水和花鸟不同凡响,一家人靠他的画笔为生。
在那个时代,社会上既没有像样的博物馆,也没有现在这般雅致的印刷品,要想提高绘画技艺,一是靠拜师学艺,一是靠临习和观赏家族的收藏;恭王府里的丰富收藏满足了溥儒成为书画家的基本条件。对于当年的王公贵族来说,书画这种技能仅仅是一种展示修养和消磨时间的“玩意儿”,谁也没想靠这些谋生,溥儒卖画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溥儒刚开始卖画的几年,为了顾及“王府”的颜面,溥儒也不能每年都搞画展(卖画),只能两年搞一次。得到社会认可以后,则有画商到府里订件,然后再拿到琉璃厂的画店出售。
即使后来成为著名画家,溥儒也把书画看成“雕虫小技”,而往往更看重自己的诗文和著述。对他而言,除了一些字画要拿出去换“钱粮”外,高兴时写画的许多东西都随手送了身边的朋友和学生,也使得一些人后来拿去换了银子或成为收藏。
1937年,溥儒生母项太夫人去世后,为办丧仪,他以三万大洋卖掉了祖传的墨宝《平复帖》,此帖被当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购得,1949年以后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
1938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年,溥儒一家迁往颐和园的介寿堂租住,重新过起了隐居生活。
在颐和园这段日子,溥儒画画的时间占了大多数,据他身边的人回忆:
先伯父居颐和园时期,是在沦陷期间。平时蛰居作画,很少与外界往来。偶有人来,如梅兰芳前妻孟女士,《时报》主编管翼贤等人,闲谈而已。心畬先生生平,对金石古董之类,特别珍爱。……一时琉璃厂古玩商,争来以石换画,大谋其利。此外,先生还爱古砖瓦、陶俑、陶器之属;但所藏之物,多为古玩商行骗之赝品,先生顾而乐之,日久天长,在桌下屋角,积成瓦砾一堆而已。
溥儒的绘画作品多表现荒寒之景;在残山剩水间,发泄出国破家亡的苦痛,给予观者一种悲壮苍凉之感。在这期间,表现写实的作品不多,《昆明秋色》是少数以佛香阁为主题的作品,他在画中题有:
太液惊波起,秋风满上林。
如何赋禾黍,遗恨遍江浔。
日本人占领北平,对溥儒而言,是双重“国变”,其心情格外沉重,所填词曲也愈发低沉,这在所赋《八声甘州,秋日怀苍虬侍郎》中可见一斑:
望幽燕暮色对残秋,千峰送斜阳,正萧萧木叶,沉沉边塞,滚滚长江。已是登临恨晚,谁共赋沧浪。
更何堪,江山异色,怨黍离,转眼变沧桑,伤心处,远天鸣雁,声断潇湘。
这期间,他也曾寄诗给宗室画家溥雪斋,在《壬午秋怀雪斋从兄》的五律中共勉坚守民族大节:
湖上闻归雁,秋风寄所思。
共期薇蕨老,敢忘棣华诗。
丧乱书难尽,艰危节自持。
脊令原上望,流涕此何时。
因为1949年以后溥儒去了台湾,他的名字和绘画作品便很少出现在大陆的宣传媒体上,上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才得以了解一个不同于“大阿哥”的满族后裔。
因为一到傍晚,介寿堂会随着颐和园工作人员的作息而关闭,使我没能看到这里“掌灯时分”以后的样子。
因要考察、核实一些专家所说的建筑“错中”现象,就选取沿着万寿山山坡建设的两组建筑——听鹂馆和画中游——来看。由介寿堂出来,沿着长廊北侧的小路可以一直来到听鹂馆的正门北面,看了一眼“金枝秀华”的金字门匾,就又顺着原路折到“山色湖光共一楼”建筑的东侧山路上,由此爬到画中游南侧的一段平台上。
研究建筑群的中轴线“错中”,在平地上是看不清楚的,只能找一个高地,采取俯视的角度研究全局。站在澄晖阁的二层平台上,可以俯视下面的听鹂馆院落,对比两组建筑内中轴线位置的不同。
“画中游的中轴线与南邻的听鹂馆的中轴线并不对位而略错开少许。这种‘错中’的情况并非造景的要求,可能出于风水的考虑,这在清代皇家诸园中屡见不鲜,大内宁寿宫花园就有多处‘错中’的做法。”
看着下面的听鹂馆院落,很自然地想起民国年间借住在这里的四川籍画家张大千,想起他在这里的画作,与溥儒等北平画家的交往,与日本人的周旋,最后才逃出日本人占领的北平,先到上海,后又回到老家四川。
据张大千自己说,他曾经借住在颐和园(听鹂馆)两年,也就是1937年、1938年的样子(1938年夏季离开)。再对比溥儒来颐和园的时间(1938年),两人应该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作邻居。
在民国时期的画家中,张大千是在他的兄长张善子的引领下步入上海和北京画坛的,其早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当过一年土匪,去日本学过一段染织工艺,回国后又做过不到一年的游方和尚,直到1919年正式拜清末遗老、上海文人曾农髯为师才算上了正路。
1925年当他初到北京时,画作仅卖每幅20元,后来北京画家汪慎生雇用他仿制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画作,很长一段时间,是靠作伪谋生的,但也由此练就了一手过硬的笔墨功夫。现在国内一些博物馆和私人手里的石涛与朱耷的画就是当年张氏所作。
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期,张大千的名声渐起,并与溥儒和北平画坛有了密切交往。加之琉璃厂的画商和报人的宣传,则有了“南张北溥”之说。
在颐和园居住期间,张大千带着他的三太太杨婉君和大风堂的弟子数人住在听鹂馆中。这时期留存下来的作品以古典山水画和大写意荷花为多。
天津博物馆就收藏着张大千题有“昆明湖上听鹂馆”的一件设色山水——《仿石溪雁山三折瀑图轴》。画面上云烟缭绕,有山深林密之感;盖在画面右下角的朱文印更是有趣——“山水姻缘等于婚媾”。很能表现张大千的风流倜傥。
另外收藏在该馆的、画于1935年的大幅青绿山水人物图轴题有“蜀人张爰大千时客故都”,但这时张氏应该还未到颐和园居住。
张大千一生画荷花甚多,早期以写意荷花为主,上世纪40年代初期,去敦煌临摹壁画以后,又画过一些工笔重彩的荷花,晚年患眼疾,只得又画写意荷花了。
在晚年,张大千曾在向他的弟子叙述写生的重要性时谈及颐和园,回忆起那一段对景写生的美好时光:
为了画好荷花,我曾赁居北平颐和园两年多,每天的早、中、晚三次,我都要去到荷花池畔,细心观赏,并旁及到其他的龟、鱼、虫、鸟、杂草等物,还下苦工对荷花写生,所以我能够对荷花的各种生态,烂醉于心。这样画起荷花来,就能够随意挥毫,无不毕肖而成趣了。
在我眼力好时,大幅荷干都是两笔完成:一笔从上至下,另一笔从下至上,两笔自然接榫。现在画一笔荷干,要跑几步方能完成,而每一次走动,心脏便剧烈作痛。所以每画一干,必须先含一粒舌片。
直至晚年,在台北外双溪的摩耶精舍,张大千还在院子里养了数缸荷花;这些亭亭玉立的荷花既是画家的画本,也带着画家对故土的思念。
据当时溥儒带的女学生回忆,她曾随着老师到听鹂馆中做客,看张大千画写意荷花,当时的感觉是“气势大,格调高”,对一般人而言,临习并不容易。那时的溥、张两位画家应该是时相往来,在一起研讨诗文、合作书画的。
(摘自《颐和园测绘笔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2月版,定价:6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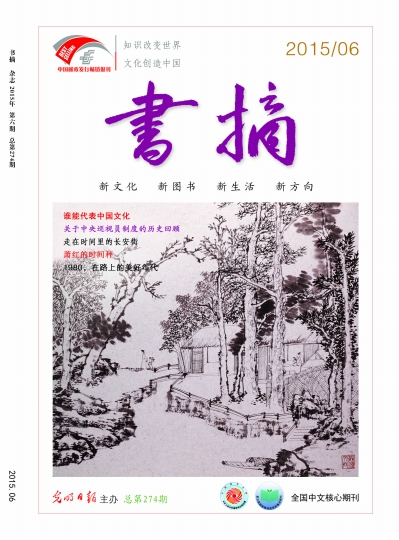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