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1923年至2013年)教授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特别是他对当下中国的走向,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出路的思考,不仅远未过时,有些至今仍不失为有效的镇静剂、解毒剂。
中国“乡巴佬”
1923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即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父母均出生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竹内出生的镇上,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家,可并不是像大城市那样单独辟出一块日人屯驻地,而是与中国人杂居。
竹内的父亲,早年曾救过一位被土匪绑票的地主的命(土匪虽然厉害,却不大敢惹日本人)。地主出于感恩,贷了一块地给东洋恩人。用这块地,竹内夫妇建了几间屋,经营了一爿和式旅馆。一位中国厨师,会烹制全套的日本料理,生鱼片、烤鱼、烧蛋等,都很地道。附近的日本人,若想吃正宗日料的话,只此一家。“他们在旅馆可以住宿、吃饭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有一种回到‘内地’的感觉。”(战前,在国外的日本人称日本本土为“内地”,而海外为“外地”)
竹内实五岁失怙。母亲隐忍而有远见,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常帮助中国苦力。旅馆的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后来回忆说:“母亲告诉我说:‘土匪头子住在这儿,看看罢。’”这种童年期的现场体验,对日后成为汉学家的竹内实来说,是一种接合中国民间社会的“地气”。
竹内在中国读的是日本人学校。虽然镇上只有二十来户,满打满算四五十个日本人,但却有一间日本小学校,“从日本来的校长和他的夫人,在一间教室里教着两三个班级的学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科书也是日本文部省编写的国定教材”。包括漂流海外的适龄学子,“一个都不能少”——日本对基础教育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可竹内的母亲并不满足于此,“母亲的想法是,小时候学一门什么技术,将来总会有些用处”。因此,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
十一岁时,举家迁至“满洲国”的新京(即今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中等教育,于1942年(昭和17年)回国。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十九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30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祖国的陌生人
竹内实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走上汉学之路,恩师是一代宗师仓石武四郎。竹内一路追随仓石,从京都大学到东京大学,出学部,入大学院,直到毕业后进入中国研究所。
东大时代发生的一件事,给竹内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1946年,中国作家谢冰心随夫君、中国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社会学者吴文藻访日。因战时,仓石曾把冰心的一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出版,故带竹内一起去作家夫妇落脚的公寓登门拜访,并邀请她来东大讲学。冰心讲课时,便由竹内口译。开讲之前,冰心问了竹内一个什么问题,竹内说自己是边打零工,边读书。冰心听后,介绍了一位想学日语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多年后,竹内回忆起来仍心怀感激:“那位成员给的讲课费可真不少!我能把大学院坚持读下来是托谢先生的福。”随后,就听说吴文藻先生辞去了代表团的职务,准备回大陆。“当然对我们并没有那样说,而是以得到了美国大学邀请的名目,离日赴港,从香港却不转美国,而是去了北京。据说在中国本土受到热烈欢迎,皆大欢喜。这个行动给我们以很大的影响。”从此,在历史性拐点上,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成了竹内观察、思考中国问题时的一条主线。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竹内实作为译员和友好人士曾数度访华,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殊荣。客观上,也使他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的细部,体会到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偏差,赋予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某种临场感,同时也看到了某些日本左派人士意识形态先行的不靠谱。
1960年6月,竹内实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团员中还有开高健、大江健三郎等名作家,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的接见是一个契机。竹内实后来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泽东专家,著有三种毛的传记,是毛语录和毛诗词的权威翻译、阐释者。
与此同时,竹内的学术触角开始向四周延伸,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鲁迅研究、邓小平研究、中日关系史等,视野所及,几乎涵盖了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且均有相当深度的开掘。
作为日本顶尖的毛泽东研究权威,竹内始终享有访中的“特惠”,甚至在邻国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少数几个可以徜徉北京街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因此,他远比一般汉学者掌握更多的一手信息,这也许是他免于盲目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对“文革”持怀疑态度:
1960年我访问中国时,曾会见过赵树理和老舍,听说这些人在中国都受到了批判,我觉得这种批判与人的信义是相悖的。而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却有人在以前被其赞扬的刘少奇受到批判时,竟也反过来恶意地谩骂他。
我并非对刘少奇的过去全都肯定,但很讨厌那些如此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便决心不再对刘少奇说坏话。自己曾经在一个讨论会上发言说:“比起日本的革命家来,中国的反革命要更好一些。”
1968年,竹内以《诉诸毛泽东》的著名长文,肯定毛在“终结近代中国屈辱历史”上的功绩的同时,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国家荒废,不啻空谷足音。但在“左”“右”标签满天飞的时代,竹内却感到一种被两头夹击、动辄得咎的尴尬。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几年以前,我已经与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疏远”。作为从中国山东省张店“冒出来”、跻身精英学界的“乡巴佬”,竹内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劣等感,越到后来,越发觉得自己的“不合时宜”,有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不折不扣的“祖国的陌生人”。
“友好易,理解难”
作为终生视中国为“第一故乡”,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汉学家,竹内实无疑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可吊诡的是,就在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的翌日(1972年9月30日),竹内却在公明党的机关刊物《公明新闻》上发表评论,谈“今后的日中关系”,明言“应该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
竹内深知,1972年的建交,实际上是两国政治家共同推动的、一种基于国家战略的政治和解方案的实现,并非是基于两国国民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日本民众其实对中国并非多么感兴趣,毋宁说态度倒有些冷淡。这就是事实”。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与作为“国家”的中国进行交往,并非是自今日才开始的。
日本与清朝或中华民国,都曾有过外交关系。然而,正如历史告诉人们的,在清朝,日本曾在其领土上与俄罗斯打过仗;到了中华民国时代,又扶植过“满洲国”、冀东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并未尊重过对方的主权。
从今以后,则似乎要重新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打交道了。
那么,我们当真准备妥当了么?遗憾的是,并非如此。
竹内指出一味高喊“友好”,未必就能实现“友好”的目标,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在竹内看来,所谓“友好”定位,起初就有问题:
比如我觉得,一开始应该先有日中协会;接着,应该是日中理解协会;最后,才应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协会的会员可以多一些,而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少一点则无妨。至于“友好”是否会世世代代传下去,那是很难回答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以时论的尺度衡量,竹内不只是“不合时宜”的问题,简直就是“乌鸦嘴”了。可他却我行我素,自有一番坚守:“对于民间的活动,政党并不应该进行干预。”中日民间交流理应回归“正道”,那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要知道,竹内形成这一番思考的时候,正值中日关系“蜜月”期,“日中友好”几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断有政治反对势力出台“搅局”,但“搅局”的结果,却反而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势下,竹内敏锐地察觉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本身即是一种僵化,也未尝不是中日关系大起大落、骤冷骤热,动辄“打摆子”的初期症状(诸如宝钢事件、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首相的靖国参拜、光华寮事件,等等)的病因之一。于是,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前瞻性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瓶颈,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甚至曾建议以平假名书写的“喜欢”,来逐步取代用汉字书写的“友好”。
在奠定中日关系基础的基本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后的1978年10月,竹内在《中央公论》杂志撰文指出: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则应该加深“理解”,才能“友好”发展,即所谓“关系—理解—友好”。当时,由于日本无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是赞成两国首先恢复邦交,建立关系的。但是从前几年开始,我觉得这种关系似乎被颠倒了。滥竽充数以求加深“友好”,或徒具形式的代表团接触之类,这些并无意义的举动和结果表明,按“友好—理解—关系”这种颠倒的顺序,并想加强“关系”,是难以奏效的。
日中邦交恢复后友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双方当然都是有利的。但是,决不应该放松对“理解”这一中间环节的努力。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友好”诉求先行,而“理解”滞后、发育不良的状况,确确实实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竹内不仅看到了问题之所在,而且提出了解决方案,力主展开“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研究,以期两国关系能最大限度地“去政治化”,以相对客观化的、正常的“体温”落地。只有如此,才可望生根。竹内版超越“友好”的中日关系论确实不失为醒脑的清凉剂。
(摘自《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3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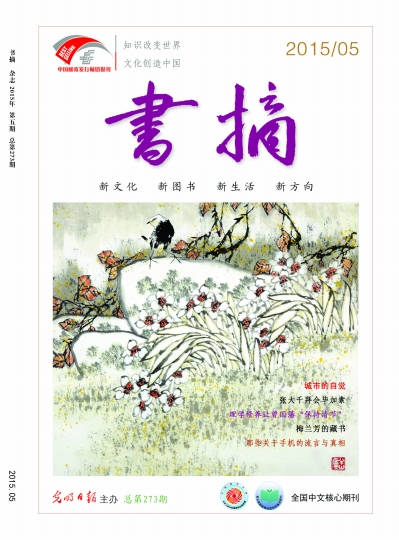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