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晚,北京落着小雨。我接到苗子、郁风夫妇打来的电话,告诉我祖光于午间辞世。他俩的语调低沉而平静,我也不太感到突然。因为一个真正的祖光,一个谈笑风生、睿智灵敏的祖光,早在五年前那个令人伤心的江南春雨的四月,已经跟随他深爱着的凤霞远远地离去了。
这五年的岁月,他独自默默地坐着,不再说一句话。朋友们去看望他,心里都很难过,只能拉着他的手,默默地相望着,用心灵和他对话。也不知他感受到了没有。
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人们通常只把它看成一个大文化人和一个民间艺人的奇妙相遇或一个新文艺工作者和一个旧艺人的美好结合。如果从人性的纯美和心灵的相通来看他俩的爱情,简直要认为这个美丽的婚姻真是上帝的一篇杰作。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五十年。他的名字对我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在我的心里,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
吴祖光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不但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而且闪耀着动人的人性光彩。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关于他,我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他逝世后许多往事涌上我的心头,他的精神生命永远不会离我而去。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在大人物面前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他也从不以大人物自居。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上世纪50年代初,我和他交往时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而他那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必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做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大吃一惊,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有警卫陪着,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哩。”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又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的事,还讲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我们三个都不是党员,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做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邀请。
1953年祖光编了一本散文集《艺术的花朵》准备出版,那里收集了他写的十多篇描述梅兰芳、程砚秋、常香玉、新凤霞等戏曲表演家的极富情趣的散文,每一篇都附有一幅很精美的插图,大都出自名画家手笔,如张光宇、丁聪、郁风等,但是祖光特意把写梅兰芳的那一篇留给蔡亮,要他画一幅梅先生《贵妃醉酒》的舞台速写。蔡亮那年刚满二十岁,还是美院的学生,祖光信任和扶植无名青年,没有半点论资排辈的俗见。《艺术的花朵》出版后,我们都为蔡亮高兴,这是他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从吴祖光身上感受到了中国文化人对后进者的一片爱心。三十多年后,蔡亮已成了一位名画家,他回忆起这件事时深情地对我说:祖光的用心到我当了教授后才真正领略到,他是给我一个机会,要我向那几位名家学习,看看自己和他们的差距在哪里,鼓励我上进。我想起他对我的培育,就懂得了我应该怎样爱护自己的学生。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于直言。我接触吴祖光是1952年从朝鲜前线回国以后,他那时住在东单栖凤楼,离我住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氛的小院子,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富吸引力。吴祖光是一位有很高艺术成就的剧作家,当我幼年时在剧团里做小演员时,他已是戏剧界著名的“神童作家”了。他的剧作《风雪夜归人》《嫦娥奔月》《捉鬼传》等,都是我喜爱的作品。除了他的学识,成就和智慧以外,他为人仁爱宽厚,同情别人的疾苦,而他的谈吐又那么活泼风趣,所以在他家做客特别愉快而不感到拘束。他的美丽而又善良的夫人新凤霞对我们也很有吸引力,他们那时结婚不久,凤霞每天晚上都要登台演出,白天在家里练功练唱,她的琴师每天都来家,和她一起琢磨推敲新的唱段。她虽然忙,还是那么热情地款待我们这些没有成家的年轻朋友,给我们包鸡肉馅的饺子吃。我们遵照中国人的方式亲切而恭敬地叫她“大嫂”。我们喜欢去他们家,喜欢听祖光谈戏剧,听凤霞唱戏,也喜欢在他们家吃饭。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因为我和路翎在一个创作室工作,我们几个朋友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外围的“小家族”,被关起来审查批斗。“反胡风”运动本来同吴祖光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真纯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出于一种善良的心意,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公道话。他不知道这样做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点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点党内斗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躲避都来不及,吴祖光的率真就这样给他自己招来了一场大祸。
? 1957年,吴祖光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文联召开的“鸣放”会,是周扬、阳翰笙两位文联领导人亲笔写信派人来请他去的。他出门前,新凤霞劝他不要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吴祖光和黄苗子、丁聪、唐瑜等文化人被打成“二流堂右派集团”,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被定为“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股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揪上台,听任人们用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
1979年春,“小集团”平反后,我和几个朋友在祖光家重逢,凤霞已经瘫痪,我们抱在一起,是那样淋漓痛快地嚎哭起来。
1980年春,我结婚了。我的岳父在他工作单位的食堂办了两桌酒菜招待亲友。凤霞叫儿子吴欢背着她出席婚宴,她说:“别的宴会我都可以不去,杜高的婚礼我就是爬也要爬了去!”她把她自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幅《双挑》由祖光题诗“开花春灼灼,结实夏双双”赠送给我。食堂的大师傅和服务员们听说新凤霞来了,都来围住她,请她唱几句评戏。她已经很久不唱戏了,但她要用自己编的词唱几句,刚刚唱完“好人遭罪,苦尽甘来”两句,便哽咽着,泪流满面,唱不下去了,只好由女儿吴霜替她唱了一支歌。这情景使在场的人们都受感动。
新凤霞也是一个奇迹般的杰出女性。一个几乎不识字的民间艺人,身残志坚,靠着自己超人的灵性和刻苦勤奋,靠着对祖光的深情笃爱,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下,居然把自己锤炼成一个作家、一个画家、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一个独一无二的典型的中国式的女才人。人们都知道,吴祖光戴着右派帽子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后,文化部一位副部长找新凤霞谈话,要她立即和吴祖光离婚,划清界限,新凤霞回答:“祖光是好人,我要学王宝钏那样,在寒窑里等他二十年!”只有中国文化才能培育出对爱情这样忠诚而又不向权势低头的坚强女性。
平反改正以后,吴祖光担任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上,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呼吁政治民主、倡导思想自由的发言。他勇为弱小者仗义执言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吃了整整二十年的大苦头而改变。到了90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商场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这就是我所说的吴祖光不改的文人禀性。他的名句“生正逢时”表明了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记得1995年8月,蔡亮突然逝世的噩耗传来,我很悲痛,跑去告诉祖光时,我哭了起来,我说:“小家族”的朋友们一个个都走了,汪明走得最早,好日子都没有看到;田庄呢,刚平反,就没了。罗坚本不该走得这么早的,谁知道他的心情是那么压抑呢;最可惜的是蔡亮,才华正茂,巴黎的蔡亮工作室还在等他回去,怎么忽然就死了呢?我没有好朋友了……祖光一把拉住我的手,眼眶里闪着泪光,对我说:“还有我呀!”
又有一次,我去看他,讲到田庄的爱人敏凡身体不好,孤身一人,生活困难。他叹了一口气,默然点点头。我起身走的时候,他把我拉住,带到他的书桌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交给我:“这一千元,是我的稿费,给敏凡送去,就当我给田庄的。”
祖光就是这样一个爱朋友、重道义、不忘旧情的中国文人。
只要回想一下已经过去了的那些噩梦般的漫长岁月,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无不在极“左”政治的沉重压力下经受着精神煎熬,无不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而唯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始终是他自己。难道这不是一个奇迹吗?
吴祖光逝世后,千万人都在悲痛,都在悼念他,赞美他,都更加认识了他的生命的价值,更加懂得了他对于我们民族的意义。因而我深信吴祖光是永生的。
写于北京安定门住所
(摘自《生命在我》,作家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36.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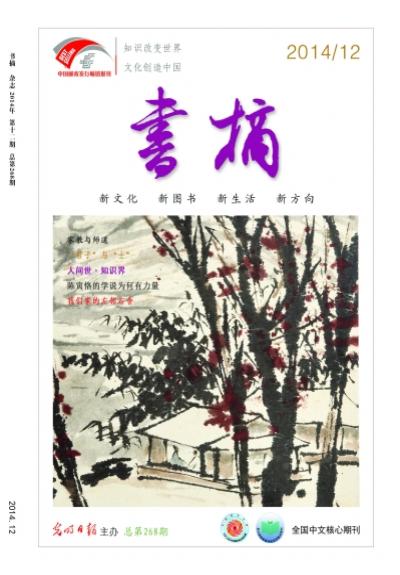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