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院儿
今年九月里的一天,坐车路过南池子,北井胡同正在一瞥间,却是已成一片瓦砾,不免心里一震。早就听说南池子一带要大拆,没想到这么快真的就拆了。
1958年从福州到北京,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在南池子北井胡同。南池子在天安门旁边,明朝的时候,这块地方大部分是内南城;清朝,为内务府所属机关。现在这里最有名的古迹,当然是明清两代保存皇家档案的皇史宬。北井胡同却是名不见经传。南池子大街偏南的一段还有个南井胡同,好像比它名气稍稍大一点,大约南井胡同里的那口井,井水是甜的,而北井胡同里的井,井水是苦的。
北井胡同窄而短,用北京话说,是条死胡同,所以胡同口的牌子上写明“此巷不通行”。南池子大街上这样的胡同不止一条,箭厂胡同、冯家胡同,都是。胡同里一共住着七家,独门独院的只有两家,其一是二号,其一是六号。二号是个两进的四合院,据说主人是资本家,当时最惹人注目的,是他的家里有一辆摩托车。三号院里住着两户,记得都是工程师。虽然不是很正规的四合院,但四面的房子齐齐整整,院子里两个花池,也总是收拾得很有样子。五号是个大杂院,住在院子里的几家,家境都不大好。其中一家的女主人,是街道居委会主任。我家住六号。小小的院子里,北屋两间,西屋两间,东边一间小板房堆杂物,南屋做厨房,旁边是一间只有一个蹲坑的小厕所,化粪池开在院子里,满了,要请掏粪工背着粪桶拿着粪勺来掏。北屋和西屋之间还有个夹屋,便是我的卧室。院子的东北角,是一棵两搂多粗的大槐树,夏秋时节,槐荫匝地,把院子遮蔽得严严实实,槐花开起来,清香缕缕。槐树霸占了几乎所有的阳光和养分,北房前边原有一方小花池,也曾种过不少花草,可细细瘦瘦总是长不旺。只好养几盆文竹、绣球、秋海棠,常年放在北屋的窗台上。
外婆16岁结婚,做了一辈子家庭妇女。公园遛早,戏园子听戏,打毛线,看小说,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中山公园(社稷坛),文化宫(太庙),是天天去的地方。文化宫的东门,就开在南池子大街,走去很方便,门票三分钱。从文化宫的西门穿出去,是午门,中山公园即在午门西,门票五分钱。公园里的唐花坞,鲜花四时不败。唐花坞外的藤萝架,春夏秋三季,都是清幽的坐处,看书,打毛线,无不合宜。藤萝架不远,便是有名的来今雨轩。来今雨轩常年卖着冬菜包和豆沙包,那是留在我童年记忆里的美食之一。
南池子离王府井不算远,但徒步来去也还不是很轻松,所以多半是回来的时候坐三轮车,记得车钱很固定的是两毛五。东安市场的北门有个清真小吃店叫丰盛公,里面卖奶油炸糕,酥脆的皮儿,绵软的芯子,再来一碗杏仁豆腐,清凉爽口。丰盛公往里,便是吉祥戏院,吉祥戏院看戏,一个月大概不少于三次。外婆喜欢的是青衣戏,悲戏,苦戏。印象深刻的一出,是《生死恨》。女主人公苦了一生,却在幸福即将到来的时候死了。整出戏,唱腔特别多,幽咽凄婉,催人泪下。每唱到精彩处,人们都要为它幽咽凄婉得好而鼓掌。每月十五号,是外公发薪水的日子,第二天一家三口必定要去吃西餐。最常去的是文化餐厅。出胡同口往南拐,走到南湾子,穿进去,出来就是南河沿。文化餐厅坐落在街西。餐厅是长方形的,宽敞,洁净,人很少。常点的菜是土豆沙拉,炸猪排,奶油鸡茸汤。
南池子在天子脚下,每年国庆节街上都要过游行队伍,穿着各式艳丽的服装。高兴的话,可以坐在胡同口,从早上看到中午。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放礼花,运气好,说不定还会有降落伞飘到院子里。虽然地处中心,有四达之便,但南池子从来是安安静静。夏日里,街道两旁的大槐树绿荫交午,总有着特别的清凉。早点摊,副食店,菜站,小酒铺,不多,却正好敷用。静悄悄的胡同,静悄悄的街道,平静而有秩序的生活,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紧贴着皇城才特有的气象。
北井胡同的第一次消失,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时候南池子大街改称葵花向阳路。胡同本来是大街中大大小小的凹曲,门牌号码,大街、胡同,各成系统,这一回都被抻直,用门牌号把大街和胡同统一起来,北井胡同六号,便成了葵花向阳路158号。
外婆是湖北黄陂人,父亲名叫金永炎,曾为黎元洪幕僚,还做过短短几天的陆军次长。短寿,47岁就死了,老家的田产分在子女名下。外婆早早嫁人,田产放弃,土改划成分,本没把她算在内,文革一起,却成了漏网地主,抄家之后,勒令返回原籍。外婆不露声色吞下安眠药,从容而去。很快,不知从哪儿迁来一户工人成分的五口之家,超负荷的小院从此再没有往日的恬静和安宁。二号院也抄了家,主人被驱逐出去,院子里一下子住进了四五户,成了大杂院。经历了文革,承载过古老文化的真正的四合院其实已经很少,胡同所包容的,几乎都是杂院,居住环境乃至生存环境都很差的大杂院和小杂院。
1994年的时候,忽然有点儿怀旧,于是到离开二十多年的北井胡同看了看,看见胡同里的房子都很破旧,窄而短的胡同越发显得可怜巴巴。在北京生活了44年,可是能够作为生活见证的,差不多都不存在了,真不知道应该黯然,还是应该欣喜。
大院儿
1979年,我从小院儿嫁到了大院儿。仍然没离开东城。
大院儿在东总布胡同。朱一新说:“总铺胡同,铺俗讹捕,或讹布。井二。有元贞观。《燕都游览志》:东院在总铺胡同东城畔,昔时歌舞地,今寥寥数家如村舍,兼之人掘土为坯,满目坑堑,从寒烟衰草中,想走马章台之盛,邈不可复寻,犹记旧游有陈家园、郝家亭子,树石楚楚,并无存矣。”这儿和南池子不过隔了三条南北向的街,就已经不是皇家气象,而可以搬演“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的艳冶故事了。不过东总布向南岔出的一条宽胡同,现在叫作贡院西街的,旧时有过举场胡同的名称,据《京城坊巷志稿》,这儿是元代礼部旧址,明永乐改为贡院,清仍之。如今,十几层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矗立在胡同口,出入于大楼的莘莘学子,多半都是“进士后”了罢。
又想那“井二”,以为到底和井有缘。谁知至今连井的遗址都没能找到。看前人的记载,北京的胡同,有井的居多;现在,可都哪儿去了呢。
大院儿大,却也还不是四合院。院子里一幢二层小楼,据说是德国人盖的,有百余年的历史了。小楼平面布局很奇特,——没见过德国人怎么居家过日子,所以始终弄不明白它的设计意图。最大的特点是门多,有一间屋子四个门的。第一次来访的客人,十个有十个出来进去找不着门。我住的房间,两面都是玻璃长窗,人说这儿原来是德国人的花房。中国人却是早没这些讲究了。
但花还是种的。大院里树多,草多,花也多。这些,自然都和德国人无关。
文化大革命以前,大院是一座美丽的花园。进大门,入二门,石子甬道通向后面的一带假山。假山前面是葡萄架、藤萝架、龙爪槐,还有一个蓄水一米的金鱼池。一棵枝干嵯桠的老杏树,年年结出又香又甜的大黄杏。文革中,大院主人十年磨难,大院也就面目全非。石子路掀了,金鱼池填了,龙爪槐、藤萝架,都成了“深挖洞”的牺牲品,——这段历史,当然都是听来的。如今,大院花木又恢复生机。没有了人工经营,倒添了几分野趣。
春天,最早见花的,是连翘。花不茂,柔条披拂,疏疏缀着一星一星的鹅黄。相跟着的,是桃花。桃花也瘦,细枝横斜,寥寥点着一朵一朵的淡粉。楼角的一丛竹子,悄悄见出绿来。它委委屈屈生在北地,要熬过一冬的寒冷,所以总是绿得不情愿。庭院深处的一株丁香,常常不知不觉就花开花落了。假山旁边,是一蓬白蔷薇;紧挨着它的,有一丛白色的太平。它的脚下,更有一大片夜来香。不开花的时候,那些油绿肥厚的叶子,也挺可爱。
楼角下一株凌霄,沿着楼房攀缘而上,把楼顶都给拱得翘起来。一个长夏,窗外满是绿荫,小长喇叭似的红花,也久开不败。只是免不了要带进来一群一群的蚂蚁。后有好事者说楼房都要被它拱破了顶,于是三下两下把这一株老干从根劈死了。
最可爱的,是棔。合欢花、马缨花,绒花,都是它。古人还有叫它朝开夜合的。最早知道合欢叫作棔,是从《红楼梦》里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凹晶馆联诗悲寂寞”:湘云以一句“庭烟敛夕棔”,就差一点难倒了才情十二分的林妹妹。不过这“庭烟敛夕棔”,也实在好,朝开夜合的棔,于此“境界全出矣”。后来在《群芳谱》上看到“合欢”一条下面的许多记载,都是挺诗意的,只是“棔”似乎不大用。大概因为合欢二字合起来上口,意思又特别美丽罢。记得小时候南河沿整整一条街上都种的是合欢树,六月发花,直开到金秋,一街的幽香,能飘到和它相邻的南池子。几年足迹不到,再过,已是“寻芳去迟”,不知是砍了还是移了,总之,一街的合欢树,已经成为童年的记忆。
大院儿里说不清来历的花啊树的,还多呢,“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对这片风景的最佳形容,已经让鲁迅先生作成了名句,我只好老老实实地说:“大院里,还有两棵枣树。”但不知它是不是也做小粉红花的梦。
只是,大院儿和大院儿里的花木,还能存在多久呢。
这担心不是没来由的,——离东总布不及一箭之遥的北牌坊胡同,已经平掉,要盖大楼了。
北牌坊原先住着人称“范老板”的老出版家范用先生。迁出旧居的前一天,我赶去告别。当日北牌坊的半条胡同都成瓦砾,老板的小院孤零零的,一面院墙已被拆掉一半了。
院子不大,也是一幢二层小楼,住了不止一家。但房子开间大,又高,加上院中花木繁盛,夏秋之际,绿荫匝地,我常和老板说,这儿有潇湘馆的清凉。
院子里,一棵国槐,一棵洋槐。一株香椿之下,生出几茎嫩枝,过几年,也就是香椿树了。靠窗两棵丁香,花已开过,留下一片绿荫,是为长夏遮阳的。夹在丁香中间的是太平,刚刚含苞。主人却等不到它开花了。主人别去,太平也就结束它的生命,——小院将夷为平地,再不见旧日风景。当然,新蓝图已经画好,该成为历史的,就让它成为历史罢,胡同,正在慢慢成为历史,不是“四合”、却也可爱的大院儿小院儿,早晚不也会成为历史么。
(摘自《棔柿楼杂稿》,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6月版,定价:30.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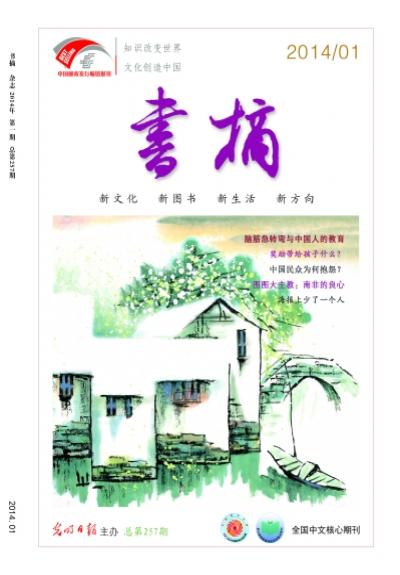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