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车的万人巴扎(集市)许多年前便在全疆闻名。每逢周五,千万辆毛驴车从远近村镇拥向老城。田地里没人了,村子里空掉了,全库车的人和物产集中到老城街道上。库车四万头毛驴,有三万头在老城巴扎上,一万头奔走在赶巴扎的路上。一辆驴车就是一个家,一个货摊子。男人坐在辕上赶车,女人、孩子、货物,全在车厢上。车挨车,车挤车,驴头碰驴头,买卖都在车上做。
我有幸一次次地走进老城巴扎。我不买什么东西,也没啥要卖的。我和那些喜欢逛巴扎的维吾尔人一样,只是逛一种闲情。看哪儿人多,热闹,就凑过去。
并不是每个人上巴扎都做生意。
每个巴扎都是一个盛大节日。
女人在巴扎上主要为了展示自己的服饰和美丽,买东西只是个小小的借口。女人买东西,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挑,从街这头到那头,穿过整个巴扎,再转回来,手里才拿着一点点东西。
年轻小伙上巴扎主要看漂亮女人。
没事干的男人,希望在巴扎上碰到一个熟人,握握手,停下来聊半天。再往前走,又遇到一个熟人,再聊半天,一天就过去了。聊高兴时说不定被拉到酒馆里,吃喝一顿。
我到巴扎上什么都看,什么声音都听,遇到新鲜事情就蹲下来仔细打问。我觉得,我比那些在巴扎上收税的戴大盖帽的税务员,更了解这些做小买卖的。一次,我看见几个税务员,从一位卖奥斯曼草的妇女手里,强收了三块钱的工商税。最后,那个妇女收拾起卖剩的几小束奥斯曼草,哭着回家去了。我不知道那个妇女的家庭情况,不知道那三块钱对她意味着什么。但我清楚,那些卖奥斯曼草的妇女,一天都挣不了三块钱。
当然,巴扎上更多的是热闹,是有意思的事情,我随便写了几件,有兴趣你就看看。
最小的生意
早晨,我走过沙依巴克街时,看见一位维吾尔妇女,面前摆着几小把奥斯曼在卖,几个年轻女人围着挑选,已经卖出去一把,收回来五毛钱。我数了数,她总共有七小把奥斯曼,全卖完能收入三块五毛钱,其中的本钱是多少我就不知道了,或许是她自己种的,或许是两三毛钱一把从别处批发的,守一天卖掉,挣一块多钱。
这还不是最小的生意。离她不远,另一位蒙面妇女,面前摆着拇指粗细的七八把香菜,一把卖两毛钱,菜叶上洒了水,绿莹莹的。看装束是城里妇女,或许从赶集的农民那里,四毛钱买来一把香菜,再分成更小的七八把,摆在街上卖。
下午我转过来时,见她面前还摆两小把香菜,叶子已经蔫了,看样子卖不掉了。街上人已经不多,她挪动着身子,像有收拾回家的意思,又抱着一点点希望,等着朝这边走来的几个人。
我大概算了算,她这笔买卖,除掉本钱,最多挣八毛钱,还赚了两小把香菜,够晚上做羊肉揪片子用了。
还有一个卖针线的小女孩,几十根不同大小的针,插在一顶小花帽上,每根针上穿一截不同颜色的线。一根针卖几分钱,一根一根地卖。
我离开巴扎时,看见那个抱了一只歪葫芦,卖一天没卖掉的老汉还坐在墙根。他看上去表情安静,目光平和地望着街上渐渐散去的人,又像望着更远处我不知道的什么地方。他的歪葫芦在夕阳下有着红色艾得兰斯绸的光泽。我知道这种老式葫芦,已经很少见了,知道它香甜味道的人也可能不多了。
明天后天,这只葫芦和这个老汉,还会出现在周边乡镇的巴扎上。下一个礼拜五,说不定他又转回来,坐在这个墙根,还抱着那只歪葫芦。
我没上前去问那只葫芦的价格。我知道不会太贵,三块两块,就买来了。
老式瓜菜
在沙依巴克街的瓜菜市场上,老式的西红柿、甜瓜、土毛桃,矮小的芹菜、萝卜,一筐一筐摆在那里。几十年前我们吃过的那些未经“改良”的瓜菜,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我看到一位农民,筐里放着几个又小又难看的甜瓜。我觉得眼熟,问名字,“克克奇”。我小时自家的菜园里就种过这种叫克克奇的小甜瓜,秧扯得不长,瓜也小小的,一棵秧上结三四个。奇甜,还有一种很浓郁的特殊香味。
那时候,在一些人家的小菜园里,总有几样别人家没有的稀罕瓜菜。都是些古老品种,靠主人一年年地传种下来。我们家的克克奇,就是母亲每年拣最甜最饱满的瓜留下种子,在窗台上晾干,来年再种,可是后来就再见不到了。我们都不知道是哪一年忘记种了。那种特殊的浓郁香甜味,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的时候,竟都没有被察觉。
库车这块土地上是否还遗留着一座人类古老的菜园子,我们喜爱的那些在别处早已绝迹的老式瓜果蔬菜全长在那里。
但我知道,那些珍贵的种子,只保存在个别一些农人手里。他们喜爱那些土瓜果,每年在自家菜园种几棵,产量不高,果实也不大,卖不了几个钱。只是自己喜欢那种味道,就一年年地种了下来。如果有一年他们忘记种了,或者,他们仅有的几颗种子叫老鼠偷吃了,一种作物便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
我们培育改良的又大又好看的瓜果长满大地。它们高产,生长期短,适合卖钱,却不适合人吃,它把人最喜爱的那些味道弄丢了。“改良”的结果是,人最终会厌恶土地,它再也长不出人爱吃的东西。
事实就是这样,我们改良成功一种物种,老品种便消失了。没有谁负责为那些老品种留下样种,到最后,我们都不知道人类最初吃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如果改良错了,路走绝了,我们从哪里重新开始。
能变成钱的东西
各种各样的吃食,冒着香味儿等候那些嘴和肚子。有钱人吃的抓饭、拌面、缸缸肉,没钱人吃的馕、羊杂碎。在以抓饭闻名的乌恰市场,我看见几个妇女卖煮熟的洋芋蛋,两毛钱一个,四毛钱、六毛钱就吃饱肚子——老城的穷人给乡下来的更穷的人们备下简单实在的廉价食物。
赶一天巴扎不能空着手空着肚子回去。
有数的两筐杏子,一麻袋青菜,价格卖好了能吃一盘素抓饭、两个烤包子,卖不好就只有啃自带的干馕子。收成是可以想到的,一年里只有几样东西变成钱:不多的几棵树上的杏子、一小畦没种好的辣子和西红柿。地里的麦子刚够自己吃,埂子上的几行苞谷,早掰掉煮青棒子吃了。屋后的白杨,长粗还得几年。几只土鸡的蛋,一个个收起来,还不够换茶叶和盐。对于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有意外的收入。不会有更多的快乐幸福,但也不会再少。县上的统计报表中,有这些贫困村庄的人均收入,少得不能再少。有没有一份报表,统计这些人的笑声。他们一年能笑多少回,今年和去年的笑声,是否一样多,哪一年人们的笑声减少了。有没有人去问问那些忧郁沉默的人,你怎么不笑,怎么好长时间听不见你的笑声了。有没有人去问那些快乐欢笑的人,你高兴什么呢,有什么高兴事让你一年四季笑个不停。
眉毛的粮食
有一种叫奥斯曼的草,维吾尔人称它为“眉毛的粮食”,据说有生眉养眉的功效。在库车农村,几乎每家房前屋后都种一些,女人们用奥斯曼的叶汁涂抹眉毛,久而久之,眉毛便像吸足了养分的庄稼一样,变得乌黑发亮。
这种“眉毛的粮食”学名叫菘蓝,株秆粉红,叶子深绿,种在庭院里既可当花欣赏,又随时随地可采叶描眉。一位妇女,只需种三五株就够一年用了,用不完的拿到巴扎去卖。扎成小束,一束卖五毛钱。城里妇女们的眉毛比乡下妇女更饥渴,她们有的在花盆里种几株,解燃眉之急,更多的要到巴扎去买。老城巴扎的奥斯曼生意经久不衰,每年都有许多妇女做这种无风险的小生意,靠别人的眉毛挣钱过日子。
冬天眉毛“吃”什么呢?维吾尔妇女在春天花红叶绿之时,便采集大量的奥斯曼鲜叶,用挤压出的叶汁拌以适当羊油,制成不腐不烂的眉膏,以备冬天之用。另一种储存方式是像烟叶一样晒干存放,但涂眉效果不如前者。
在巴扎上,还能买到一种特殊的头油,是用沙枣树的树胶制成的。据说用这种头油抹出的头发又黑又亮,还有股沙枣花的浓香。
维吾尔女子最引人注目的美是那双眼睛,而使眼睛熠熠生辉的则是那两弯令人惊异的浓黑眉毛。眉是五官最上一官,美容先美眉,维吾尔妇女似乎天生就知道这个道理。在库车小巷,常看到三两个维吾尔女人迎面走来,还看不清五官容颜时,便已被她们的浓黑眉毛吸引。待走到跟前,眉毛下又黑又深又大的眼睛、笔挺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嘴唇,那样的容貌,让人很难移开眼睛,移开了也还会再一次追望上去。
按维吾尔人的古老传说,女孩双眉间距离,决定了日后婚嫁的远近。两条眉毛隔得远的女孩子,一定会嫁到很远的地方。母亲总是希望女儿留在身旁,所以女儿一出生,母亲便用奥斯曼叶汁涂抹她的眉毛,稍大一些,女孩便学会自己用奥斯曼涂抹眉毛。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长大的女儿两弯秀眉紧紧相连,嫁去的地方喊一声就能听见。
如今,这种眉毛的粮食已被制成眉笔、眉膏,价格很贵。库车老城的女人们,仍旧喜欢用新鲜奥斯曼的叶汁涂抹眉毛。那些自然的东西,机器一加工便变质了。
(摘自《在新疆》,浙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定价:42.8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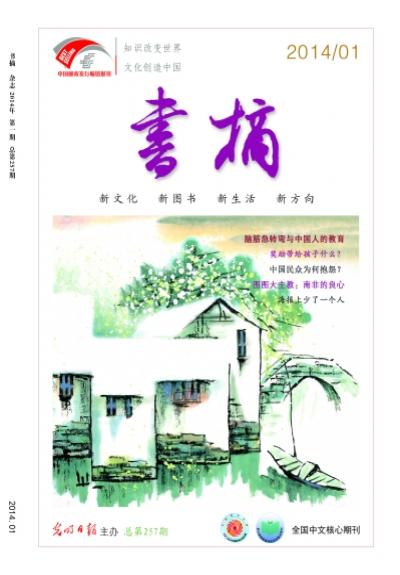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