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有点白发宫女说开宝遗事的意味。写出来,是希望给后来的人,提供一点往昔岁月的参考资料。
一位80后青年看罢此文给出两句评语,一句是,“那个年代未免有点恐怖”, 另一句是,“你们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青少年时期简直就是一群傻帽”。
右 派
——一个被拴在树上受辱的人
是1966年或1967年的事。在我们小学校操场边的槐树上拴着一个人,绳子一头拴在树上,另一头拴在那人反剪到背后的两只手上。
操场边围着一大群人,多是十二三岁的学生,中间也有几个大人。大人在那里呵斥着被捆缚的人“老实交代反党罪行”一类指令,孩子们则向那被捆住的人掷石块、吐唾沫。
被捆着的人像头牲口似地闪避着。他浑身污秽,脸上有陈旧的血痂和新鲜的血痕,眼里充满了哀哀无告的痛苦和凄楚。
我至今不明白,乡亲们为什么把定做右派的人叫做“打成”右派(把反革命分子也称作“打成”反革命)?在那时的斗争会上,对地主、富农一般都称做“斗”,斗地主,斗富农。而对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则称做“打”,即打右派、打反革命。事实上,地主、富农、右派、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统称地富反坏右)在斗争会上都是要挨打的,为什么在称谓上却不同呢?“斗”与“打”,内中应该是有历史演进成分的。
我的那位叔辈,算是我童年“亲眼目睹”的唯一右派。后来听说摘帽了,平反了。据说平反之后成了家,自家开了个小店,日子过得还行。
“万岁”与“打倒”
——一位喊错了口号的老师
万岁与打倒,怕是“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
“打倒”的面很宽,上至中央的刘少奇,下至生产小队长。“万岁”则是专用,多为“毛主席万岁”。我在1974年底参军之后,军营里士兵发言最流行的话便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会认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可见“万岁”一词,对一代人濡染之深。
教过我的一位姓罗的小学老师(他小时生牛痘留下一脸痘疤,俗称“麻子”,乡亲们当面叫他罗老师,背后叫他罗麻子),管学生很厉害,吼一声会吓得我们小老鼠一样不敢吱声。“文革”初起时他是造反的积极分子,据说是他第一个在批斗会上扇了校长的耳光。就是这样一位威风八面的人物,在参加县城里的一个什么辩论会上,领头呼喊口号,一激动把“打倒刘少奇”吼为“打倒毛主席”,全场震惊,立即就上来一群人把他打翻在地,作为现行反革命监禁看管。大约半年之后这位老师再回学校时,神情萎顿得像换了一个人。
1978年之后的中国开始重视经济建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人的思想也逐步从个人迷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走上实事求是的轨道。回首往事,赞叹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个人认为小平的首功,是让中国人告别了“万岁”,抛弃了“打倒”。
工 分
工分这个名词的含义,现在的青年怕是不知道了,然而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前,中国农民的劳动计酬是以工分形式实行的。
我所在的生产小队,一个男劳动力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一整天计10分;如果承担犁田、挑粪一类重体力劳动,则可计到12分。一个女劳动力,如果从事的是和男劳力一样的工作,可与男性记同等分,若从事工作较轻,一般情况是一天记8分。而十三四岁的儿童算半劳动力,劳动一天可得4~6分。那时,一个劳动日(10分)一般值两三角钱,高的可达七八角,低的只值七八分钱,当时形象的比喻是不够买一盒经济牌香烟,这种香烟一角钱一盒。
变 天
——个敏感的天气词语
我家邻居是个中农成分,或许是土改时家有几亩薄田。中农在那时是团结对象,不是依靠对象。而我家是贫农,在我幼小的心里是很有优越感也很有警惕性的。邻居老太太夏天在院子里晒柴火或衣服,常常看看天空说“怕是要变天呢”,我听见便很惊骇,觉得老太太说“变天”这个话,太大胆了。那时脑子里也不知怎么就装了一个“变天就是要改朝换代”的印象,因此每当两家发生口角时,我都产生过要揭发邻居老太太说“要变天了”的念头,但大概还是觉得邻居老太太并没有什么“变天”行为,说“变天”也仅仅是指天气,终于没有向队里的造反派揭发。但“变天”这个词却印象很深。现在爱人回家说“要变天了,把外面晒的衣服收回来”,我总会开玩笑说:“你说要‘变天’了?当心打你一个‘反革命’!”
无名英雄
——一次兴奋而没有效果的劳动
记不清具体年代了,反正是“文革”期间的事,有一段时间生产队里突然流行过一阵“无名英雄”的风气。最初是生产小队长在社员会上介绍了邻近第三生产小队(我所在的是第一生产小队)的群众觉悟很高,晚上不睡觉把集体的旱田都翻挖了。我的故乡属川北浅丘陵地貌,稻田分为两种,一种是成年蓄水的,叫成水田;一种是麦收后再蓄上水插稻秧的,叫旱田。旱田一般在稻子基本成熟时把水放掉,稻子收割后,因泥土板结,生产队的耕牛又瘦弱无力,多靠人力用锄头一块块地翻挖并琢碎,再种下一季麦。挖旱田是一件很费力的活儿,而三小队的旱田居然被社员们不要工分黑夜里自觉做了,这思想境界——还能不是无名英雄吗?
队长第一天晚上提示之后,第二天就发现队里也有一块旱田被人挖了。看到那块被人夜间翻挖的旱田,社员们纷纷猜测惊叹:我们队也出无名英雄了!当天晚上队长又组织社员大会,表扬了挖旱田的,说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块田是谁挖的,还不知道该把工分记给谁,但这说明我们队里也有了无名英雄!第三天夜里,队里又有几块旱田被挖,有社员私下也有议论说,昨天晚上谁谁谁看见谁谁谁下地了。晚上队长再次组织会议,说昨天晚上生产队里又涌现了一批无名英雄,还说这天晚上他没有睡觉出去观察,已经知道了一批无名英雄的名字,考虑到这些同志不愿意公开姓名,他只好替这些无名英雄保密。第四天,我和母亲坐不住了(父亲在相邻公社农具厂上班),下午出去看好了一块约半亩尚未开挖的旱田,天黑后便一人提把锄头去挖,整整挖到天快亮时才挖完,而且去挖田的过程中也没有见到其他人。次日发现新增加的被无名英雄翻挖的旱田也就那一块,队长也再没有表扬提及,此后也就再没有出现夜间挖旱田的无名英雄,好在剩下的旱田没过两天也就安排挖完了。
我那时十六七岁,而我母亲是快四十岁的农村妇女,居然能被这种“无名英雄”的气氛激发调动起来,可见“左”这个东西,能量够大的。
(摘自《温故·二十六》,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7月版,定价:29.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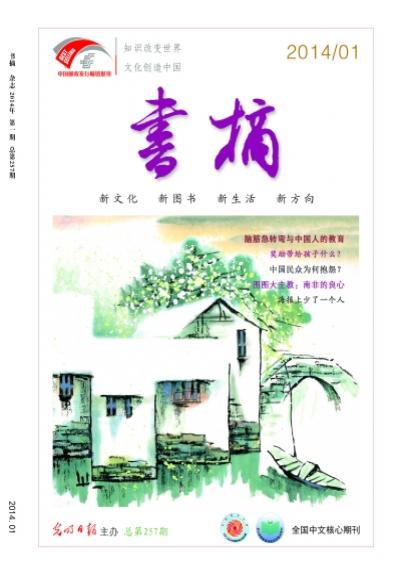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