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父亲俞平伯应聘到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授。那时我家住在北京东城,父亲去清华教课就要至青年会乘学校的班车,很不方便,就带着我们于1930年秋迁至清华南院七号宿舍。清华南院是由十几所小住宅围成的,中间空地是个网球场,环境很清静,和城内的四合院房屋大不相同。当时我只八岁,它给我的印象很深。
初至清华园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我的学校名“成志小学”,是清华大学为学校教职员的子女设立的。学校就在清华园内。小学校很小,学生也不过约二三十人,所以学校就将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和五、六年级分成三个班,每位老师同时教两个年级。这办法也很不错,因学校学生少,所以不论是哪个年级的学生,互相都认识,也较熟悉。当初上过成志小学的同学,现在有不少已成为世界上的知名学者了,也许就是因此,成志小学虽已没有学生了,但校舍仍保持原貌。
我上小学年代是1930-1934年,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了,许多往事已经无法回忆,可是却有一些小事至今仍记忆犹新。儿时往事本来就值得回忆,清华校园的童年往事更令人珍惜。
我每天上学都要先经过一条小河,河并不大,但终年流水潺潺,每当春天,河岸杨柳发芽,景色很好,我那时不会写诗,而父亲却曾写有一诗,题名《清华早春》,诗云:
余寒疏雪杏花丛,三月燕郊尚有风。
随意明眸芳草绿,春痕一点小桥东。
这首诗就是描写南院门前小河的景色。
经过小桥,就是清华园大门了,再西行不远就是成志小学。记得我上小学时,功课只是平平,到了六年级将毕业时,我们班上只有两人,我名列第二,这真是和世间流传的小笑话雷同了。
上图画课,有一次老师出的画题是一首唐诗“松下问童子……”那时我哪里能画这样意境深远的画呢!见题后茫然不知所措,可是真有同学按诗意就画出一张很好的画来,不知为何,此事我记得很清楚。
在班上,有一次老师让我上台讲故事,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上向大家讲,心里非常紧张。那天父亲也来听,他在日记中有一小段记载:“上午有课,下午至成志小学看润民讲故事,神气尚好,只是说得太快。”可见我当时紧张的情态。
小学的毕业典礼,大家要唱歌送别。这首歌词和曲调,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其歌词是:“榴红吐艳,柳碧垂丝,现诸君毕业正当时,看那些花儿草儿,也为人伤心别离……”歌子委婉动听,至今难忘。这样就结束了我的小学生活。
清华大学只附设小学,没有初中,所以我就在燕大附属初中上学,由清华园来此上学的还有熊秉明,我们一同在初中同学三年,每天骑自行车同路往返。下学后,主要活动仍是在清华园内。自日本侵入我国东北三省、九一八事变以后,清华大学抗日气氛很浓,在大礼堂时常有抗日话剧演出。我最爱看曹禺先生(他当时是清华的学生,名万家宝)演的话剧,至今仍留有印象。
我父亲那时也是充满爱国忧国之心,他说:“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他还写了一篇《贡献给今日的青年》刊登在《中学生》第二十一期。他号召青年要“信自己的力量;信中国是可救,是应救的;信我们是可以救中国,我们是应当救中国的”。
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时,讲授《清真词》和“词”习作课,此外还讲授小说和戏曲。他认为词、曲有相同之处,它们都是乐府的支流,与昆曲也有联系,所以他就联合一些同好者,研究昆曲。参加者很多都是清华名人,如朱自清先生夫妇、浦江清先生、汪健君先生和谭季龙先生等。也有清华中文系学生华粹深等多人。后渐渐就组成了曲社,因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华北势力很大,他们就将曲社定名“谷音社”。是取“空谷足音”之意,也是针对当时的时局而言。“谷音社”社员由原来十余人发展到三十多人,还在清华工字厅举行过几次曲集。在清华校园中也有一定的影响。
父亲住在清华南院时和陈寅恪、朱自清、浦江清、杨振声等教授经常来往。朱自清先生曾住在南院的单身宿舍,距我家很近,因系单身一人,饭食不方便,父亲就请朱自清先生每天来我家共餐,朱先生一定要付伙食费,父亲当然不肯收,朱自清先生一定要付,最后只好收下,而暗中却又把这钱全部用在给朱先生添加伙食上。朱先生后来渐渐地察觉了丰盛的饭菜是专门为他做的。饭费本是一件小事,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是抗战以后,父亲因亲老而留在北京,他坚不与日伪政权合作,高风亮节为世人所重。朱自清先生自昆明寄《怀平伯》三首七律,是很有名的,久为人传诵。其中第二首有句云:“西郭移居邻有德,南国共食水相忘。”就是说在南院与我家共饭的事。
第三首有句云“庭空三径掩莓苔”和“引领朔风知劲草”,都是对我父亲的鼓励和关怀。
1935年清华大学在南院宿舍之南,新建了一片宿舍,称之为新南院。房屋较好,屋前都有一大片空地,用矮松树围起。我家也就迁至新南院四号。母亲喜爱园艺,她在门前种了玫瑰和月季花,前面空地就种了一大片花生。后院则种了草莓。还未等太熟我就常去摘食。那时我正读初中,闲暇之时,常骑自行车在清华园内各处游玩。我喜欢清华园的幽雅宁静。
1936年,我国首次参加奥运会,由清华大学马约翰教授任主教练。集训队就设在清华大学。在操场上常常有运动员练习,我有空闲就要去观看。记得撑竿跳名将姓符,只有他一人在柏林奥运会上得到决赛权,虽然未能进入前三名,但也算是为国增光了,因为这是我国参加奥运会的开始。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占领北京,清华大学南迁。以后抗战胜利,清华大学又迁回来。但我也没有机会再去。直至1950年,那时我已大学毕业在天津工作,新婚后,偕妻陈煦回北京省亲,同去清华园访旧。行至清华园大门,门卫老校工还认识我,看见我,他就说:“你不是俞大头吗?”童年时的外号为新婚之妻所知,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是,确又使我感到非常亲切,似乎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我们还一同去看成志小学,虽然已无学生,但校舍仍在,连外观都没有改变,“成志小学”四个字仍然在门上。我给陈煦讲一些往事。小学旁的小土山是我昔年常去玩耍的地方。我们又去看南院和新南院旧居。可惜经过日本人八年的占领,已不是当年的气氛了。
我在清华园内共住七年,时间不算长,但童年往事至今仍留下美好印象。
(摘自《永远的清华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48.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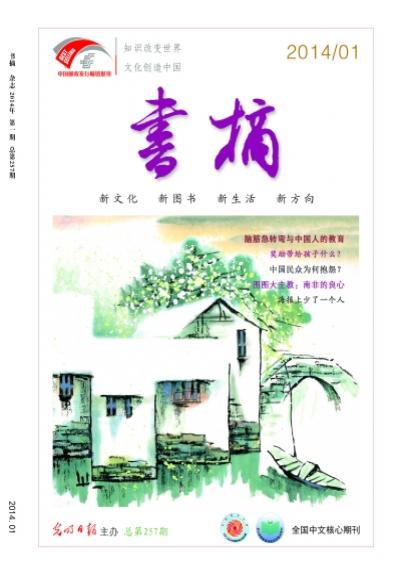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