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年前的一个“秋”日——1979年10月14日,在巴金的家,发生了下面这场今天读来仍能与老人有心灵上共鸣的对谈。但人已离去,一个萨特和西蒙·德·波伏娃来过的“家”已成为纪念馆,人们聚在这里却还能感受到“春”。
反封建的任务还多得很!
李黎:也还在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沉思》?
巴金:这一次是预备出全集,一共大约一百五十万字。我在“靠边”的时候读这部书有更多感触,“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很像尼古拉一世搞的。现在感觉反封建的任务还多得很,还远远没有完成。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里还有很多封建的东西。
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有一个完备的官僚主义的作风和机构;赫尔岑的书就是攻击俄罗斯那时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官僚阶层,公文旅行,时间花在公文里。我们现在什么事都要静候批示——任何大小事物;时间上都很浪费。这是与现代化冲突的,一定要打破。
作家有权改自己的作品
巴金:……现在外国有人说我修改自己的文章,是“迎合潮流”,我说我不是的,我从拿起笔来就改我自己的文章,每印一次就改一次,不断地改,每次发现缺点就改。我说文章又不是考卷,你可以根据我的初版来评论我的思想变化;但我的作品是要与读者见面的,我愿意以最好的形式出现。所以我说作家有权改他自己的作品。
我的思想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对我也是个很大的启示;我自己也算经过一次锻炼、一次考验——生死关头的考验。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人经得起生死关头的考验的。我算是经过了这个。所以我现在也没有什么顾忌,写东西也不为名也不为利,就是为把我的感情留下来献给人民。
“文革”还会再来吗?
李黎:所谓“生死关头的考验”,很多人是没有通过的,不是他们不够坚强,而是考验太严酷了。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却仍然有这样的力量与信心。
巴金:这是为了祖国和人民。从小我就觉得中国人受尽苦难、受尽欺凌,心里有股气,觉得中国人不应该这样子,所以解放后中国站起来,我感到很高兴。我把笔换了,来歌颂新社会,结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事,才对社会、对环境认识得比较清楚。所以我要把这点写出来,对祖国、对人民有所贡献,使将来不会再走这条路。
李黎:在国内我问不少人:像“文革”这样的事会再来吗?大家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会。”
巴金:我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我也清楚了,要是再来也是很容易的,但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责任使它不要来。我到国外访问时有种过去没有的、特别强的感觉:中国人无论怎样都摆脱不了——尤其出了国——跟祖国的关系。每个人都要用全力把国家搞好,每个人都有责任。在国外有些人觉得国内有很多缺点,我说缺点是有,要老老实实对付现实,但国家好坏每个人都要负责,不能等别人。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来不来,要使它不来,每个人就要负责,使它不再发生。要是每个中国人都这样,就不会发生。我对民主问题也是这样子想:民主不是恩赐的,是自己有责任去争取民主才有。你肯讲话,才会让你讲话,你不敢讲话呢,……我们过去是封建社会太久了,一切是长官意志,你自己不讲嘛,听长官意志嘛,长官当然就“我说了算”了。
作家要对后代负责啊!应该不怕。不怕就没有事情了。现在主要是每个人都怕,当然“凡是派”就出来了。
李黎:上世纪30年代一些伟大的作品,像您的、像茅盾先生和其他人的,都是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一到解放之后,你们这样的作品就没有了。好像一条线之后就一切都好,只能歌颂了?
巴金:(“嗨嗨”地笑了几声)文艺要繁荣,第一是要多,然后是要好。我常说我们从茅盾起,后来都没有写作品,他主要是文化部长,忙啦。我们这辈的老作家都没有写——都想换支笔来写一写,有些想改造好了再写。我觉得知识分子的改造是通过作品在实践中改造。……所以,我觉得应该总结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的希望还是“繁荣”。我的意思觉得宽是可以宽一点,只要歌颂新社会。
应该让作家写他自己擅长的东西
李黎:中国的文学传统,从《诗经》开始,就是有并行的“美”与“刺”——歌颂与批评,都是很重要的。现在是不是该开始一种比较灵活的观念去解释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
巴金:我主张应该让作家写他自己擅长的东西,譬如像茹志鹃这样很有才能的女作家,她有两本短篇小说集《高高的白杨树》和《静静的产院》,善于从小事反映大事,从一个人的普通生活反映出新社会的幸福生活。但她就不断受到批评,说她是写“家务事、儿女情”、不写英雄人物。我觉得可以提倡一部分人写,但多数人不一定要写英雄人物;我们主要还是平凡人多些,英雄少。有些人说——我也这样说过——要树立榜样呀,大家学习的榜样呀。事实上读者不是这样的,不是读一本书就可以来学的,所以要写英雄人物就跟一般读者距离很远。他们学不上的。写一些平凡人物,像上世纪50年代写一些中国社会风气,一般人民的思想、青年人思想,这是很好的。
并不一定要“做官”才方便“体验生活”
李黎:我前几天见到丁玲先生的时候,她说作家要是不“做官”,收入少不说,想去什么地方“体验生活”也不可能,所以虽然做官会占去你许多写作时间,但比较起来做官对写作还是有方便。
巴金:(笑)做官嘛,就是方便一点。至于“体验生活”是没有办法的,倒并不一定要做官才方便体验生活。我主张作家不该脱离生活。脱离了生活再去体验生活就差一层了。“体验生活”是有很多困难的。生活得我自己选择,不能由机关或作家协会替我选择。
我们有人可以不写作品也照样做作家!
巴金:我有一种说法——有人不赞成——就是我们有人可以不写作品,但可以成为作家,可以生活。我们养起一个专业作家,他可以不写作品也照样做作家,报上常见面,这里也有活动那里也有活动,几年不写作品。但是日本作家要不写作品就生活不了。现在我见到茹志鹃就讲:我在她这年纪,二十年里就写几十部作品,她就是两本短篇。就是有种种限制,限制着她、不让她发展。所以我主张以后应该宽一点,只要一个大目标,不反对社会主义、不反对我们国家、不反党。现在有刑法了,违背刑法依法起诉,不违背刑法,宪法上讲的有从事文艺创作活动的自由,宪法上是保证这个自由的。作品写得不好,写篇文章批评就算了,不是犯罪。古今中外文章写得不好也没犯过罪,是不是?
有人问是不是也要有部“文艺法”,我说有刑法了,用不着了嘛。
李黎:如果没有“法治”的观念,有什么法也不管用。“四人帮”的时候有宪法,还不是要践踏就践踏。
巴金:中国再不搞法治就危险得很,四个现代化就永远搞不了。其实守法是很简单的事情,应该一切照法办事情嘛。
不要养作家,应该尊重作家
李黎:想听听您对新一辈年轻作家的看法。
巴金:中国今天的文坛很不错,今天许多年轻人发表的作品都不错,比我们初出来的那个时候都要好。作家协会,只要有什么事提醒他一下,让他发展去。我总是说不要养作家、不要设专业作家,宁可有稿费高一点的业余作家,给他种种方便。作家总得要写作。我们现在作家不写作。这个问题我吵了好多年。还有一个是“跟得紧”的问题。以前30年代的作品现在都编了文集,丢掉得很少。但我现在很多作品稿子写好就不能用了:我写一篇文章记在朝鲜会见彭德怀司令员,当时打电报到处发表,后来彭德怀“有问题”,这篇文章就从我的集子里抽掉了,现在彭德怀平反了,文章又见天日。所以文章越跟得紧,毛病就有了。
对作家应该尊重——不必养起来,但稍为重视他一点,不必像使用一般干部那样子,高兴时捧几句,不高兴骂一通。有时把文学的作品说得一钱不值,作家也是,有时候一部作品不得了,影响好大!
真正写作的人,都是从生活出发的
李黎:我想请教您一个所谓“典型”的问题。现在常说:这个不够典型;好像非得真要有多少个姓甚名谁的这样的人在面前才叫典型,否则便是制造低级趣味或者别有用心。
巴金:这个,我们现在有,过去也有,就是对每一个人物都说不典型。我说这个没关系,比如要有人写个作家是坏人,我也不会说“这不典型”而提出抗议。说典型,有许多理论是研究理论者自己搞出来的,是为了研究起来方便,还想指导作家。真正写作的人从来没想到这些问题,他是从生活里出发的,生活里给他印象最深、感觉出来的就写。一般作家是没什么“主义”的。有一种作家想创造一条路子,先搞个什么“主义”出来,大宣传一通,怕别人不了解。像欧洲一些现代派画、抽象画,我实在看不懂,几十年了我也看不懂。就文学作品来说,它还是为多数人服务的,它将存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存在下去还是要人懂的。很奇怪,有些人搞创作先要自己解释,要搞个理论;其实作品跟读者见面要作品本身能打动人,而不是要先看理论;有些打动人的,一辈子忘记不了。
过去知识分子讲“气节”,秋瑾被杀了还有人收尸
巴金:我是主张大胆写作的、创造的。我的1962年的发言题目就是《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主要就是作家缺乏勇气和责任心。我也是这样子。
李黎:可是“勇气”太大了,大概从“反右”就打下去了,到了“文革”时说不定就给打死了。
巴金:当然也有。那时没想到这点。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就是这样子,平反不了就死掉了。“反右”的时候还没想到这些问题。这一点我们只能怪自己,如果真正坚持就不会这样了。我觉得中间老舍倒是写了好多好作品,像《茶馆》,是老舍最好的作品,但写的还是解放以前。老舍是跟得最紧的,他劳动强度真可说是劳动模范。但他的结果……(黯然)我想起来很难过。
……陈企霞讲过一段话,我也重复讲过,就是过去的时候还有人仗义出来说话,秋瑾被杀了还有人收尸;现在一个人说有罪,谁都怕,朋友都跟他划清界线,没有人来仗义执言,没有人出来辩护一下。
我觉得知识分子有很多缺点。中国过去知识分子讲气节。现在气节呢?搞改造的时候,把这个也“改造”掉了(笑)。面子架子都丢掉了。现在最可怕的就是这个。没有气节。朋友都靠不住了,谁也不找谁,我“靠边”的时候很清静,谁也不来找了。所以我提议现在应该有点人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也好。现在应该鼓吹点革命人道主义。有了人道主义,很多人不至于活活的没有什么罪名就被打死,不至于好好的就开了追悼会。我倒没受过体刑,精神折磨有。我说人道主义现在是需要的。不管怎么样,主席也讲过不能虐待俘虏嘛。
中国文艺的前途
李黎:请谈谈您对当前中国文艺的前途有什么看法吧。
巴金:首先一个是要贯彻“双百方针”,一个是“民主”。主要的还是要作家自己了解自己的勇气和责任,不能靠别人给。作家不是在上层指挥下写出东西的,文学史也不是这样写出来的。还是要靠作品写出来的。希望现在的作家能多写些东西出来,只要编辑方面能大胆一点,反正有法在,该吃官司就吃官司。
李黎:问题是写了敢不敢发、能不能发,条条框框多不多。
巴金:就是这个问题。一个是敢不敢发,一个是改不改他的。
不过现在好点,全国刊物很多,有时这个刊物不敢发,另外的敢发,也有几家敢说话的刊物。现在是编辑责任重大。我觉得让题材宽阔一点,让作家放手写一点,胆子大一点。
李黎:中央叫大家胆子再放大一点,可是才大一点,就有“歌德”、“缺德”这些话来了。
巴金:直接管的人也不同啊,编辑也不同。慢慢来嘛。都是这样子,不会明天起来就忽然形势好转了。
你不晓得当时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以为真犯罪呀,(笑)我们真老实呀,真想改造个彻底,我真想在机关传达室里做个值班的,都觉得幸福。那个时候批判我时,我是觉得真有罪,认真地考虑。后来我才发现他们假,他们不认真,他们完全是演戏。我就看了觉得自己比他们高了。所以这也是有个过程的。
对文化大革命要总结,多留点材料也好。现在也复杂得很。本来说等以后下一代总结嘛,现在好像等不了,恐怕得总结了。总之,前途是有希望的……
(摘自《半生书缘——寻访世纪文学心灵》,三联书店2013年8月版,定价:29.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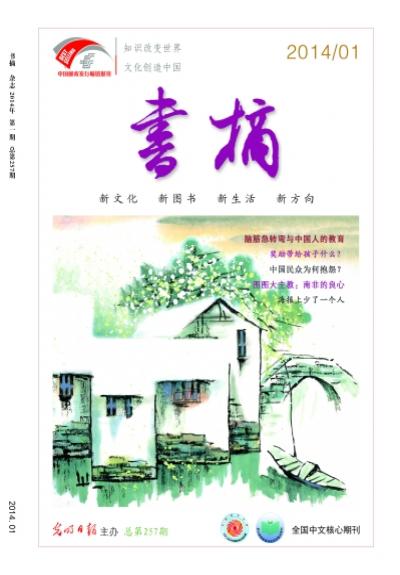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