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风
(7月17日)
……
我扶王元化先生到医院的走廊里,先生的身体靠着我,我感到了先生的虚弱,我们用非常慢的脚步踱步,走廊中只我们单独两个人贴在一起。
先生感慨地说,琦幸啊,我想我给你讲一下一些不宜现在发表的历史,你要答应我,要等到我眼睛闭上之后才能公开。我点点头。
先生喘着气慢慢地说,那就是在反胡风的时候,胡风曾经说过“对于王元化要拆穿他”。
“拆穿他”,是怎么回事,我不讲,没有人知道。这是胡风给罗洛一封信里讲的。
先生几乎是贴着我说,我那个时候弄新文艺出版社,出一些书。胡风那个人宗派意识很强。他们认为只胡风一派的书可以出,别人的书都不可以出。他们想出天蓝(原名王名衡,诗人。后被打成“胡风分子”。此处指要再版天蓝的诗集《预言》)的一部诗集,后来华东文化方面的主管部门不让出,说其中有些问题。他们不服气,我也跟他们说,这是不能硬来的,要按照组织原则。但是他们不大懂。他们就写信给胡风,说王元化不愿意斗争。我说这是领导机关的(意思),天蓝的书只好这样,于是他们说我是两面派,对领导不提意见,实际上心里是有意见。这就是要“拆穿他”的意思的由来。
是啊,总要有个组织原则。胡风这些人不懂这些。我对于胡风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不喜欢的。但是后来说胡风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的。后来(被打成“胡风分子”)搞了半年,结论说你对敌斗争是好的,受过表扬的,为什么在胡风这个问题上没有站出来。我只好说胡风思想是反动的,反马克思的,但是我从组织上没有办法说他是反革命。我不承认的。(当时的文化界领导曾经说:“只要王元化承认胡风是个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是王元化始终无法承认胡风是反革命,认为他只是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尽管他并不认同胡风的所有文艺观点以及组织作风。)
我听了不由得暗自佩服先生的这种骨气,这是何等的人格?我不由得说,那你不是两头受气,两头受到冤枉了吗?
先生说,琦幸啊,我这个亏吃得可大了。胡风这个人我是不喜欢的,如果他当了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可能比周扬还厉害。
说完这句,王先生顿了一下,叮嘱我道,这些东西等我闭上眼睛再发表吧。
于是我们在走廊里默默走着,回到病房。王元化先生躺下休息。没有再说话。
关于第三次反思
(7月19日)
天气非常热,买了一些水果,让先生榨果汁。我到先生床前,把他扶起来,慢慢坐到沙发上。
我主动谈起了有关王先生三次反思的话题。我说,您的一生有过三次重要的反思。这三次反思发生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不可以说,上世纪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在你的三次反思中是最重要的一次。
先生说,那当然了。我的第三次反思主要谈的呢,就是整个的启蒙思想,后来的启蒙思想形成的一种倾向。启蒙运动,使人类脱离了中世纪,人们觉醒了,相信人的力量,相信理性的力量,这都是很好的。没有这个,人不能从中世纪慢慢走出来。只是过分相信理性的力量,过分相信人的力量。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面就说到的,他那个时候就批评了,他用了一个古希腊语,翻译出来就是“不可知论”。他认为人的认识当然是相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反思是,我觉得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尤其到近代的量子力学,它有测不准定律,开始怀疑了,宇宙里面是不是都是那样子有规律的?我看也不一定有这样的自信吧。
我们的启蒙不是归于启蒙,而是归到激进啦。就是认为人的认识可以达到、可以掌握到相对中的绝对。
后来张汝伦引用苏格拉底的一句话,“我知我所不知”。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往往缺乏这种东西,孔子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样提出了这一个几乎相同的命题,就是说,有很多东西不是我能够知道的。我们缺乏怀疑主义,缺乏怀疑精神。我第三次反思的主要问题在这里,不是批评那些激进主义和“左”的问题。激进主义的根本核心是在这个问题里,当然激进主义我是批评的。
所谓思想界的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它可以并存的,有时候甚至可以互相吸取点什么东西,虽然它们在竞争时斗得很厉害,但不是一个绝对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解放后,一个时期使文化遭殃的就是这个东西,造成极大的混乱。这种情况是二十年中国哲学的倒退,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一种紧箍咒似的厄运。人类的认识领域是极其狭窄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微观是无穷的,你只是认识某一个的一小部分,再深入下去,你就不会认识。在宇宙里面你不过是小小的地球,(在这上面)你认识了一些知识。但是离开了地球,你的物理学、化学不一定都有用。人的认识是一种真实的反映论吗?我怀疑。我觉得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这是我的最根本的一个命题。一旦认为自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非常大胆和独断,因为不是为了个人的东西,是为了真理。这是我的第三次反思的核心。
中国思想史有一个脉络
(7月22日)
……
先生说,我们今天谈谈学风的问题。我说,好啊。
先生说,陈澧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太被人知道,但是他对乾嘉以后的学风影响很大。他提倡治学不立门户,这是了不起的见解。
我们近代的思想史啊,有一个偏差的地方,就是说着重在政治,着重在维新改革这个方面,因此对于整个学术的脉络就没有理清楚,比方用的都是维新的啦,或者张之洞啊,李鸿章啊,然后是戊戌的一些人,包括严复后来的《天演论》啊,都是这样的一批。但是在整个清代它总有一个学术思想脉络,这个学术思想脉络是要花工夫研究的。
我们的思想史,什么东西都不提。潮流为什么会有,怎么个变化呢。思潮不是一个突然的无缘无故的变化,而是一个学术发展当中的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脉络。
陈澧认为学术可以很缓慢地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的。你看后来像康有为,突然之间从廖季平那里学了今文学,他的什么《孔子改制考》啦,《新学伪经考》啦,都是很虚浮、很浮夸的,经不起推敲,这样就形成了社会上会有不道德的风气。
我这才知道先生的意思,哦,从学术的风气不端,可以影响到社会的风气。学术风气不仅仅是知识人,而且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风向标。我问,那么就是从康有为开始有这个问题。
先生说,是的。我觉得康有为对当时的社会影响很大,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先生拿出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翻到其中一页说,我觉得钱穆的有一种解释很好,说有一些人他不愿意去强为争驳了,跟人家去辩论啊,讨论啊,像我们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跟人辩。他说卷入门户派系之争,就要显示自己立学之正,之大了。所以他希望学术不住地自我掌握,收到一种潜移默化之功,不是一种刺激性的对人的感受。人家真正地去读了他,很好地去理解他,这才能真正产生一些影响,这个话我觉得说得很好。
我说,也就是说,一种学说或学术的提出,不是强要人去接受,而要让学术自身发挥作用,慢慢地自然形成一种影响。
先生赞赏地说,你这个理解不错。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比梁启超的那个更有用,因为他的资料完备,梁启超高屋建瓴,很有气魄,写得也很好,我说这些,朱维铮恐怕会不赞成的。
章太炎号称古文学派,他是最后一家古文学派。但是太炎先生是一个反传统很厉害的,反儒很厉害的人。实际上他跟真正的古文学派原来的东西距离很远了,他在那里赞成法家,赞成秦始皇,而批判儒学。反专制却赞成秦始皇。
先生又举出一个例子:鲁迅也是这样。
我答道,是啊,鲁迅是章太炎的学生。
先生说,鲁迅的国学没有超过章太炎的范围,在国学方面,鲁迅没有什么新的见解。
我说,那么鲁迅的思想中也有这种矛盾之处吗?就是对于传统要反,但是心里还在保留着这些东西。这个观点确实其他人没有谈到过,也没有往这方面去想。
先生颇为自信地说,从来没有人谈过,我谈的观点多半都不愿意重复别人的话。
关于鲁迅
(7月23日)
……
先生说,昨天我们谈到的是鲁迅。鲁迅的法家思想很厉害。《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凭自己的政治观点立章节。对儒家的评价很低很低,对法家的评价很高。
我们中国的思想史是一塌糊涂,一本糊涂账的思想史,很多问题都没有理清楚。
鲁迅在这方面就比较地偏,你看那文学史(指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他对贾谊的评价不高。实际上贾谊假设不做《过秦论》,西汉的儒者假设不把秦朝作为总结,西汉王朝也许没有一两百年就完了。这是要经过多么艰苦的摸索过程。
鲁迅当年恨程朱理学恨得要命,取名字都是取骂程朱理学的名字的,坏人都是程朱理学的人,我觉得他非常有才华,偏才的闪光啊,但是有时候实在偏极了。鲁迅说我喝鱼肝油不是为了爱我的人,是为了恨我的人,这不是斗争哲学么。
鲁迅的偏激在当时是很可以的了。所以我说五四有四种思维方式,其中一个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点。鲁迅是的,陈独秀是的,胡适也是的,在这个方面他们都一样的。我批评鲁迅是有一点,实际上我是很尊敬他的,对他很佩服的,但对他的缺点我一定要指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治学态度嘛,迷信什么你就让我全部说好,我是做不到的。我觉得研究鲁迅必须要实事求是。
他们(那些研究鲁迅的人)不懂章太炎,也不晓得什么儒法啦,这些问题搞不清楚,所谓鲁迅研究。并不能只是研究鲁迅,而要综合地各个学科一齐来。这实际上是因为鲁迅本人的学问和思想是牵涉到很多不同学科的。
(7月25日)
当年,国难当头,爱国情绪兴起,读了大量的鲁迅的东西,非常佩服,觉得他把中国的问题讲得非常清楚,当时所有的作家中我最佩服的是鲁迅,喜欢他的小说的沉郁和杂文的犀利。他的所有东西我都读了,有的甚至还能够背诵。但是后来的观点有所变化,鲁迅在他的《二心集》之后,接受了党的理论家瞿秋白等人的影响,不少文字都带有遵命文学色彩,思想开始左倾,例如对于群众的看法,早年对于群众有着客观的看法,但是到了晚年,同样的一件事件,他却站到群众一边。
不过,鲁迅到了晚年逝世之前的有的文章,超出了左翼的影响的局限,写得非常好。像《我的第一个师父》、《女吊》、《死》等等,对于人性的刻画非常细腻。可惜并不多。
……
(摘自《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28.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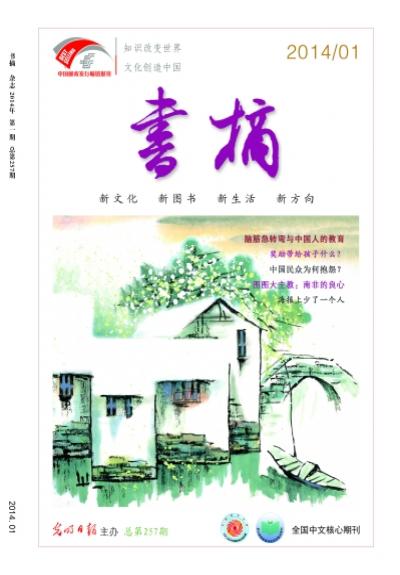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