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汪曾祺先生,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传说中读者与作者的相遇一般惊心动魄——“我读了你的作品,夜不能寐”。但我碰着汪先生的场面,显然没有那么气派。一个小孩子要出门去玩,照她的习惯,得带上一本书,一本愉快又不轻飘飘的书。于是,她从母亲的书柜里挑了一本汪曾祺的书。
当时的阅读记忆,现大多已在脑海中淡去,除了《故乡的食物》。11岁正是对食物最感兴趣的年纪,异国的土地上,我把这一篇翻来覆去地读,活活把东南亚菜品吃出高邮的味道来。从前,我以为写美食只能写它的滋味、色泽,顶多写到如何烹调也该结束了,哪里想到还有人把话题扯过来拉回去。写斑鸠,光写它与猎人的搏斗,对其滋味只字不提;写“鵽”,先把此字的门道摸清楚,再辨析“鵽”与“沙鸡”之别,至于味道,“鵽肉极细,非常香。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比鵽更香的野味。”好了,这就算完。
回国后,我的中国胃被安抚,这本书也放下来了。往后几年,多是些色彩浓重的文学作品充斥着我的视野。老实说,它们也与横冲直撞的少年气质更相符些。话虽如此,得空我还是读了不少汪先生的书。究其原因:他的文章短。特别是小说,多是下课铃响了拿起来,上课铃响了能放下的篇幅。后来,读《说短》,其中道:“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他确实诚恳地实践着鲁迅的教导: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删去。
此番思想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颇深。写作者时常面临一个问题: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一不留神,就容易废话连篇。于是,我向汪先生学习“收着写”。首先,把语言收住。这主要有两点,第一,短。第二,准确。其次,把感情收住。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收得太紧,小说会变得冷漠;收得不紧,有一种张扬肆意的风格。我读汪先生的文章,感到他的感情很深,但这种很深的感情都很重地放在一个句子里,这个句子便成为整篇文章的重心。例如,《鉴赏家》写画家季匋民和果贩叶三的友情,很深厚,然而深厚到什么程度呢?“叶三死了。他的儿子遵照父亲的遗嘱,把季匋民的画和父亲一起装在棺材里,埋了。”
按理说,照汪先生这种写法,文章虽可以短而准确,未免失去些意趣。因为读者读书是需要反应时间的,文章太短,略有所感时,已经结束。显然,汪先生的文章没有落入这个套子。应该说,他对在重要部分下笔墨总是很吝惜的,力求以最简短而准确的用词来表现“主题”。除此之外,他在文章中放了许多“闲笔”。这些“闲笔”看起来郑重其事,洋洋洒洒一大丛,让人难以忽视。可若比“主题”为明珠,“闲笔”为草木,单赏明珠,光华太盛;单看草木,无甚色彩;而草木葱茏,明珠其间,就是一个相映成趣的场面。更别提他的“主题”与“闲笔”其实构造自然,从未互相混淆,这是功夫。
梅尧臣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如果平淡意味着缺乏戏剧冲突,那么汪先生的小说,可以说是平淡的。他爱写人们在街头巷尾能看到的生活,这在80年代是比较稀奇的。起先我以为他性格敦和,所以作品也如此,后来发现,倒不全是。他是刻意藏敛了某些伤痛在写的,他的愿望是叫人有点反思,而不是写得那么白,叫人伤心。他的故事最多只叫人心酸,他人真好。
汪先生对自己的定义很清醒,“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他的儿子汪朗也对他的写作提出看法:“人间送小温,决定了汪曾祺不会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深刻、伟大,这些词像天边的月亮,很远,很高,人须仰望。汪先生不会写月亮,不会写波澜壮阔与振聋发聩,他笔端是月亮下的闲话家常,是有过童年的人们望着月亮时想起的真正景色。
机缘巧合,我在汪先生视为第二故乡的昆明度过了大学四年,母校正是前身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的云南师范大学。文林街、正义路、金马碧鸡坊……他的文里文外都已被我摸得门儿清,我甚至到处寻找他所写“培养正气”的汽锅鸡。我循着他的足迹认识昆明,我对写作和生活的认识,也无不是如此。
我是一个受汪曾祺文字庇护长大的孩子,这实在是一种幸运。
(作者:张闻昕,系云南师范大学学生)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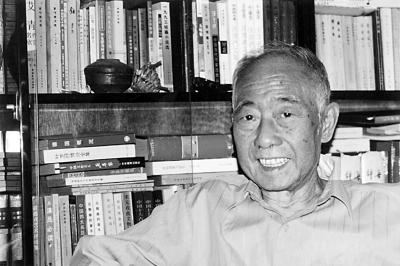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