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我便进入了西京城郊一个既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村庄——文庙村。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小村庄构成的小社会,它是大社会大世界的缩影,更是与正在行进着的当代生活发生同步声响的艺术世界。文庙村呈现出的令人屡屡感到心理纠结以至悲怆的生活世相,正是陈彦对生活的客观再现和对生活本真的还原,因此也产生出更富感染力的艺术效果,足以见出作者从生活到艺术创造的深厚功力。
文庙村具有强烈和浓郁的文化象征韵味。这与村子的历史渊源,以及这个以文化立庙的专注于文化象征的名字有关,而更深彻关联的是,小说人物精神心灵世界里有着浓厚得难以淡释的文化底蕴。这些人物中首先得数罗天福。
罗天福是从山区来到文庙村打工的一个农民,在山区老家的村子里当过民办小学教师,后来又当过本村的党支部书记,其身份依旧是农民。然而,他精神和灵魂里的文化底蕴,决定着他的行为方式,无论在纷繁的谋生市场,还是在家庭频发的诸多事变中,罗天福都在坚持着一种道德操守。
我在感知罗天福精神信念的坚守所遭遇的几近破灭的痛苦时,也感知到作为这个民族传统精神和传统美德所面对的危机。罗天福的痛苦,当属今日商品社会诸种世相冲击传统道德底线必然发生的事。作者将罗天福的人物身份定位为,既做过民办教师又做过乡村支部书记的一位农民,这个人物形象具有阔大的社会基础和深广的典型意义。他对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痛苦坚守,也就有别于知识阶层从理论意义上的探索、疾呼,更见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在社会底层的蕴藏和面临的危机。罗天福的生存空间里,显示着人文人性人情的审美剖析与审视,是一种贴近的现实感与崇高的审美感的汇聚。由此可见出作者陈彦对当代生活的倾心关注和敏锐发现,也见出他独有的深刻思考和难得的生命体验。
罗天福的儿子罗甲成,是从山区刚刚进入西京城里一所名牌大学的新生。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生位置,致使他的精神和心理发生变异。他的根系仍扎在父母打工卖饼子的社会底层的文庙村,而他倚栖的是名牌大学的高校;他既脱离不开维系他生存的打工族这个弱势群体聚集的一方最不堪的角落,又要时时处处面对身边各种优裕者不无得意的面孔。
置身于这种反差极为悬殊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位置里的罗甲成,由于他的个性,即自信与自卑这个难以调和的矛盾构建的精神和心理形态,致使他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心理裂变。我能感知罗甲成的自信与自卑纠结的心理,这个人物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而是当下处于社会底层人群普遍心理形态的涵盖。在庞大的弱势群体尚不能短时期内改变生存状况的时势里,罗甲成这种焦灼的心态就不会缺少呼应者,一个艺术形象的生命力就会久远。
作者用什么样的神秘而又高超的手法,创造出陌生而又鲜活的“这一个”和“那一个”?我以为关键在于他准确地把握着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
罗天福,这个进入城市边沿依赖打烧饼谋生的普通中国农民形象,之所以能对我发生震撼性的阅读效应,就在于他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性。他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最优秀的本质精髓,便是仁和义,便是对善的坚守和对恶的拒绝。他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作为做人准则,而且完全融入了血脉。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他独特的心理结构形态。陈彦准确地把握着罗天福这种独特的心理结构,个性化的“这一个”就呈现于他的笔下、读者眼前了。我从罗天福的身上,感知到民族传统的优质文化在民间的深厚蕴藏,且相信这不是“最后一个渔佬儿”,那些和他一样从事各种职业打工谋生或继续在乡村依赖土地春播秋收的农民群体中,不乏与罗天福一样恪守着传统文化且融入血脉的默默无闻的人。
在罗家父子时断时续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中,透过表层的具体事由,我看到的仍然是不同文化心理结构之间的冲突。罗甲成既缺失传统文化的修养,似乎现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也很淡薄,支撑他自信自尊到欲望膨胀的一点优长,仅是聪颖的天资。这样,他和父亲罗天福的冲突,就是截然相异的两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冲突。作者陈彦以解构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这把钥匙,打开的是深入人物灵魂的各个隐秘的角落。再看颇具神秘色彩的另一个人物东方雨老人,他与罗天福素昧平生,只是在文庙村不期而遇,即进入相识且相通又相知的状态,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信奉是“无隔”的。尽管他们在文庙村的生活位置颇多差别,个性里的情趣和行为也各具一格,却丝毫不影响由精神心理的相通形成的相互敬重。及至罗天福把处于精神崩溃状态的儿子送进东方雨的神秘院子,罗甲成才终于找到了精神和灵魂的栖息之地,即对传统文化的归属感。未来的罗甲成如何完成自我的精神剥离,以及重新建构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完全可以期待。
罗天福这个人物丰厚的文化心理蕴藏,必然会对周边的各色人物产生影响。罗天福的文化心理决定着他在文庙村这个小社会和家庭中的个性行为。陈彦准确地把握住了罗天福等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创造出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物。单就罗天福而言,当属当代文学作品中独得的“这一个”。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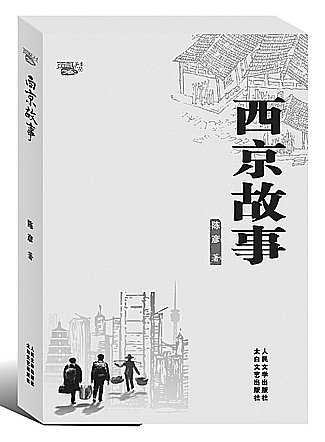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