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数不多被美国政府明确禁止的实验项目上,政府资助的克隆人研究名列其中。我担任副总统期间,1996年首只克隆羊多莉刚诞生不久,当发现克隆人很快可能变成现实,我强烈支持暂时禁止下一步将人类牵涉其中的大规模探索项目,并且提议成立新的美国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来审查克隆人技术在伦理、道义和法律上的影响。
几年前,作为参议院科技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我成功推动“人类基因组计划”中3%的支出用于研究该计划在伦理、法律和社会方面的广泛影响(现在被称为ELSI资助),这能确保对那些复杂问题——它们本身涌现的速度要比答案来得快得多——进行详尽研究。这已经成为由政府支持的最大的伦理研究项目。后来被任命为基因组计划主管、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者之一詹姆斯·沃森对这一伦理研究项目给予了非常积极的支持。
几乎是从DNA时代一开始,克隆人的伦理问题就被推到风口浪尖。沃森和克里克于1953年发表的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并没有忽略,我们提出的这种特定染色体配对理论直接意味着可能出现基因材料的复制机制。”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担任美国众议院科学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时,我曾经进行了一系列关于克隆、基因工程和遗传筛查等新兴科学的听证会。当时专注于克隆动物的科学家在15年后成功地创造了多莉,而自此以后,他们克隆了很多其他家畜和动物。
但是从实验一开始,这些科学家就非常清楚,他们在克隆动物上所取得的成就可以直接用于克隆人类,唯一阻止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伦理担忧。从1996年起,几乎欧洲每个国家都认为克隆人是违法行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把这一行为称为“伦理上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将违反某些主导医疗辅助生育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类基因物质安全的保护”。
然而,大多数人预期随着时间推移和技术的发展精进,克隆人最终还是会出现——至少在具有明显医疗裨益而且大体不会对被克隆者和社会造成明显危害的情况下。2011年,纽约干细胞基金会实验室的科学家宣布他们已经通过对一个成人卵细胞重新编码将其调回胚胎阶段,然后从它出发创造能自我复制的相同胚胎干细胞,实现了人类胚胎克隆。尽管这些细胞的DNA同捐献卵细胞者的DNA并非完全相同,但是它们自己彼此是完全一样的,这提高了在它们身上进行研究的效率。
包括巴西、墨西哥和加拿大在内的一些国家禁止克隆人类胚胎研究。美国还未能实行这一点,而一些亚洲国家则似乎对大胆着手克隆人类胚胎的科学——只要不是真的克隆人的话——顾忌少得多。不时有报告称有这个或那个不孕不育科医生在某个不禁止克隆人类的国家里某处秘密实验室里工作,并且已经成功打破了针对克隆人的现代禁忌。这些故事大多数,甚至全部都被认为是伪造的。目前还没有任何克隆人诞生的消息得到确认。
总体而言,那些倾向于同意克隆人实验的人认为这一进程同其他形式的科技进步并无本质不同,任何情况下都无可避免,而且其医学贡献要比大多数实验的前景更有希望。他们相信,是否要进行某种特定克隆的决定权应该像堕胎决定权一样,掌握在父母一方或双方手中。
那些反对克隆人的人则担心其应用将会削弱个人尊严,有可能使人类变得“商品化”。理论上,克隆可能会导致大量复制同一个样本人的基因,形成大批量生产,这一过程同自然生育有着本质差别,就如同制造业和手工艺之间的关系。
有些人的论断建立在每个人都拥有权利和应该受到保护的宗教观点上,但是也有很多人并非出于宗教理由反对克隆人类,而是出自一种更为笼统、事关个人尊严的人道主义。本质上,他们担心对于人类的利用可能会削弱这些被利用的人作为完整之人的定义。然而,这样的担心似乎建立在人类可以被简化为各自的基因组成这一假设上,这一观点同那些认为要把保护人的尊严作为优先考虑的观点有所矛盾。
无论是暂停发表包含如何制造危险的H5N1禽流感变异病毒细节的论文,还是暂时禁止政府支持克隆人研究项目,两者都是非常罕见的例子,代表了对于发展可能出现潜在问题的一种深谋远虑(或者争议),为的是评估它们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产生的影响。两者也都证明美国的领导力带来了至少是暂时性的全球共识。在这两件事上,并没有出现某个强大行业不顾公众疑虑一意孤行的情况。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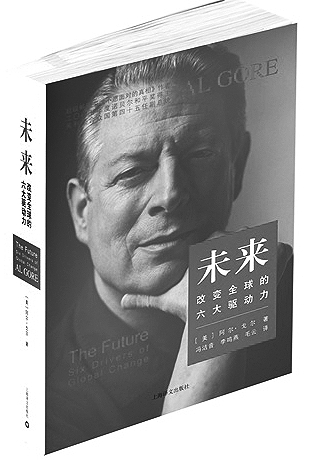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