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行进在烟尘弥漫的官道上,他突然停下来,咕噜道,“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可是在今天,所有的远游都有些像郊游,所有的乡愁和离情,突然间有了虚假的味道。“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走不出我的视线”,当这种诗情变为现实时,我们一半是欣慰,一半是失落。短信,QQ,微信,微博,Skype……它们永远追踪着你,让你无处躲藏。
30多年前,当我离开皖北家乡,前来北京读书的时候,家父千叮咛万嘱咐,家母泪水涟涟,好像儿子即将万里关山,一去不返。走进大学校园的我,至少有几个月思乡情重,心绪低落。歌手张明敏在《毕业生》中这样唱道:“回忆当年离乡背井,深夜里梦回旧家园。游子的热泪沾湿枕畔,最难忘父母的慈颜。”赶考的学子,怀里总是日夜揣着父母。
那是1979年,转眼到了2009年。30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又一个儿子将“离乡背井”,到遥远的地方继续啃书本。但这个儿子和当年的父亲不一样,他是主动放弃了离家门口不到10公里的最高学府,远走香港。
校长、班主任苦口婆心,亲戚朋友不是指责就是表示惋惜,只有我态度漠然,听之任之。当香港大学前来面试的那位英国绅士给了他一个strongly recommand(强力推荐),当香港中文大学一遍遍地打电话来,对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毅然决然地做出了选择。
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很快的,他开始怀疑自己。坐在开往香港红磡的火车上,儿子满脸的不乐,好像只要跳下火车,他就能重新做一次选择。一路上,他一直都在玩那个新买的手机。这仿佛是一种象征:在他读大学的四年里,我们每个人手中的手机,都变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难以废离;同样越来越重的,还有网络。
在香港,父子俩住在沙田的丽豪酒店。第二天,从沙田乘港铁前往只有四站地的香港中文大学。快到的时候,儿子突然说道,我的选择可能是错误的。我看了他一眼,没有吱声。他又说,这个夏天,可能所有的选择都是错误的……
转眼4年过去了,今年夏天,儿子从香港中文大学毕业了。我去香港接他,帮他收拾、清理东西,找了一辆车往深圳搬运。离开学校的时候,他望着校园葱茏的山色,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他说,我选中文大学,选对了。
4年之后,在他身上所发生的变化,正是我想看到的。同时我也更深刻地认识到,无论是超音速还是高铁,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物联网,被缩短的都只是表面的距离;文化的同质化也只是一种表象,很多东西你必须身处那种环境,才能学来。
一位深圳的朋友到罗湖关接我儿子。他发现,在我儿子的背包里,装着一个很大的水壶。“在内地,哪个大学生出门还背着水壶?都是买矿泉水喝。但香港的学生不是这样,因为是花父母的钱,总是能省就省。”在香港,儿子学会了用钱,该花的时候就花,不该花的时候一分也不花。
大三和大四时,儿子先后在民族证券、光大国际和中信银行等机构实习。我本以为他只是为了拿一个实习鉴定去糊弄学校,没想到他对实习要求得很高,对鉴定反倒不太在意。这和内地大学生有些不一样。
我还注意到一些细节:每天晚上,儿子都得把短裤和袜子洗了,永远是自己洗;逛商场的时候,如果他买了一件稍贵的东西,他的脸上都会有一种歉意(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挣钱);在外面吃水果,他会一直拿着那些果皮,直到找到垃圾箱;他们大学同学聚会,几乎都是AA制和分餐制……
我把儿子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当他再回到北京时,我看到了两种文化的冲撞给他留下的痕迹,我看到他成功地避开了关系的困扰和各种不良习气的熏染。从另一个环境里归来的儿子,像一面镜子,照得我常常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和习惯而感到羞愧。
这个夏天,儿子又面临着选择。开始是在留港工作和出国读研这两者中间选择,然后是到哪所大学留学的选择。在他所申请的学校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士)、哥伦比亚大学、伦敦政经学院等名校都录取了他,衡量再三,他却选择了一所最没名气的学校——克莱蒙特学院。唯一的理由是:克莱蒙特给奖学金,不用花家里的钱。
这孩子,这思维,已经完全是“国际化”的了。我本想说:“儿子,你要上最好的学校,家里给你钱。”但看着他那张青春、激情、充满自信的脸上全是灿烂的阳光,我张了张嘴,努力把话咽了回去。
(作者为本报高级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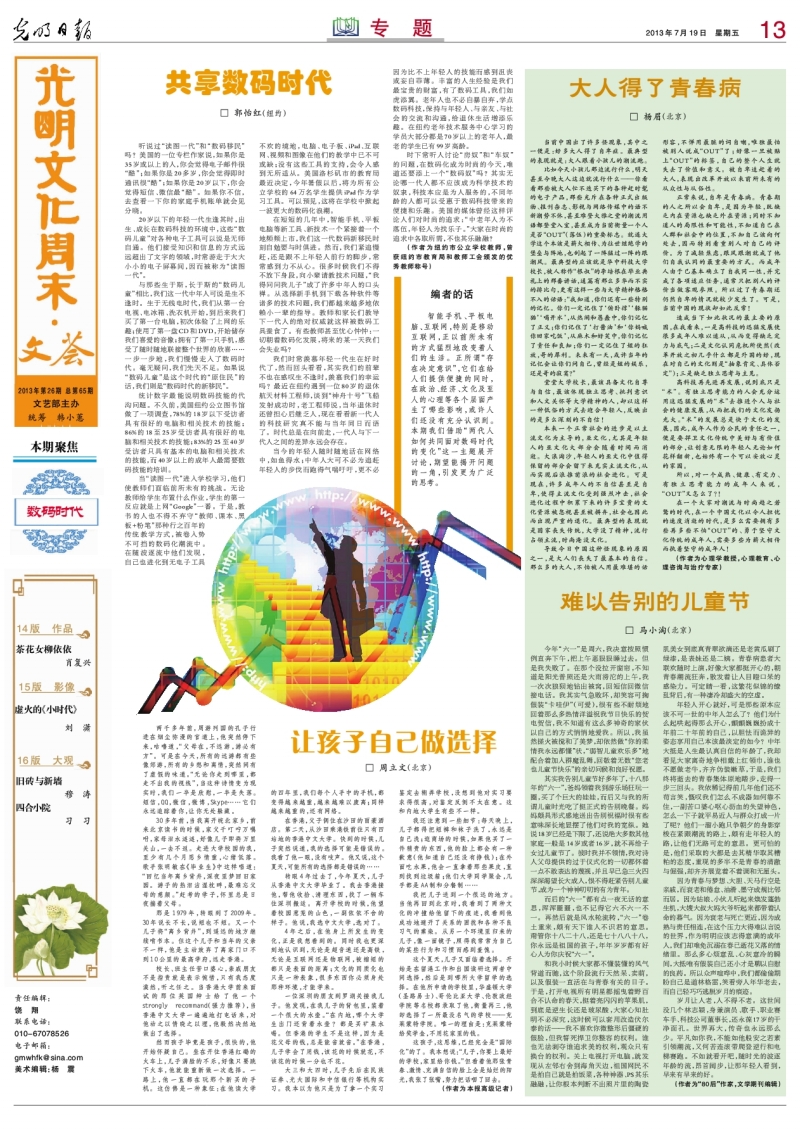
 上一版
上一版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