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五十多年前毛泽东与罗稷南关于“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的对话“打动现实的兴趣”,引发了不小的“波澜”,或以后辈视角叙述“前人事迹”,或以亲聆身份回忆“亲历过往”,或以学术思路追寻“历史真相”。今年4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以下简称《追寻》),似可看成是这场风波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对比此前轰动一时的说法:“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著者秋石先生(原名贺金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通过多方考证,基本认定毛泽东当时的说法应该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相信读者不难从中解读出前后迥异的情感基调和语义内涵。
只是,同一场“毛罗对话”,内容并不复杂,亲历者仍有健在,结果却为何会如此大相径庭呢?
相异的观点主张常常来自不同的认知态度和言说方式。关于历史的认知和书写向来既有史家所主张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也有文人所提倡的“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诗性风格。《追寻》中,秋石正是从质疑亲历者对“一段重要史实”的认知和言说开始,继而发现其关于“亲聆”的描述破绽百出的。
让秋石不解的是:“亲历者”既然意识到“这场短暂而又撼人心魄的对话涉及中国现代史的一段重要史实”,为何要随性地运用“遥体人情,悬想事势”的文学笔法?为何要草率地把它视为“孤证”不作校核?为何要轻易地将它全权授予他人“放手删改、调整”?
“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底(的)思索,打动现实底(的)兴趣,和现实底(的)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只有在我们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上世纪40年代,朱光潜对克罗齐关于“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作出的阐释,对于今天如何看待和寻找“历史真相”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不管是亲历者的回忆还是质疑者的辨析,五十多年前的“毛罗对话”都是在当下现时的思想活动中复苏并获得它的历史性的。然而,当亲历者跨越超过半个世纪的风烟重回那个短暂的瞬间时,经历了多年世道沧桑和人情冷暖的冲刷与改塑,此“亲历者”已非彼“亲聆者”,更何况追忆时又如此感性,书写时竟那般修辞。因此,“亲历者”的回忆遭遇“追寻者”的质疑应在情理之中。
文学以虚构想象取胜,史家凭客观事实说话。假若是文学者,以自身经历“遥体人情,悬想事势”,本无可厚非。然而,“这场短暂而又撼人心魄的‘对话’”偏又涉及“一段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史实”,关乎两个对社会历史进程和民族精神指向举足轻重的伟大人物,因而,即便是“亲历”或“亲聆”都应该以史家实录精神“析理居正”,“文疑则阙”。因为有时即便是亲历者回忆亲历事也总免不了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有意或无意地“虚其美,隐其恶”。
记得上世纪80年代,罗尔纲在《关于胡适的点滴》一文中,记述了1930年11月28日与胡适一起自上海迁北京在火车站时的场景。根据他的回忆,“广交游”的胡适在离别上海时孤寂凄凉,几乎没有一个朋友来送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罗尔纲纳闷不已:“为什么亲朋满上海的胡适今天却一个人都不来送行呢?”
但是,学者余英时却在胡适当天的日记中读到:“今早七点起床,八点全家出发,九点开车。到车站来送别者,有梦旦、拔可、小芳、孟邹、原放、乃刚、新六夫妇、孟录、洪开等几十人。”于是,余英时在确认了并非罗尔纲记忆不好之后,感慨道:“我不愿去猜测他的动机,但是我敢断言,这是他想以浓墨刻画出一种极其恐怖的气氛,所以才虚构出这样一篇绘声绘影的绝妙文字来。我不能不佩服他想象力之丰富,但是如果胡适这一天的日记不幸遗失,罗先生的虚构便将被后人当成实录了。”
史学大家尚且如此,可见,个人回忆录的史料价值的确值得审慎。
有着“资深媒体人”和“草根学术研究者”双重身份的秋石先生,正是怀着新闻工作者的“求真”和学术研究者的“严谨”投入这场关于“毛罗对话”历史真相的探寻。
首先,作者努力寻找到仍然健在的“亲聆者”。自2003年1月至2009年2月,秋石耗时六年多,自费数万元,逐个寻找1957年7月7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参加毛泽东同志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会的健在者。在对当年36位“亲聆者”50次的“寻踪问迹”后,秋石查实:2002年还有8人在世,2009年仍有3人健在。
其次,作者认真阅读了当年“亲聆者”的回忆材料和相关历史文献。在认真查阅座谈会不久《解放日报》刊载的《毛主席接见本市文教工商界人士》报道,以及《文汇报》刊载的黄宗英、应云卫、谈家桢、李锐夫、漆琪生、笪移今、束世澂、苏德隆等13位“亲聆者”的感受发言后,秋石发现:毛主席当时接见的是上海文教工商界代表,而非仅仅是文艺界人士;座谈会的现场“一派随意祥和气氛”,而非“天地幽纷,忽明忽暗”;所有出席者在与毛泽东同志亲切随和的谈话中无一不是心情激动,深受鼓舞,而非“疾电炸雷,交错撼震”。
尤其是在查阅了1957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秋石找寻出毛泽东当年关于“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的明确回答:“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在此基础上,秋石经过多方调查、考证,认为毛泽东的回答应该是:“依我看,依鲁迅的性格,即使坐进了班房,他也还是要说要写的。”
第三,作者以翔实的材料、严谨的逻辑论证了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在《追寻》的下篇,他认真梳理了自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之间毛泽东与鲁迅虽身未谋面但心灵相通的无数个真实细节和感人画面。井冈山岁月,毛泽东曾对鲁迅的忘年交冯雪峰说:“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对鲁迅著作爱不释手,一套《鲁迅全集》从延安带到西柏坡,又从西柏坡带进中南海。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不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和亲朋好友“读点鲁迅”,而且还把鲁迅奉为“中国的第一圣人”,称自己是“圣人的学生”。
当《追寻》以丰富生动的事例呈现出毛泽东对鲁迅著作阅读之全面,理解之深刻,运用之娴熟时,读者没有理由不相信毛泽东在家书中的那句“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的感慨确系发自肺腑。
历史既不是“想象主体的想象活动”,也不是“僵死事实的汇集”。对于“历史真相”而言,不管是社会名流的回忆,还是草根大众的质疑,我们既不能拒绝科学批评的意见,也要毫不犹豫地坚持真理。历史应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真相永远在于不断地追寻。(作者为南昌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上一版
上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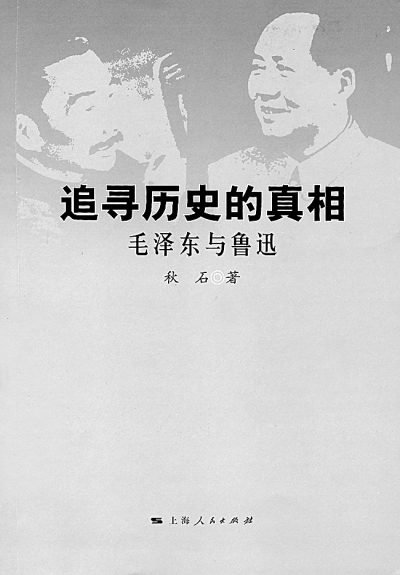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