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名的诗歌中有许多的禅宗意象,这增加了诗歌的朦胧感。《掐花》是废名创作的一首小诗,全诗仅84言,却蕴藉深远。作者从新批评的“含混说”解读这篇作品。
新批评理论中的“含混”概念
上世纪的新批评学派认为,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复杂的而非单一明确的,“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体。当我们反复阅读并且发现文本的新内涵时,“我们通常所指的并不是发现了更多的同一种东西,而是指发现了新层次上的意义,新的联想式,即我们发现诗或小说是一种多层面的复合组织”。([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由此,他们提出了“含混”一词的概念。
含混,英文中来源于“ambiguitas”,现为“ambiguity”,其传统意义是指日常生活用语与文本表达的缺陷,即将观点意图表达得模糊不清或晦涩难懂。西方的文论传统一直将语言的明确性作为基本要求,并追求文本的单一解释,因此在极长时间里,“含混(ambiguity)”含有贬义色彩。威廉?燕卜荪将该词引入文学理论,他强调通过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深入挖掘文本本身的内涵,在《朦胧的七种类型》中,第一次为“含混”一词正名与分类,把文本中语言的丰富意义称作“朦胧(含混)”。在中文语境的文学理论中,“含混”也称为多义、朦胧、晦涩、模糊、复意等。
“含混”不仅是新批评理论的一个关键的批评范畴,它的提出还影响了其后整个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与批评家对诗歌的审美取向。如今,它既可以表示作家创作时的意图与策略,又可以指涉读者在根据自己的经验理解文本时引起不同的反应。在文学批评中,它多用来说明文学语言的模糊性、多义性与不确定性。
《掐花》的多重结构
《掐花》是废名创作的一首富有禅宗色彩的诗歌,全诗仅84个字,却有多种理解,可谓蕴藉深远。与废名的绝大多数诗一样,《掐花》有着梦幻的意境,却又不脱离现实。废名曾说他写此诗的灵感便来自佛经:“读《维摩诘经》僧肇的注解,见其引鸠摩罗什的话,‘海有五德,一澄净,不受死尸;……’”(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221)有感其景其意,便在下意识间创作了此诗。而废名的诗歌中一直充满着大量的禅宗意象,往往有言已尽而意无穷之感,使得读者常常猜测是否有些言外之意未曾被自己解读出来。本文便运用新批评的“含混”的概念来解读这首诗。
《掐花》
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
跑到桃花岸攀手掐一瓣花儿,
于是我把它一口饮了。
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
大概就跳在水里淹死了。
明月出来吊我,
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
此水不现尸首,
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
首句“我学一个摘花高处赌身轻”实为用典,引自吴梅村“摘花高处赌身轻”,原句描写的是一个寂寞女子在寂寞中寻求一丝刺激,“我学一个”带有些孩童的俏皮与不安分,隐隐点出了作者意图背离平淡的倾向,但不明显。
摘花高处赌身轻,何处摘花?第二句便给出解释,至桃花源岸。桃花源岸又是何处?“避秦时乱”之处,是避祸之处,隐居之所,历代文人墨客心向往之然身不能至之所,所谓“世外桃源”是也。为何摘花?从诗人运用的“桃花源”此典可以看出,多少暗藏着对于人世社会的不满,或是对一种超越喧嚣境界的寻求。解释并不是单一的,但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那种意欲脱离于社会尘世、做个不食烟火之人的心态。对于摘花的含义,我们也可以大致地理解了。
诗人已然寻到桃花源,掐下花儿,似乎目的已经达到了,但这时诗中的矛盾便出现了——真要成个仙人的时候,诗人又害怕了,“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在这里,诗人出世的倾向突然就变为对出世的怀疑与害怕,或许是害怕成为仙人所要付出的代价,害怕“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情形,于是竟不惜用死亡来否定出世,径自“就跳在水里淹死了”。之后“明月相吊”,作者欣喜地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凡人”,毕竟凡人才能淹死,仙人怎么会淹死呢?
末句“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则又升华了意境,那种烟云水月的笼罩的哀愁,既梦幻又忧伤,似乎再从人世转向超世的姿态去了。但倘若作“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一语观之,恐怕还是留恋人世与求而不得的伤感居多——双向的解读又再次增添了语意的含混与意境的朦胧。
粗读之下,我们能捕捉的只有那种如梦如幻的氛围,这似乎是首意欲出世的厌世诗歌,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又可以把它看做一首肯定人世的诗歌看待——诗中看似矛盾的意境就是一种“含混”现象的存在,文本内容的悖反显示出诗人自己无法统一的含混思想。这种内容的悖反与含混令读者不知所措,有此诗无解之感,于是读者便会自行放弃文本而去自己寻找解释,自行放弃表面的现象转而去找寻文本之中的真正的主题。
既然难以解读诗歌这种含混现象背后的东西,那我们先来看看与之相关的意象——诗人的死亡——这实际上是出世与入世间矛盾的外化表现:诗人饮下一瓣花儿,本想是超脱于现实人生,但又不愿意脱离于尘世,又犹豫了,这种犹豫与苏轼“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的心态何其相似!于是便有了“跳在水里淹死了”的这一情形,而当他从死亡的臆想中清醒过来时,又愈加强烈肯定了现世,产生了对于现世的温存感(“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此水不现尸首/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行为是入世的,却引用了佛经中“海不受尸”之说将死亡美化,使得死亡如梦幻一般不真实,这种空灵的境界连废名自己也觉得“很是美丽”。用出世的语言描述入世的行为,出世与入世的冲突和转变都交汇于此。
用禅宗的方式去描述入世的行为,这不禁令人遐思:这其中是否体现了儒家与释家的冲突?我觉得是这样的。这种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态度不正是历代文人们的体现么?他们出世时因信仰儒学而心怀天下,避世时又依靠佛道老庄而遁居隐匿。隐居时却还依旧放不下儒家的入世想法,即便洒脱如陶渊明者,在《陶渊明集》中仍有《述酒》一篇在评述当时的政治状况。再联想稼轩被弃达27次,一生都在佛道与儒学之间数度徘徊,在入世与出世间,最后还是选择回归儒家,也不难体会此诗矛盾含混的本质。
诗人的心境应也是如此,废名在谈关于此诗的创作时并未提到这一点,只是单纯地说,他觉着“自己对于生活太认真了”,诗人是无意识的,但是读者却可以感觉到这种意识、这种冲突的存在。冲突在诗人死亡的想象中达到高潮,随后逐渐走向平静,“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更有一种涅槃重生之感,仿佛在入世里达到了佛家拈花一笑的境界,在儒家与佛家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而诗歌也如瑞查兹所言,在“相互干扰、相互冲突、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冲突中“结合成了一种稳定的平衡状态”。( [英]瑞查兹:《想象》,杨周翰译,《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上),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P83)
原文本中隐藏的爱情含义
解读完了文本的这一种含义,我们再回过头去看一看。
先前我们把“花儿”当做世外桃源的象征,但如果把女子当做“花儿”这一比喻的本体,我们竟然又会发现诗歌中的另一层含义——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首单纯的爱情诗歌来看待。与入世、出世的思想冲突过程相近,诗人也经历了追求(“跑到桃花岸攀手掐一瓣花儿”)——害怕(“我害怕我将是一个仙人”)——否定(“大概就跳在水里淹死了”“我欣喜我还是一个凡人”)——释怀(“一天好月照澈一溪哀意”)四个过程,同样的也是把重心与转折放置在“死亡”这一意象之上。诗人在死亡的臆想出现之前,呈现的是一种对于爱情难以把握的心境,想要追逐爱情,却又担心走得太近而破坏了美感,但是从死亡的臆想中清醒过来之后,还是肯定了自己原先对于爱情的态度,释怀了。不禁让我联想起黑塞,黑塞说他爱的只是“爱本身”,所以他可以把自己的爱送出去,“送给路旁的花,酒杯里的闪闪阳光,教堂钟楼里的红色圆顶”。这种心境,这种态度,又与这首《掐花》何等相似。
从诗人死亡的臆想角度中来看,我们会非常奇妙地发现,放弃与坚守、入世与出世、超越与留恋的犹豫不决最终是汇于此处的,所有的含混被死亡的意象消解,又通过死亡再次构成了含混。诗中的“花儿”既可以从爱情的角度解读,又可以通过出世的方向探究,“死亡”意象既可以表示诗人对于爱情的释怀,又可以表示精神上的涅槃。当然,我们不必将它们分别开来对待,这首诗中文文本中的各种含混现象造成的不同意义交汇在一起,形成了整首诗歌复杂的思想状态——这就是含混现象对于诗歌的升华,如果硬要解读并确定出诗歌中的真实意义,反而削弱了诗歌的审美效果。可以说“死亡”这个意象是整个诗篇的基点,它就像一个线团的线头,诗人通过拉动“死亡”来拉动整首诗歌,读者也可以通过扯动“死亡”来体会整个诗歌的含混状态。
朦胧诗的含混使得我们可以做出多种解读。在文本中无法得到充分说明的情况下,读者便会自己去寻求解释。禅宗的意象实际上介于韦勒克定义的“公用象征”与“私用象征”之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无异于私用象征,也可以说它是一种隐藏极深的公用象征,它需要读者自己去发掘破译文本,而废名诗歌浓重的禅宗色彩使得他的诗歌尤其难解又多解,因此含混的出现在所难免。含混多解现象的存在延长了读者的鉴赏过程,使得诗歌的可读性和审美特征大大增强。犹如韦勒克所说“细心的研究者能够像密码员破译一种陌生的密码一样解开它”。( [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修订版)》,P215)这也是废名的朦胧诗可堪玩味之处。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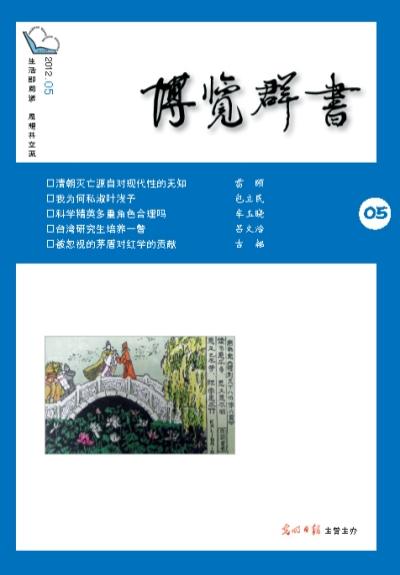


 缩小
缩小 全文复制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上一篇